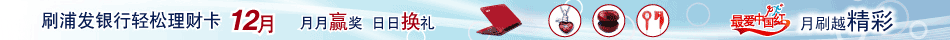尽职的快乐
“尽职的快乐”
在纳粹德国的国家机器中,像耶普森这样本质不坏却恪尽职守的警察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文 | 河西
西吉的父亲---第三帝国警察严斯·奥勒·耶普森,骑着自行车来到画家南森的家。他要告诉南森的是一个坏消息:南森被禁止绘画。从今天起,一年四季无论什么天气,他都要严格执行这个禁令,这是他作为一名警察的职责所在,尽管他们打小就认识,算得上是多年的朋友。
在少年教养院中,西吉被老师关在禁闭室里写作文,思绪仿佛一团乱麻,就在这样如蛛网般的追忆中,西吉重新回到与南森在一起的时光,在父亲“履行职责”时,他却偷偷地收藏南森的画,就当自己在为父亲的“罪恶”救赎。
最终,他给自己完成的这篇厚厚几大本的作文命名为:“尽职的快乐”。
恪尽职守?伦茨在《德语课》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罪责问题:在纳粹德国的国家机器中,像耶普森这样本质不坏却恪尽职守的警察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饱受争议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恶之平庸”的著名论断就像是为《德语课》写下的一个哲学注脚。汉娜·阿伦特将尖锐的矛头指向了包括艾希曼在内的整个第三帝国的臣民们,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精神未见异常、甚至可能还以厚道著称的人们,事实上正是希特勒的同谋犯,是“最终解决”命令的背后支持者。他们以默许代替抵抗,以顺从放弃了质疑和重估,从而使纳粹得以顺利地消灭600万的犹太人。
“恶之平庸”,阿伦特运用这个术语并不是要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在阿伦特看来,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将希特勒和艾希曼之流钉在一根“恶魔”的耻辱柱上,对其历史根源、社会机制以及哲学成因都不追问,那么希特勒式的恶魔就会潜伏在社会的肌体之内。一旦条件允许,这些寄生虫们就会英勇地向负责保持健康的白细胞们发出挑衅的信号,他们或者被镇压下去,或者成为一个时代潮流的风向标。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对纳粹大屠杀中普通大众的帮凶角色作了深入的分析。鲍曼的答案是:正是现代官僚体制及其相关产业促成了这样一桩不美满的婚姻。官僚体制对象的非人化、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操作准则渗入到大众的精神深处,就必然导致人类主体性的缺失。正如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所证明的,一个对实验目的并不了解的实验员可以轻而易举地按下电击的开关。
伦茨将笔触深入到政治哲学的领域,用小说的方式回应着阿伦特和鲍曼的哲学沉思。显然,不仅是德国人,所有在极权社会中曾经经历过苦难的人们,都不应仅仅将罪责的矛头简单地指向当时的某个政权或者某个“邪恶”的个人,反思自身是苦难后应该完成的一门“德语课”。■
《德语课》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许昌菊 译
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