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F官员点评历次气候大会:流泪场面成经典时刻
 12 月16 日下午,德国人史蒂芬·辛格在哥本哈根会议主会场贝拉中心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办公室
12 月16 日下午,德国人史蒂芬·辛格在哥本哈根会议主会场贝拉中心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办公室

 2000 年,COP6 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但这次会议无疾而终,图为NGO组织在张贴抗议的横幅
2000 年,COP6 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但这次会议无疾而终,图为NGO组织在张贴抗议的横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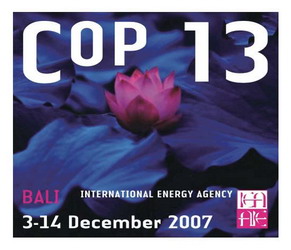 2007 年,COP13 会议印尼巴厘岛举行,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
2007 年,COP13 会议印尼巴厘岛举行,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
专访15次气候大会的见证者史蒂芬。辛格--“即便你游行了,最后还是得回家”
过去15 年,从第一次到现在的第十五次,史蒂芬· 辛格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的所有大会(简称COP)。12 月18 日,睡眼惺忪的史蒂芬在哥本哈根会议主会场贝拉中心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过去的15年,COP 会议上几乎什么都发生过,哭泣、沮丧、对峙、骂人、游行、欢笑??实在是太多了。”史蒂芬告诉记者,“无论结局如何,这次会议肯定是有史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COP会议,但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快点回家睡觉。”
文、图/ 莫书莹
德国人史蒂芬。辛格(Stephan Singer)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任职超过20年。如今的他是该基金会全球能源政策主任(Director of Global Energy Policy),也是全球同事眼中最资深的基金会工作人员。“过去15年,他参加了从COP1到COP15的所有会议。”在哥本哈根,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员工蔡涛向媒体介绍史蒂芬时,总要加上这么一句。
本报记者与史蒂芬。辛格的采访约在12月16日下午进行。当天,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COP15)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当天早上,哥本哈根会议主办方宣布:随着各国元首的到来,谈判级别将提高。此前,丹麦首相拉尔斯。拉斯穆森刚刚宣布,接替已辞职的丹麦能源部长康妮。赫泽高,出任大会主席。新的谈判会议刚开始,拉斯穆森就抛出了一份新的协议草案。
消息一出,位于哥本哈根会议主会场贝拉中心的新闻室忙作一团。
而在世界自然基金会贝拉中心办公室里,史蒂芬则对记者表示,他完全没有留意当天早晨的新闻。“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对我来挺平常的。过去的15年,COP会议上几乎什么都发生过,哭泣、沮丧、对峙、骂人、游行、欢笑……实在是太多了。”
他神情激动地谈起前一天晚上自己在贝拉中心遭遇小偷的情形。“我记得是在吃饭的时候,由于人实在太多了,我就感觉一个个子很小的人一直往我身上挤。”在COP的会议上遭遇小偷并不是多么稀奇的事情,参加了15次COP会议的史蒂芬对此事早已见怪不怪,他自嘲说在这方面自己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专家,“我立刻就意识到大事不秒,果然,在这个小个子走掉之后,我一摸上衣口袋,皮夹子已经不见了。”
后来,史蒂芬神奇般地找回了自己的钱包,里面的钱当然是没有了,不幸中的万幸是小偷没有拿走他的证件。据悉,在整个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贝拉中心已经记录了80多起盗窃事件,“偷什么的都有,皮包、照相机、录音笔、衣帽间里昂贵的皮大衣……”
但小小的盗窃事件显然已经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随着哥本哈根会议(COP15)进入最后三天的关键时刻,整个贝拉中心灯火通明,史蒂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进入疯狂工作状态。”16日当晚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员工在贝拉中心渡过的第一个不眠之夜,他们必须跟踪会议的进程,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并即时做出评估报告,并发送供媒体参考的新闻稿,“这并不算什么,昨天晚上,他们(编注:哥本哈根全体会议)也在彻夜开会直到今天早上5点。这种多边会议就是这样的,结果就好像是蛋糕上的那层糖衣(ice on the sugar),不到最后一刻是不可能有的。”
虽然已是下午,记者面前的史蒂芬睡眼惺忪。“我已经有超过24个小时没有闭眼了,现在有点神情恍惚。”他一边说一边指指手中仅存的一点健怡可乐,笑称,“全靠咖啡和这个东西,我才能保持清醒。”
他说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回家休息,“无论结局如何,这肯定会被列为有史以来最令人印深刻的COP会议,但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快点回家睡觉。”
史蒂芬点评历届COP会议
1994年3月2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生效。1995年,《公约》缔约方第一次大会(COP1)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史蒂芬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他对柏林会议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当然,那个时候外界对气候问题根本是闻所未闻,也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这个会议投入那么多的关注。”他补充道,“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出现。”
史蒂芬说,柏林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会议通过了《柏林授权书》等文件,各国同意立即开始谈判,就2000年后应该采取何种适当的行动来保护气候进行磋商,以期最迟于1997年签订一项议定书,议定书应明确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发达国家所应限制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那个时候开始,公约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就是不同的。”他这样解释。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最初的《公约》区别对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共识上天然的间隙就此形成;这预示着在之后漫长的缔约方会议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也成为每次会议唯一争论的重要议题。
在史蒂芬的心中有一张有趣的历届COP会议排行榜。比如,1997在日本京都召开的COP3,史蒂芬认为那是有史以来组织的最成功的一次会议,“整个会场中心其实非常小,参加会议的人也很多,但日本人把会场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都觉得非常舒服方便。”
史蒂芬认为,200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COP8、2003年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COP9是15次COP会议中最为无聊的会议。“一般而言,会议讨论的议题多一些,争论焦点多一些会比较有趣;但在新德里和米兰举行的会议都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米兰,最后还以没有成果结束了会议,实在是令人感到冗长无聊。”他解释说。当时在米兰,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令人吃惊的是,在史蒂芬的心目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会议不是在京都举行的COP3会议,“虽然在京都各方代表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相比之下,2000年11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COP6会议最令他印象深刻,“整个会议的过程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尤其是在最后一刻,协议突然破裂,有一些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人开始在会场中大哭起来。”他回忆说,“所有人都知道新任美国总统布什即将正式就职,他上台以后可能对气候谈判的态度更强硬,所以大家本来都是希望在海牙会议上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结果并没有,一些人开始变得非常绝望。”
在当年的海牙会议上,谈判形成欧盟-美国-发展中大国(中、印)的三足鼎立之势。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执意推销“抵消排放”等方案,并试图以此代替减排;欧盟则强调履行京都协议,试图通过减排取得优势;中国和印度坚持不承诺减排义务。各国代表对于包括碳汇、国内减量计划的补充性、遵约机制等关键协议都无法达成共识,大会主席所提出的一些建议草案也未获得欧美等国认同,主席方最后不得不宣布,一切等到2001年在德国波恩举行的COP7。
同样参加过所有COP会议的乐施会资深政策顾问安东尼,和史蒂芬一样对那次会议记忆深刻,“是的,很多人都大哭了起来,因为大家此前为达成最后的协议做了许多的工作,挑灯夜战,筋疲力尽,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有一些人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在气候谈判会议的现场,有一些流泪的场面已经成为会议历史上的经典时刻。比如2007年的巴厘岛会议,最后阶段,由于各方利益僵持不下,眼看着协议的最后期限到了,谈判又要面临延期,缔约方执行处秘书兼会议主持德博埃尔当众大哭,最后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离开讲台,这一幕让安东尼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收看电视机,等待最后结果的到来,许多人也许已经对此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看到德博埃尔哭,有些人简直是看呆了,有一些人看到他哭也哭了。”安东尼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大会主持人当众哭泣,“当然,这对于他来说也没什么不好。”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德博埃尔最后的眼泪真的起了作用,反正最后的结果是:随着美国代表在稍后妥协,巴厘岛会议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协议。
哥本哈根不是终点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中主要有两个工作地点,位于贝拉中心主会场内的是主办公室,办公室就在中国代表团新闻交流中心对面,在这里工作的多是基金会的政策研究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起码是一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研究专家,每天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这里对最新的政策进行研究,撰写报告。“你看,那个坐着的女孩主要的工作就是撰写报告,刚才那个走来走去的人是美国问题专家,门口那个聊天的人是俄罗斯通,我可以负责德国政策……”史蒂芬向记者解释说。基金会提供的报告供所有人使用,有时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成员也会特别前来问一些问题,或要一些数据。
基金会的另一个办公地点是位于市中心步行街的北极帐篷,在那里,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种宣传活动,比如前两天在这里引起众人关注的“融化中的北极熊”冰雕。每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北极帐篷内都有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他们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北极专家、冒险家、摄影师在帐篷内发起演讲,或组织集会向普通民众宣传气候变化对极地带来的影响。
这也是NGO的工作中最广为人知、也最有趣的一部分,像史蒂芬这样的政策专家也对参加这种活动充满兴趣。2001年,继失败的海牙会议之后,COP会议继续在德国波恩举行。为了向与会的各方政府施加压力,世界自然基金会准备组织一次别开生命的活动,他们设计了几个时任大国政府首脑的头套,由基金会的员工扮演成几个大国的领导,在波恩的会场外面踢足球,“寓意着这些大国领导将气候问题当足球一样踢来踢去,毫无诚意。”基金会当时尽量选择来自本国的员工扮演该国的领导人,德国人史蒂芬负责扮演施罗德。
“不要小看这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成功地将信息传达给了民众。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其实都很害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现在气候变化问题非常严峻,但如果本国的领导人无所作为,大家必然对他们很失望,那么下一次大选就肯定要遭遇挑战。”史蒂芬解释说。
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基金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想各种办法,尽量把活动办得别致有趣。更具挑战的是,每一次,留给那些负责创意的工作人员的时间并不会很长,“和我们写报告一样,他们也会密切关注会议的进程,根据会议的走向策划活动。”史蒂芬说,有的时候,这些活动的诞生不过是灵光乍现,“有一个人提议,其他人响应,这事就成了。”
不过,要在会议期间举行这样的活动,最好获得大会的同意。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中,所有NGO的活动基本上都是经过大会审批的。但偶尔也会有突发事件,比如12月16日中午一些非洲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会议中心抗议大会缺乏透明性,“在这种情况下,大会有权没收你的证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安东尼解释说。
就在安东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间隙,有一个女孩走到她面前轻声说:“六点半,搞定了。” 安东尼欣然点头。当晚六点半,刚刚抵达哥本哈根的衣索比亚总理接受了乐施会的约见,“这样的会议通常不会很长,大概10多分钟,我们跟他谈论我们的想法,衣索比亚是G77的成员国,我们希望他能向G77以及中国传达我们的想法,希望他们能为推动协议达成继续施压。”安东尼透露说。
这并不是乐施会在本次会议上约见的唯一一位国家元首,在很早之前,他们就确定了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作为约见目标,其中包括了非洲的几个国家和英国(编注:乐施会的总部在英国),“不过我们没有约美国,估计奥巴马也不可能见我们。”
安东尼告诉记者,像这样负责游说政府的工作通常在会议举办前的几年就已经开始了。“在诸如英国这样的一些地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很大,所以约见英国的官员不会很难;而另外的一些国家,我们会在会议之前就频繁地参加各种活动,尽量多认识人,或者他们也会要求我们提供一些建议。”
而对于史蒂芬来说,游说工作还需要投入私人感情,“有些时候,我们与他们做朋友,出去走走,喝杯啤酒,或是聊聊足球,关系熟了就好办事了。”
在哥本哈根会议的最后时刻,会场内人们的热议话题之一就是这次会议究竟能否达成最终协议?但已经第15次参加COP会议的史蒂芬,对于一切早已见怪不怪。
史蒂芬告诉记者,如果会议最终没有协议,世界自然基金会也暂无在哥本哈根举行任何集会游行或其他活动的计划,“即便你游行了,最后还是得回家。”对史蒂芬这种资历丰厚的环境政策分析家而言,哥本哈根会议不是起点,也绝不可能是终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依然漫长。而他现在最想做的是会议结束后立刻回家,无论这次会议结果如何,至少圣诞长假可以让他已经严重透支的身心得到暂时的松弛,“前面的路还很长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