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开启大国相对衰落的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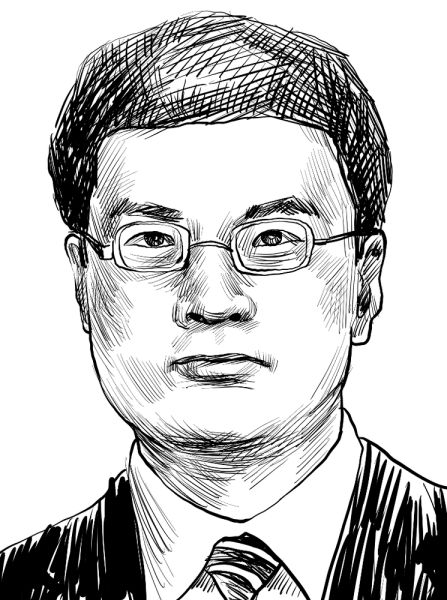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
开启大国相对衰落的世纪
达巍
十年前的2001年9月11日,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那一天将标志着世界政治意义上的21世纪正式开始。这就好像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常常被看作世界政治意义上的20世纪的始与终一样。
定义世界政治的“世纪主题”
9·11这类重大政治事件之所以会被赋予开启和终结“世界政治世纪”的地位,是因为这类事件具有重新定义“世纪主题”的作用。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维也纳体系形成,欧洲大国的多极竞争构成了19世纪世界政治的主题,并一直延续到一次大战达到高潮;在取而代之的世界政治的20世纪,也就是从1917年到1991年,大国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殊死竞争构成了“世纪主题”,上半场是革命、战争与美苏的崛起,下半场是两极格局与旷日持久的冷战。每一个“世纪主题”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并深刻影响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比如,因为19世纪的经历,很多人都认为多极化或多极世界才是世界政治的常态甚至理想状态,殊不知那既有可能只是欧洲18-19世纪的特例,而且也远说不上美好。因为20世纪的经历,很多人放不下“冷战思维”,要么觉得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早晚要“埋葬”别人。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面对秦王“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威胁,安陵君的使臣唐雎凛然陈词:“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2001年的9月11日,19个普通人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证明,“布衣之怒”同样也能产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恐怖效果。9·11事件之所以被看作世界政治的一个分水岭,是因为这一事件在这一点上区别于此前人类文明史上所有事件:也就是一小群普通人就能够打疼甚至打赢全球权势最强盛的国家。9·11事件所产生的21世纪世界政治新的“世纪主题”是,这将是一个大国权力开始相对衰落的世纪。大国的权力将日趋分散、日趋受限;诸多新行为者不断涌出。过去的主角仍在卖力演出,却越来越掌控不了台面;舞台上已站满自说自话的演员,配角、跑龙套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连台下观众都要粉墨登场。这将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纪:两极世界极尽简约的几何美感、多极世界势力均衡的力学美感都将渐行渐远。
这一新主题背后的首要推动力当然是全球化。资本、技术、人员、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扩散,不以国家意志为转移。发展中国家无法自外于全球化而取得经济发展;发达国家手里也不掌握全球化的“开关”,也同样无法控制全球化要素流动的方向与速度。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团体、个人摆脱了国家的控制,获得了过去不曾拥有的力量。
大国权势被否定的时代
近代以来,国家特别是大国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主角。国家之上虽无世界政府,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权势竞争会最终形成金字塔结构。这一态势到冷战高峰期达到顶峰。全世界被划分为美苏阵营,在两大阵营之内,秩序森严,分工明确;在阵营外,可供纵横捭阖的空间也相当有限。9·11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其他行为体虽然很难强迫大国做什么,但是这些行为体却越来越拥有一种说“不”的能力,让大国不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和控制。
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国很难真正改变其他大国的重要决定。克林顿在1993年就发现,资本有自己的逻辑,只能让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否则美国国内的企业家也不答应。今天,美国没办法不让中国建造航母,更阻止不了中国花比较少的钱,就达到以非对称能力吓阻美国军事介入的目的。同样,美国人或许更喜欢梅德韦杰夫,但是也没办法让阻挡普京的脚步或者改变俄罗斯的方向。
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国也对中小国家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小布什宣布了三个“邪恶轴心”国,打下了没有核的伊拉克,随后深陷泥潭,最后只能撤军;对一步一步走向拥核的朝鲜、伊朗,美国仍然一筹莫展。由于战争成本的上升、民众对伤亡的敏感,即便是大国对中小国家也越来越“打不起”仗。武力作为世界政治的解决方案,用武之地越来越小。同样道理, 小布什极力在中东布下民主的种子,结果被拉下来的不是内贾德,二是老朋友穆巴拉克。美国在中东经营多年,也不能保证地区形势就朝着于本国利益有利的方向发展。
不消说,9·11事件本身,更直接说明了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无奈。
醒来,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
台风从不考虑国家边界,而是横扫整个太平洋西岸。台风所到之处,不管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样都是鸡飞狗跳,手忙脚乱。不同的是,基础设施的好坏以及准备的充分与否,会决定最终灾害的结果。全球化就像这样一场热带风暴,不以国家而以全球为单位。这股风暴横扫一切国家,在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重新分配财富,在穷国和富国都造成贫富分化,并让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无产者却仍然彼此敌对;这股风暴让人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到长三角、珠三角、孟买、拉各斯、墨西哥城去,到伦敦的托特纳姆和巴黎的北郊去,有的造就新的财富传奇,有的沦为城市贫民;这股风暴让班加罗尔、开罗、德黑兰、纽约、北京的年轻人都注册了微博账号,或者“脸谱”主页。让他们在信息海洋的冲击下,相信自己有多么成功或者多么悲惨,自己的国家是多么的朝气蓬勃或者让人绝望。
在全球化造成的世界范围的大重组过程中,比过去多得多的人开始了布热津斯基所谓的“政治觉醒”过程。越来越多的人思想中曾经自足的“小黑屋”被台风掀了顶,于是他们开始发问:为什么我比我的父辈富裕这么多,或者为什么我比父辈更为艰难?为什么我的国家领导人40年不曾更换,或者为什么我的国家里政党永远在恶斗,完全不顾国家信誉或民众感受?为什么我的家乡驻有异教徒的军队?为什么欧洲人工作那么轻松?
这些“觉醒”的人,有的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视作唯一出路、“历史终结”之处;有的成为了本国民族主义的愤青,在互联网上宣泄激情;还有的则成了狂热的宗教信徒,甘愿成为一枚人体炸弹。正像9·11事件中那19个人所代表的,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更容易获得惊人的力量,并且借着媒体的影响去震撼世界。他们有的人创办自己的企业,梦想着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有的走向开罗的解放广场或者走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山区;有的人在巴黎以及伦敦的郊区趁着夜色焚烧汽车、抢砸商店。这些人都是世界政治中的无名氏:就好像我们多数人都说不出深圳华强北的山寨电子产品,究竟代表了谁的梦想、谁的血汗,我们绝大多数人至今也还不知道,在埃及究竟是谁把穆巴拉克赶下了台,并且控制着当前局势?利比亚的反对派到底由什么人组成?在美国,究竟华尔街的人是怎么玩的,就让世界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到现在也无法自拔。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要干什么,但是世界、世界政治,包括所有国家、所有的人,都在被他们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改变着、塑造着。
崛起在大国衰落的时代?
9·11事件之后的十年,“中国崛起”普遍被看作本世纪世界政治最大的变动因素之一。这一判断极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一场变动还是在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层面的变动。中国崛起,是在大国权力相对衰落的框架内部的相对崛起,是世界政治范式内部国际关系这一部分的变化。在此,“崛起”与“衰落”发生在两个不同层面,“崛起”被包裹于“衰落”之内。我们需要的,一是摆正心态;二是顺势而为。
邓小平同志定下了中国“永不称霸”的战略宣示。这不是宣传辞令,而是高瞻远瞩。这个世纪也不再是一个大国可以像19世纪或者20世纪那样,通过大量使用硬实力来称霸的世纪。美国人在经历了漫长的伊拉克战争之后,最终提出“巧实力”的概念。他们认识到,尽管硬实力仍然重要,但是单纯使用硬实力,代价可能太高、效果可能太差,可能成为“笨实力”。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我们需要吸取美国人的前车之鉴。大国越来越难以单纯通过硬实力来解决领土争议、实现分裂国土统一、保障能源安全或者迫使其他国家奉行对自己友好的政策;更无法通过硬实力来改变一个群体的认同、维持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决定全球经济的相对获益和受损者,更不用说以硬实力来控制跨国传染病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了。因此,中国的崛起,绝非重复中央帝国的辉煌,也不是复制欧洲列强、日本、苏联甚至美国的路径;崛起的中国,也只能呈现与这些霸权国家不一样的样态。对于一心重现大国荣耀的人来说,这种崛起有点“生不逢时”;但对于看重民众福祉的人来说,这种崛起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在大国权力相对下降的大环境下,大国并非无可作为。毕竟,在诸多行为者中,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仍然是最重要的行为者。关键在于,如何顺势而为,把握攸关未来国家竞争力的人口、教育、创新、环境等因素。如何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在其中不断力争上游;如何拥抱新技术,同时未雨绸缪地就新技术对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可能产生的冲击预作准备;如何释放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并实现动态中的稳定;如何让公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发展,进而产生自己的话语体系,塑造影响非国家新行为体的想法。在最后这方面,应该承认,似显颓势的美、欧仍掌握绝对优势,中、印等新兴国家在这方面则还远未崛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