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惨案源头金三角揭秘:毒品暴利与烟农无缘
 2003年1月,大旱中的缅甸境内某佤族村落。
2003年1月,大旱中的缅甸境内某佤族村落。
文/刘旭阳 图/摄影/王艺忠
2001年6月26日,中老缅泰四国在澜沧江-湄公河800多公里的航道实现自由通航。这条流经上述四国加柬、越的河流,被称作经贸“黄金水道”。因为流经老、泰、缅交界的“金三角”——世界85%海洛因的产地,这也是一条魔鬼航道。10月5日发生的13名中国船员遇害“湄公河惨案”,让这片神秘山林再受关注。中国摄影师王艺忠自1997年起便在“金三角”拍摄专题影像,他用亲身经历和镜头,讲述了那里的故事。
往年,村民一年种的粮食只够维持三个月到半年,差额靠卖大烟来弥补,但这一年情况格外恶劣。由于天旱,连最好种的罂粟都枯黄了大片。
一个山民装扮、身背照相和摄像器材的外乡人,突然来到这个位于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寒山区的小村庄,和村长艾曼攀谈起来。
村长诉苦说:“村民多半都生活困难,只有少数人家里粮食够吃。一般人家每个月只能吃干饭十天,稀饭要二十天。小娃娃每天吃三顿,我们老人只吃两顿。”
外乡人来自中国云南,名叫王艺忠,他专程来拍摄“金三角”地区居民的生存状况。
1956年出生的他做过电台文艺编辑、电视台摄像师,1992年辞职后,一直专注于用影像记录“金三角”的变迁。“1985年拿起相机玩摄影,未曾料想竟成了我不可自拔且无薪水可领的终身职业。”
专门拍“金三角”的摄影师
打小喜欢冒险的王艺忠,自从1990年徒步探险“金三角”腹地之后,就迷恋上这片神秘的山林。1997年至今,他无数次独自骑摩托车或搭车深入“金三角”,记录当地的社会变迁,特别是饱受战乱、毒品和贫困折磨的百姓。2009年7月他独立制作的纪录片《生活在“金三角”的人们》,获第16届国际影视人类学大奖。
“泛“金三角”地区种植罂粟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所有人都把‘“金三角”’当作毒品的代名词,而这也吸引我去记录它。”
泛“金三角”指泰、老、缅交界的三角地带,以湄公河及支流美塞河的汇流处为中心,总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这里丛林叠嶂、山路崎岖,人口相对稀少,但物产丰富,有金、银、宝石等稀有矿产。
一百多年前,西方殖民者带来了第一颗罂粟种子。由于“金三角”海拔多在千米以上,雨量丰沛,气候适宜,为罂粟种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当年的殖民者早已离去,但他们留下的罪恶之种却在这里生根发芽。
“金三角”是全球最大毒品产地和走私集散地,世界上85%的海洛因产自这里。它得名于外国冒险家携带大量黄金来到这里,交换“黑金”和“白金”(鸦片和海洛因)。然而,烟农的苦日子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金三角”生活着苗、瑶、克耶、拉祜、傈僳、阿卡、佤、掸(泰)等多个民族,许多人根本没有或不知道自己的国籍,也不知道边境为何物。他们其实与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同源。占佤邦人口七成的佤族延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主要种植罂粟、玉米和谷子。
当地混杂着各种地方、族群势力,以及割据和流寇武装,还有毒枭和奸商,处处潜伏杀机。在这片险恶地盘上,没有特殊背景的独立摄影家王艺忠竟能只身来来去去,本身就是传奇。没有超常的勇气和沟通能力,别说拍摄,连小命都难保。事实上,他多次在老、缅境内被抓。他说自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才拍到这些东西的。
除了冒险故事和猎奇影像,王艺忠也展现了“金三角”的另一面,揭示了那片土地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普通人在资源和权力角逐中的可悲命运。
赤贫的鸦片种植农
2001年12月,王艺忠来到位于“金三角”北部的缅甸佤邦特区时,正值罂粟花盛开季节,满山遍野都是摇曳的罂粟花。“那一次确实震撼我:那么大的一片全是罂粟花。人走进去,花比我的胸口还高。”王艺忠说。
嘎更村位于佤邦北部一道海拔上千米的山梁上,通往山村的山路崎岖不平。村民世代以种植罂粟为生。
罂粟花以白色居多,也有红色、紫色和红白相间,色彩艳丽,被称为“罪恶之花”。当时正是罂粟收割和大烟交易的繁忙时期。
王艺忠在罂粟田里遇到一位会说汉语的佤族老兵,他在帮别的烟农收割大烟。老兵是当地人,每到收烟的季节就会回来帮忙。
他告诉王艺忠:“老百姓生活只能靠种大烟,光种谷子不行。”
罂粟是当地村民唯一可以卖钱的经济作物,他们一年都在等罂粟花开放。花瓣掉落后,中间露出的花心就是罂粟果。
烟农一般将雨伞的铁骨架捆在一块,顶端磨得很锋利,每次在罂粟果上能划三道痕,让浆汁流出。划痕太深,会使汁液流得太快而滴到地上;太浅则会粘合结痂。
这些罂粟果浆汁就是烟膏,既可以当作鸦片吸食,也是提取海洛因的原料。浆汁数小时后开始凝固,烟农将它刮下来,用罂粟花瓣包好,带回家或上集市交易。这就是所谓的生烟膏。
老兵说,罂粟收割季节村里需要大量劳动力,村民会相互帮忙,主人会把一天的收获分一些给帮工者。当时的大烟价是人民币2200元一拽(相当于1650克)。
结束一天的收割,村民回到村里时,烟贩子已经在等候。他们会带来一些货物,和烟农交换大烟。
由于战争威胁一直存在,当地背枪的人很普遍。王艺忠发现,烟商的武器不仅用来防身。
“在当地,人们用一种天平来称大烟。砝码有多种多样:银元、手枪、电池、子弹、打火机、啤酒瓶盖等等。”
在嘎更村这个最底层的交易现场,烟农用一年的辛劳,积累了足够多的大烟之后,就向烟商换取一些生活用品和盖房子用的石棉瓦。
“大山把他们与现代文明割断了,没有电话、电灯。村与村之间或许可以听到鸡叫,但走过去却需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王艺忠说。
毒品暴利:与烟农无缘
商人会主动上山收大烟,大多是为了垄断收购权。他们往往会采取多种手段来控制烟农,例如按前一年的收购价,减去利息,提前支付给烟农。这样烟农不但背负起高利贷,还失去自由买卖权。村民如果想卖一个好价钱,只能长途跋涉到山下集市交易。
因为不通公路,有时要走一天,才能到山下的集市。山民们没有车也没有马,如果种南瓜或谷子,收获后很难背下山,也卖不了多少钱,而种一二十亩大烟的收获却可以轻松拿到外面去交易。它的产量和经济回报比任何经济作物都高得多,这也是“金三角”的山民离不开大烟的原因。它已经成了当地的硬通货。
“小商贩收了鸦片之后,会转手卖给更大的烟贩子。那些人再组织加工,变成海洛因四号之类。”
有些烟农根本不在乎王艺忠的存在,但他也曾接到威胁警告。“鸦片商人很忌讳你去拍。我告诉他们,我不是搞新闻的,我只是在记录历史。佤邦2005年就要禁种鸦片,作为历史资料,将来讲故事的时候用——告诉人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种植、买卖鸦片。”
在大烟集市上,王艺忠看到烟农除了用大烟换回了粮食和生活用品,还会买醉取乐。这是他们一年之中唯一可以消费寻乐的时刻;“满大街都可以看到喝醉的佤族人,有了钱他们就去喝酒。那段时间大概是烟农们最幸福的日子。”
大烟帮他们换来了粮食和短暂的欢乐。然而在罂粟收获时期之外,没有多余积蓄的他们只能继续单调的山上生活,甚至与饥饿和苦难为伴。
靠天吃饭的鸦片一年只收一季,多数被上门的商贩从600至800元的价格收走。收成好一些的,一年无非也就拿到1000多元。烟农的房屋是用几根木棍悬空支起茅草屋顶,离地只有一米来高,地板和墙用竹篾编成,好一点的才会用上木板。
高原烟农种鸦片的收入仅够糊口,但一公斤生鸦片成可制成100克海洛因,在美国黑市卖到上万美元。位于交易链源头的烟农却与毒品暴利无缘,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困顿生活,也不知道自己种植的大烟,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
对佤族烟农来说,大烟还扮演另一种角色。在缺医少药的“金三角”,鸦片被认定为一种传统药物,形成“小病靠鸦片,大病靠魔巴(巫师)”的习俗。所以当地佤族人每家都有一两人吸鸦片,最小的烟民只有三岁。
“烟农不觉得鸦片有多大的危害。他们自己也抽,还用来治病、换钱买粮食。我曾经骑摩托车经过很多原始部落的村寨,他们说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种罂粟。。”
真正懂得大烟价值、通过它获利的,一直是烟商和手握重兵的毒枭。
“金三角”艰难的戒毒之路
1897年,德国拜尔制药厂开始提取自鸦片、注册商标为“海洛因”的药物,打算用它代替吗啡,称之为“不会上瘾的万能药”。1902年,海洛因的利润占整个制药行业的5%,制作方法后来被毒枭所沿用。
1970年代,“双狮地球”牌海洛因远销欧美,在“金三角”售价为每公斤1万美元,到美国涨到20万美元。这种最纯正海洛因的生产者,就是前“金三角”毒王坤沙。
为控制烟膏生产,大大小小武装帮派开始划分“金三角”割据地盘。1990年代中期,被称为“海洛因大王”的坤沙被佤邦联军打败,向缅甸政府投降。之后,罂粟种植迅速向北扩移,鸦片高产区集中到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境内。
当地武装名叫佤邦联合军,约3万人,控制5万平方公里土地、60余万人口,是缅甸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也曾是泛“金三角”地区的最大毒品武装。
缅甸政府给予佤邦特区一定的自治权,上千公里的中缅边境线只有100多公里归缅中央政府管辖,其余由佤邦、掸邦、克钦邦等民族武装和毒枭控制。
到1990年代末期,据联合国统计,“金三角”80%的海洛因源自缅甸,而缅甸80%的海洛因又源自佤邦,佤邦于是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迫于这种压力,他们也知道罂粟不能再种下去了。”王艺忠回忆说。被《时代》周刊称为“毒品王国君主”的鲍友祥于1996年12月宣布,佤邦将在2005年实现全面禁种罂粟,并以自己的人头担保。
实现这个目标却困难重重。在高额利润诱惑下,佤邦仍有很多隐蔽的海洛因加工点在高速运转。“这种叫做四号的加工厂,一般都很隐蔽,到处都有。听说只要你一走进他们的警戒范围,就连老百姓找牛,走到那里都会被一枪打掉。”
禁令使2004年成为毒枭的最后疯狂期。佤邦执政者则要全力捣毁毒品窝点,以示禁毒决心。当年12月,王艺忠获准随同佤邦军方参与一次缉毒行动。一个连的佤邦军分两路包抄,很快控制了现场局势——毒贩不敢抗拒正规军。
“做毒品的人肯定要找很隐蔽的地方。他们装成农民,也在山上种地。当玉米地长得齐人高的时候,他们的制毒工厂已经开始作业了。”王艺忠回忆说,“一般人想不到的。远远看去,它就是一块地,上面有一些种地人住的房子。毒贩把化学药品埋在土里,房子里面就做一些简单的加工,需要什么马上挖出来用,用好了再盖起来。”
关卡是“金三角”各帮派之间的特有景观。外地人进入瓦邦辖区前,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
佤邦除了打击制毒贩毒者,还派军队不定期到各村寨清除罂粟苗,有时强制住在高寒山区的烟农向南部地区的山下移民。
“少数村民的确享受到替代种植的好处,比如下山改种橡胶或到农场做工。但大部分山民还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因为他们世代生活在高海拔的地方,过惯了亲近自然的原始生活,采野菜、打猎。那里也不适合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他们也不愿下山到农场当工人,所以仍过得很穷困。”
此外,他们不认为鸦片是毒品,在他们头脑里,没有鸦片就没饭吃。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要劳动、投资和技术,而山民一样都不具备。此外,种罂粟无论收成好坏,鸦片都能卖出去。生产粮食或经济作物却要担风险。加上当地信息闭塞,一些人思想僵化,政府一旦宣布禁种大烟,他们便跑进深山种植。
王艺忠发现,在武装帮派控制区内,毒品种植已得到控制,但在它们与政府军交界的“两不管”地带仍有罂粟种植。
“佤邦等帮派的管辖范围内,会有法律法规打击毒品种植,比如种植50棵罂粟以上的人要坐牢。如果发现有村民种罂粟,不仅要法办本人,村长、乡长也要免职、罚款甚至坐牢。但缅甸其他地方生产的大烟、罂粟籽、壳等毒品返回到佤邦销售的现象仍然存在,缅甸政府控制区内仍有不少人在种罂粟。我曾在政府控制区内一座玉石开采场周边看到大面积的罂粟地,据说面积还有扩大的趋势。”
“虽然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曾向“金三角”的山民提供粮食援助,但由于当地局势不稳定,成果远不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好。此外,当地政府非但不会援助这些百姓,甚至还向他们来征粮,根本不管百姓自己够不够吃。佤邦政府曾免除前烟农两年的交粮任务,但当地乡镇管理部门需要额外粮食招待军干部什么的,所以照征不误,导致前烟农仍过得很贫困。”
“湄公河惨案”的头号嫌疑犯
“湄公河惨案”发生时,王艺忠正在佤邦拍专题片。
“听说这个消息,我虽然震惊但并不意外,因为这不是湄公河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在湄公河的中缅泰沿岸,一直有一股很凶残的匪徒,经常劫持、敲诈和袭击各国货船,只不过这次袭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惨重伤亡。”他说。
2008年2月,王艺忠与一伙江匪擦肩而过。据报道,当时一支不明武装袭击湄公河上游中国段的一艘巡逻船,3名中国警员受伤,后来查实为当地有名的匪徒瑙坎所为。“湄公河惨案”发生后,几乎所有舆论都直指以瑙坎为首的匪帮。
“当时,我要和一些中国农业专家一起乘船,沿湄公河到“金三角”的佤邦南部地区考察,但我因有事耽误了两天,便选择在湄公河的这一段由陆路前往。到达目的地时,就听说他们在那片水域遭到武装袭击。
“事发后,据佤邦保安队长回忆,当时事发突然,中方的船刚启航不到50米,就遭到两艘快艇袭击。佤邦方面的人不多且都在岸上,没来得及回击。江匪在中方船上留下五十多个弹孔后悻悻离开,造成我方两名人员受伤。
此后这股江匪越来越猖狂,在湄公河缅甸的索累码头到泰国清盛港一带,经常袭击过往商船。这次“金三角”惨案我觉得很可能就是瑙坎匪帮所为。他们经常劫持过往商船,把毒品从缅甸经湄公河运往泰国,也许是因为被劫持船员在进入泰国水域时进行反抗才被匪徒杀害。江匪和湄公河上的船家没有仇,袭击不存在报复中国人之类的目的。他们除劫财、贩毒外,也故意给缅甸政府制造一些麻烦。”
瑙坎何许人也?佤邦两位高层部长曾告诉王艺忠,以前坤沙的部队中有一个不愿投降的头目叫约色,率领数千士兵占据泰缅边境一带。瑙坎就是从约色队伍中分离出来的,他会把非法所得的财富分成三份,一份自己留下,另一部份分给部下,第三份献给约色,以换取对方的支持,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为非作歹。
瑙坎的团伙与其他武装帮派有区别:与瑙坎帮派接壤的是掸邦第四特区,两者民族相同。瑙坎匪徒没有固定营地,一遇攻击立刻遁入山林或解散回家务农,你根本抓不住他们。和正规帮派不同,他们的势力范围没有固定边界,外人也不知道其人数到底有多少。
据泰国媒体称,瑙坎拥有一支数百人的武装,主要以掸族和拉祜族为主,他本人就是掸族。他们以掸邦东部崇山峻岭为基地,凭借重武器和武装快艇,在湄公河“金三角”河段缅、老间约50公里的水域干贩毒、抢劫、杀人和绑架等勾当,还利用缅、老、泰交界河段的执法漏洞,对过往船只收取保护费。在其侵扰下,从中国关累港到泰国清盛港间的263公里湄公河道,变成一条让人胆战心惊的死亡航线。
由于泰国采取有效的安抚手段,其境内大部分“金三角”武装都被招安,成为合法泰国公民。但在缅甸境内河段,武装匪徒仍然猖獗。
“金三角”是否还有希望?
经过多年扫毒,“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但近年来其他种类毒品的交易额却呈上升趋势。联合国近期发表的报告显示,东亚和东南亚是包括冰毒、摇头丸在内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毒品重灾区。2008至2010年期间,老、缅、泰和中国缉获的这类毒品增加了4倍。
与传统毒品相比,这种毒品加工更便利,成本更低,成为毒贩的新选择。新型毒品的生产又带动了传统毒品生意,“金三角”罂粟种植出现回升势头。2010年缅甸共生产580吨鸦片,同比增加20%。
2009年泰国警方搜缴摇头丸2700万粒,2010年约4000万粒,今年仅前8个月就搜缴3280万粒。目前,泰国“瘾君子”约130万人,每千人中就有19人,远超出千分之三的国际指数。
“金三角”毒品进入泰国分为水陆两路,陆路经泰缅边境的山区运输,或以大巴、旅游车等交通工具运抵泰国;水路走湄公河。因此,在湄公河上跑航运的中国货船,就被毒枭们盯上。
对于“金三角”乃至湄公河沿岸的未来,王艺忠不无忧虑。尽管昔日的大毒枭、大军阀已经兑现禁毒诺言,但长期割据、地方与中央的军事摩擦、地下毒品加工厂的再次兴起,都让“金三角”仍然脱不开“毒三角”的魔咒,
在王艺忠在他拍摄的一组佤邦童子军照片下面写道:“佤邦联合军为应对战争的突发,急招数千名5至12岁的童军上前线受训。‘本应上学读书的孩子你们却拿来当兵,这些还没有抢高的孩子他们能打仗吗?’本人询问佤邦官员。‘没办法,不是我们想打仗,你要怪就去怪老缅吧。’官员停了停:‘难道这些孩子打出去的子弹杀不死人吗?再说我们也不会先开第一枪。这些童军通过我们的正规训练,两年后都将成为合格的军人。我们老兵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一直在做有关‘金三角’的图片故事和拍摄专题纪录片,无论这里的百姓生活变好或变坏,我都会关注下去。我人在那里的时候,会不断发现新东西,需要你去纪录它。”
年近60的王艺忠,仍在不断地往那里跑,把镜头对准把山掏空的宝石和玉石采矿场、地狱般的矿洞、被监视和搜查身体每个孔洞的女工、卖淫、赌博、森林砍伐、悲惨的象奴……
尽管“金三角”的苦难让人绝望,王艺忠还是看到了一线改变的机会。经过10年的走访、调查和观察,他在佤邦南部军区的管辖范围,甚至在佤邦北部部分地区,发现了整个“金三角”的典范和希望。
当地民众在高度统一的领导下,一直坚持走替代发展的道路。“10年来我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军民作出的天翻地覆变化。如今,农业、畜牧业、矿业、工业都取得了可喜成果,当地百姓也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实惠。”王艺忠说。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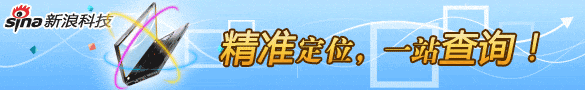
 快速增长3CM秘密
快速增长3CM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