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推“记者还乡”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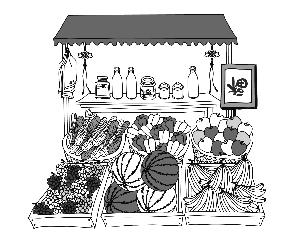 |
春节,我们回到故乡。看看乡景,听听乡音,感受乡情,那里,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吗?
今天,你或许已经离开故乡,重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故乡的烙印还在吧?
即日起,本报推出“记者还乡”系列报道,我们以记者的眼光,打量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
故乡的变或不变,都是宏大家国图景的一个注脚。
故乡地: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隔浦镇
家乡话:
“从广东坐高速铁路回家的打工者,大多数人都是泥瓦匠,其他那些打工的人都嫌票价贵。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大学生,在知道我的收入后心理不平衡,说自己读了十几年书,挣的还不如我多。”
———二表哥
县城里,去年在街道飞驰的电麻木(三轮摩托)已经绝迹,代之的是公共汽车,一块钱能够方便到达县里大多数地方。
镇里的杂货店将摊位摆到了路边,日常生活用品大多都能买到,只是有些商品的价格比大城市还贵。
楼房已经越来越普遍,平房和瓦屋已经很少……每一次回家过年,总能看到家乡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渐行渐远。
留守者
以前求温饱现在求收入
我家所在的湖北省云梦县,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县,每平方公里近千人。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隔浦镇,又是云梦县人口密度最大的镇。因为资源贫乏,工商业并不发达,外出务工、做生意的人较多。
平常出没于村子里的,大多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在家的青壮年男丁极少,曾经和我下过多年围棋的棋友想平是其中之一。
他拿着一个菜篮子,到菜地里挑菜。妻子和女儿每年都出去打工,儿子正在武汉上大学。“我在家也不是以种地为生,经人介绍在邻村的调味品厂打工,每月工资有2200块钱,春节的时候,老板还发了800块年终奖。”想平说。
尽管留在村里的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但是荒地很少。
母亲跟我说起,在家种地的人,吃喝不用愁。
很快,母亲的话在我连襟那里得到了佐证:体强力壮的夫妇俩辛苦一年,养了一头母猪,加上种地的收成,一年下来毛收入五万元,“粮食价格虽说涨了一些,但是远远跟不上化肥、农药涨价的速度。除去投资和必须的花费,纯收入没有多少。”连襟从以前的求温饱,到了现在的求收入。
但是,他显然还有顾虑。两个儿子虽说在外打工,但是,大儿子每年并没有存下多少钱,这让他不得不为儿子将来的婚事储存一笔钱。
打工者
农村人想住到县城
长期以来,老家外出做泥瓦匠的人很多。曾几何时,一位族兄从东北回来,因为没赚到钱,在火车从黄河经过时,一怒之下把砌墙用的泥刀从窗口扔了出去。
近年来,由于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发展迅速,泥瓦匠的收入节节攀升。
我家隔壁的堂叔说,他们夫妻俩去年就在东北挣了四五万元。不过,有一件事让他放不下。
去年,他儿子从学校骑车回家时,被一个精神病人刺伤。这事让他很是担心,堂叔决定,今年让妻子在家照顾儿子,自己一个人上东北,“反正我就这一个儿子,让他平安长大就好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与我们村里人去东北打工的情形不同,两位做泥瓦匠的表兄每年都去深圳。大表哥手艺高,夫妻俩去年净赚了七八万块,二表哥去年挣了三四万。
大表哥的儿子计划今年结婚,大表哥首付了10万元,在邻县安陆县城买了一套两室一厅,近100平方米的房子。大表哥说,“剩下的10万元按揭,贷款期限是10年,我准备让他们夫妻俩自己还。二儿子将来结婚,我计划在县城也这样买一套房。”
早在前三年,做泥瓦匠的族兄就以他的观察,说出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农村的人想住到县城;县城的人想住到地级城市;地级城市的人想住到省城;省城的人想住到北京上海;北京上海的人想住到外国。
未来
大不了回来种地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乡亲们30年前就到武汉做蔬菜生意,但是,微薄的收入和艰辛的积累,使得在武汉买房只是一个奢望。
赚钱较多的四五户人家,已经在云梦县城买了房。其中,一位堂叔五六年前,花9万元买了一套三室一厅。如今,这套房可以卖到30万元左右。这种升值让村里人很是羡慕,“他长了后眼睛(即有先见之明),该他得邪(即获得利益)。”
二表哥谈到自己收入时很是得意,“从广东坐高速铁路回家的打工者,大多数人都是泥瓦匠,其他那些打工的人都嫌票价贵。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大学生,在知道我的收入后心理不平衡,说自己读了十几年书,挣的还不如我多。”
而二表哥同时又对于自己的收入与房价的高企不成比例,感到不平。“我们天天给别人粉刷房子,装修房子,这些年来,至少在一千多户人家干过活。可是干了这么多年,存下的钱想在大城市买房简直就是做梦,一年的收入,在大城市最多只能买一个厕所。”
兄弟俩近10年来虽说存了一些钱,但是有一些文化的他们,担心好景不长:“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我们就会失业。”但是,他们也都同意我的劝解,“大不了回来种地,吃过这么多苦,干什么都能谋生!”他们还告诉我,村里春节前刚刚通上了自来水,“以后我装一个热水器,洗澡就方便多了。”
□本报记者 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