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丁韪良将国际法引入清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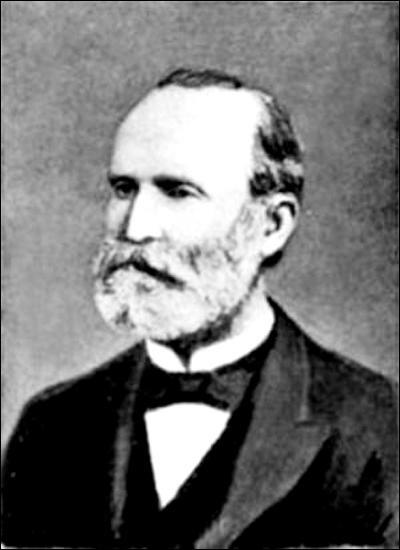 |
《万国公法》的中译本出版于1865年,译者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关于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原因,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譬如,张燕清认为它是西方对华政策的产物,即“丁韪良向近代中国社会推荐国际公法,其主观意图在于让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秩序,进而迷信西方主持的所谓国际正义,力图培植中国人的幻想并使之放弃反侵略斗争。”(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7期载《丁韪良与万国公法》);张用心则将其归结为清政府对外交往的需要,即“《万国公法》的出版,与其说是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产物”(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载《〈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但学界对丁韪良在该中译本出版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尚未引起讨论。有鉴于此,略抒管见。
1858年,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清朝大臣耆英与列维廉因为外交礼节发生争执:“他(耆英)建议列先生预先要排练一下接旨的仪式。但列先生拒绝了。耆英补充说:‘您得下跪受书。’列先生回答:‘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但皇上就是上帝!’耆英说”(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丁韪良由此认识到清政府对于近代西方外交礼仪的无知。由于不懂国际法,清政府此时也忧心忡忡:“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须时日。臣等因于各该国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欲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筹办洋务始末》,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页)而对于是否要把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的问题,来华的西方人的认识也不一致。当时,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得知有人欲将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时,就扬言:“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花甲记忆》,第159页)正是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丁韪良敏锐地感觉到清政府有了解、掌握国际法的需要,因而萌生了翻译、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
而丁韪良较高的汉学水平又为翻译并出版《万国公法》提供了基本前提。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有其专门的大量术语。19世纪的中国法学所运用的专门术语与西方法学是大不一样的,如果翻译者对中国文化没有精到的把握,将近代西方法学的话语系统用汉语表达出来,将是很困难的事情。从1850年到1855年,丁韪良不但系统学习了《尚书》、《易经》、《诗经》、《春秋》、《周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而且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有特别推究,“学土音,习词句,解训诂,讲结构。不数年而音无不正,字无不酌,义无不搜,法无不备。”(丁韪良著:《天道溯源》,伦敦圣教书类会社1880年版,第1页)丁韪良在研习中文的过程中,曾以欧洲语言中的元音作为基础,加上其他一些变音符号,编出了一整套音标。他将每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如把ning拼为n-ing,hang拼为h-ang,long拼为l-ong。根据这套拼音系统,丁韪良能够复制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语,不久便能与人交流。来华6个月后,丁韪良已经能够用汉语布道。以现在的标准看,丁韪良创造的这套拼音系统还是相当科学的。“当地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学了几天就能够阅读,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学汉语,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这一点。”(《花甲记忆》,第29页)在学习一年半汉语之后,丁韪良便用汉语撰写了他的第一首赞美诗。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丁韪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在深化,同时也赢得了同他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尊重。据丁韪良自己的回忆,“当时懂得中国学问的人甚少,所以当恭亲王了解我熟知中国的作家、作品后,立即对我另眼相看,并给我起了一个‘冠西’的雅号。此后许多中国人都尊称我为‘丁冠西’。”(《花甲记忆》,第199页)后来的驻美公使陈兰彬也称赞丁韪良:“居中土久,口其语言,手其文字,又勤勉善下,与文章学问之士游,浸淫于典雅义理之趋,故深造有得如是。”(吴尔玺、丁韪良译:《公法便览》,同文馆聚珍版》)
丁韪良于1863年5月完成了《万国公法》的翻译,1865年初便以刻印本行世,这与丁韪良与中外官员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能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丁韪良曾以嘉宾身份参加了李鸿章七十大寿的庆典,与恭亲王奕的交往也“频繁而亲切”(《花甲记忆》,第234页)。奕曾指派四名高管协助丁韪良修订《万国公法》,并允诺一旦完成,即用政府的名义刊印此书。《万国公法》即将出版之际,董恂为之欣然作序:“是书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云尔。”(《万国公法》,同文馆聚珍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曾将丁韪良引荐给总理衙门,并向他保证“将此书提交给清政府”(《花甲记忆》,第150页)。此外,《万国公法》的出版还得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支持。赫德鼓励丁韪良将翻译工作坚持下去,认为“这本书会被总理衙门接受的”(《花甲记忆》,第159页),并承诺从征收的海关关税中提取白银500两予以资助。
综上所述,丁韪良敏锐地感觉到清政府对于国际法的需要,乃是他翻译出版《万国公法》的基本动因;而较高的汉学水平又是其翻译并出版《万国公法》的基本前提;丁韪良的广泛人际关系是《万国公法》得以迅速出版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译本出版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