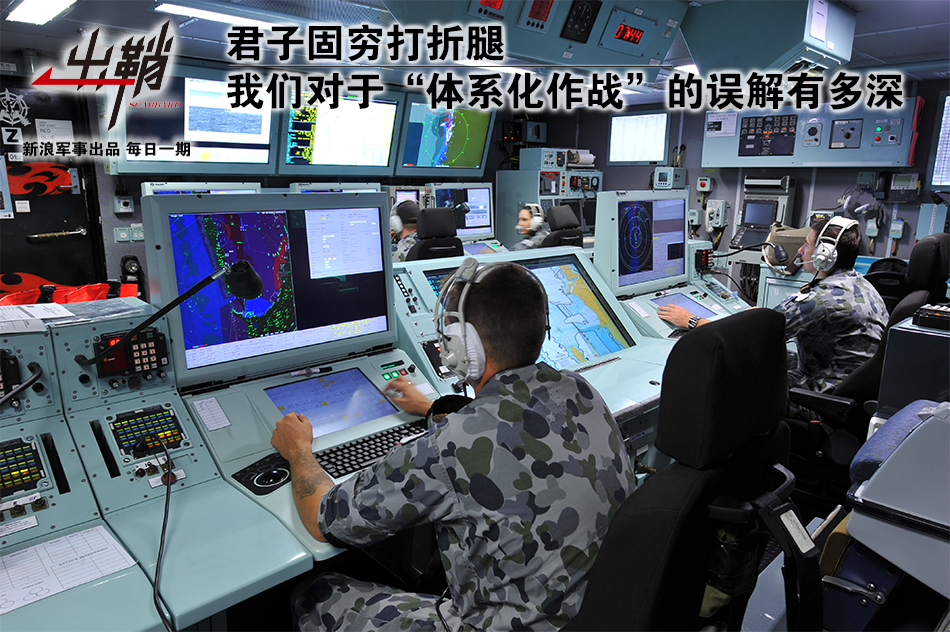原标题: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013年12月,几内亚的梅里昂杜村,一个两岁的男孩,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随后,病毒席卷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亚。2014年至2016年,几内亚确诊3811,死亡2543;塞拉利昂确诊14124,死亡3956;利比里亚确诊10675,死亡6809。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横行,成千上万的人感染并死去,平均病死率达50%。
继《血疫》之后,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带来新作《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直击了这场席卷西非的瘟疫,以及回顾了1976年的那场危机。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来自作者数以百计的个人访谈和数年来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档案及原材料的研究。书中的角色鲜为人知。然而,在这场世人生平仅见的最具毁灭性的迅猛瘟疫之中央,始终能窥见他们的行动和选择、生存和死亡。希望读者能够以此为窗口,看清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埃博拉流行病更像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新发病毒跳出生态系统后造成的震荡波。病毒在人群中自我增殖,吞噬生命,遭遇人类这个物种的反抗,最终偃旗息鼓。然而,下一个震荡波会是什么?
假如一种四级新发病毒扩散到北美或任何一个大陆的百万级人群之中,医院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么多的患者并照护他们?假如感染人数超过百万,流行病学家是否有能力追踪并打破传染链?世卫组织认为,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显示,“对于应对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和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世界并没有做好准备”。这似乎也适用于2020年我们面临的新冠疫情。
在西非疫情中,新感染的医务人员人数居高不下。截至2014年底,有近700名卫生工作者受到感染,其中半数以上死亡。这种病毒是个真正的恶魔,它随着忠诚和爱的链条传播,正是这样的情感将医院的医护人员彼此连接在一起,最终连接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他们是挡在病毒和你我之间的一道薄弱的防线。
埃博拉战争不是通过现代医药打赢的。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中世纪战争,交战的一方是普通人,另一方是一种生命形式,它想将人类的身体用作求生工具,活过亿万年的时光。为了战胜这个非人类的敌手,人们必须去除自身的人性。他们必须克制最深沉的情绪和本能,撕开爱与情感的羁绊,隔离自身或隔离他们挚爱的亲人。为了拯救自我,人类必须变成怪物。
非洲西部不存在类似于刚果盆地的远古法则那样的习俗。然而在2014年,人们与埃博拉的交战法则完全就是1976年让-弗朗索瓦·卢泊尔医生站在市场案台上推荐扎伊尔人民使用的方法。病毒通过接触体液传染。假如你学会识别症状,不去触碰体液,避免接触出现症状的那些人,放弃处理死者,你就能保住自己不被感染。
现在,守护在病毒圈大门口的战士明白他们面对的敌人强大得可怕,这场战争势必旷日持久。他们的许多武器终将失效,但另一些会开始发挥作用。人类在这场战斗中占据一定的优势,拥有病毒所缺少的某些要素,其中包括自我意识、团队作战的能力和愿意牺牲的精神。

《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理查德·普雷斯顿 著
为救婴儿忘却病毒的卢泊尔医生
摘自《血殇》,有删节
(美)理查德·普雷斯顿 著 | 姚向辉 译
米莉亚姆修女在恩加利埃马医院渐渐死去的时候,一位天主教修女联系了金沙萨一位名叫让-弗朗索瓦·卢泊尔的医生,请他帮忙研究这种疾病。卢泊尔医生当时三十八岁,领导着比利时政府在扎伊尔的医疗救助组织:热带医药基金会(简称Fometro)。卢泊尔个子不高,尖下巴,蓝绿色的眼睛,脸膛被日晒雨淋变成了热带常见的棕褐色,有一头浅棕色的波浪卷发,暴脾气声名在外。卢泊尔的家在商业区,是姆弗穆卢图努大道上一幢刷白的灰泥房屋,他和妻子乔西安·维索克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住在一起。作为比利时医疗组织的领导者,他管理着在扎伊尔各处工作的约200名医生。
卢泊尔定期在扎伊尔各处巡视,管理他手下的医生,探访乡村地带的小医院,治疗病患,提供建议,帮助医务人员完成他们的工作。每次他来到一所乡村医院,首先梳理药房的工作,然后开始给患者看病。另一方面,消息会在附近的村庄传开,说有一位名医来了,病人会来到医院寻求救助。他们会从50英里外赶来,有的走路来,有的被家人用刚果轿子抬来。卢泊尔用手头能找到的各种药物和器具治疗病患,从分发抗寄生虫药物到偶尔为之的接生,他什么事情都做过。让弗朗索瓦·卢泊尔就是所谓的
丛林医生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红色区域”。只要血检呈现出埃博拉阳性,就不允许患者离开红色区域。
作为丛林医生的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卢泊尔也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他追踪昏睡病的爆发情况,记录统计学数据,努力阻止爆发。昏睡病是一种难以治疗的致命疾病,通过采采蝇的叮咬传染。昏睡病能够荡平一整个村庄。每次这种疾病传进一个村庄都会杀死许多居民,剩下的幸存者有时候会放弃村庄,搬去其他地方居住。
卢泊尔向众人推荐名为远古法则的传统方法,使用这套方法,人们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未知疾病的侵害。正如卢泊尔在日记里写到的:
出于偶然,我得知许多个世纪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在用习惯性的经验方法处理另一种疾病:天花,它既致命又极易传染,现已被根除。每次天花爆发,疑似患病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就会被送进在村庄外建造的一间茅屋。茅屋里备有饮水和食物,村民被禁止与病患接触。经过一段时间后,假如茅屋里的人活了下来,会得到允许返回村庄。假如茅屋里没有了生命迹象,村民就会焚毁茅屋,连同尸体付之一炬。
卢泊尔、拉菲耶和布阿萨乘直升机在邦巴区来回穿梭。三位医生走访了17个小镇和村庄,在每个降落的地方用当地语言向民众宣讲,提供关于这种病毒的信息。
记住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不要触碰患病者。不要拥抱死者。死后立刻埋葬。遵循远古法则。
然而,当卢泊尔遇见需要急救但可能感染病毒的婴儿时,那一瞬间他忘记了自己,出于本能为婴儿做了人工呼吸:
萨拉特氏手术
扬布库传教区
1976年10月21日,上午5点
卢泊尔听见敲门声就下了床。天色尚黑,黎明未至。他打开门,看见杰诺薇瓦修女站在门口。她说有个正在分娩的女人被送进医院。情形看上去不太好。
卢泊尔穿上衣服,拿起他的医疗包,跟着修女走向医院门口的空地,女人躺在担架上,家庭成员围着她。他用手电筒照亮她,发现她的眼白呈鲜红色,弥漫性出血。这是这种病毒的临床特征之一。她汗出如浆,病情危重,发着高烧。她显然濒临死亡。
卢泊尔看着这个女人,内心一时间充满恐惧。她在发高烧,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他心想。有两条生命岌岌可危。通常他会立刻做剖宫产手术。但是,被那种无名病毒感染的怀孕女性的传染性很可能极强。切开母亲的身体会产生大量血液。助产士比埃塔修女的遭遇就是例证。她为濒临死亡的病重孕妇接生后感染了病毒。
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没有携带病毒。假如她没有携带病毒,他就不能带她进医院,切开她的皮肤,将她的血液系统暴露在病毒之下。他绝对不能在产科病房做任何手术,因为分娩台上有血,产房里到处扔着沾血的绷带和棉塞。手术室的情况同样糟糕。
“医院里到处都是病毒。”他对杰诺薇瓦修女说。
他决定在室外做手术。但他还是需要手术台。他问杰诺薇瓦修女能不能从厨房或餐厅搬一张桌子出来,放在外面的门廊上。修女匆忙离开后,他穿上外科手术的防护服——棉布罩衫、帽子、棉布手术口罩、橡胶手套。病毒通过体液传播。他必须确保孕妇的体液不接触他的皮肤和身上所有的黏膜组织,尤其是眼睛和口腔。
杰诺薇瓦修女带着两个男人搬来了一张桌子。他们把桌子放在门廊的一个电灯泡底下。男人们把女人用担架抬上门廊,然后滑到桌子上。她似乎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两个男人里有一个是护士,名叫苏卡托·曼德佐巴。
天花板上的灯光不够亮。卢泊尔请修女和苏卡托护士用手电筒照亮产妇的生殖器区域。在手电筒的光束下,他看见产妇阴道口周围的皮肤上有黏液和少量血液。他将两根手指伸进产道,触碰张开的宫颈。他能摸到胎儿的臀部或足部卡在了宫颈里。胎儿处于臀位,身体侧躺,被卡在产道里。

塞拉利昂:胡玛尔·汗,一位民族英雄的死亡。在西非疫情中,新感染的医务人员人数居高不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截至2014年底,有近700名卫生工作者受到感染,其中半数以上死亡。
他用碘酒清洗产妇的骨盆前侧,直接给手术区域注射局部麻醉剂。她能够感觉到医生在切开她的身体,她肯定能感觉到,但局部麻醉剂足以止痛。他请杰诺薇瓦修女和苏卡托护士按住她的手臂和膝盖,一定要紧紧抓住。他做萨拉特切开的时候,她有可能扭动或挣扎,而他下刀时必须非常谨慎。
修女抓住产妇的双臂,苏卡托护士抓住她的膝盖,抬起来,直到腿部弯曲。卢泊尔用右手拿起手术刀,左手食指按住产妇的骨盆前端。他轻轻移动指尖,感受骨骼的结构,最后在骨盆前端找到名叫耻骨联合的位置。这个位置很硬,位于阴部正上方,臀部的骨骼在此处汇合连接。髋骨在此处并不合为一体,而是形成关节,被一块厚实的软骨连接在一起。
他用手指找准位置后,请苏卡托护士拉开产妇的双膝。对她的双膝轻柔用力,他告诉苏卡托,但必须抓紧,防止她突然挣扎。
苏卡托开始拉开产妇的双膝,卢泊尔将手术刀的刀尖垂直插入髋骨前部连接处的软骨,也就是耻骨联合。然后他开始切开软骨,沿垂直方向在肚脐和产道口之间扩大刀口。他轻轻地运动刀柄,将手术刀向下插进软骨,鲜血涌出刀口,流向产道口。她没有挣扎,她只希望孩子快点出来。他继续用手术刀轻轻锯开软骨,与此同时侧耳倾听。
突然,他听见仿佛橡皮筋断开的一声脆响。这是软骨断开的声音,于是骨盆打开。听见这个声音,他立刻停止切开软骨,让苏卡托停止拉开双膝。他留下少量软骨没有切开,它将髋骨松垮垮地连在一起,就像一截胶带。要是他不小心切断了软骨,她的骨盆就会散开。
胎儿松脱了。他的一只手伸进宫颈,把住胎儿的后脑勺,将胎儿掏了出来。
随着婴儿出生,羊水和黏液涌出产道。他抓住脐带,将胎盘拉了出来。他剪断脐带,抱起婴儿,仔细查看。
婴儿没有呼吸。
卢泊尔扯掉手术口罩,俯身凑近婴儿,用他的嘴盖住婴儿的口鼻,把一口气吹了进去。他轻轻地吹了几口气,一点一点地扩张婴儿的肺部。要是他吹得太用力,就有可能撕裂肺泡。
杰诺薇瓦修女和苏卡托护士后退一步,瞪着卢泊尔。他们看见震惊的表情慢慢爬上卢泊尔的脸。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在干什么。但他的嘴依然没有离开婴儿的口鼻。婴儿的胸膛挺起来了,肺部充满了气体;卢泊尔把婴儿从面前拿开。婴儿哭了,呼出卢泊尔的气息。他活着。
杰诺薇瓦和苏卡托惊恐地盯着卢泊尔。他的口鼻和面颊糊满了黏液、羊水和从切口或产道流出的血液。这些液体无疑进入了他的口腔。
“医生,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修女轻声说。
“现在我知道了。”卢泊尔答道。
他似乎吓得无法动弹。旁观者见到各种体液在他脸上反射光线。他把孩子举在面前,继续盯着看。他遵循的是标准流程。给新生儿做了心肺复苏之后,医生应该观察婴儿三分钟。这是为了确保婴儿能继续自主呼吸。假如婴儿的呼吸再次停顿,医生就必须重复人工呼吸。
除了观察婴儿,在必要时重复人工呼吸,卢泊尔还能怎么办呢?这会儿他想自救已经来不及了。卢泊尔无计可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改变他已经做出的选择。他接生的次数太多,为许多婴儿做过心肺复苏……
那一瞬间他忘记了自己,出于本能采取行动
。卢泊尔医生很清楚他刚刚做了什么,因为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我刚刚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那天吃早饭的时候,卢泊尔很沉默。他似乎没有向调查组里的其他人提到他做了什么。也许他觉得很尴尬。他跑遍邦巴区宣讲,警告人们不要触碰呈现出那些症状的人,却把整张脸扎进了有可能含有病毒的体液。至于杰诺薇瓦修女和苏卡托护士,他们对卢泊尔的失误保持缄默。

利比里亚:缺乏足够的治疗床位是病毒失控最强有力的证据。到9月第一周结束时,随着病例剧增,首都不堪重负,已无力应对疫情。有时一家人坐着出租车满城四处寻找治疗床位,但根本找不到任何床位。
到调查结束时,流行病调查组探访了大约6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其上的17万居民。这种疾病的病例为数极少。病毒已经几乎消失。调查组找到九名患者,其中五名很快死去。他们还找到另外五名疑似患者,另有一人的血样显示他受到过感染,但活了下来。调查人员开车走访所有村镇之后,发现邦巴的这场爆发在国际调查组抵达时已经几乎结束。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阻止了这种病毒。
既然国际调查组没有阻止病毒,那么是谁呢?又是怎么做到的?
证据表明,是邦巴区的居民自己阻止了病毒。这件事发生于他们得知这种疾病的辨别方法和人际传播途径之后。卢泊尔、拉菲耶和布阿萨这三位医生扮演了其中的关键角色,因为他们先前走访邦巴区时向人们灌输了这些知识。
这是极其难以完成的任务。远古法则相悖于普通人保护与照顾亲人的本能。病毒毫不留情,为了击败它,人类也必须变得毫不留情。他们必须约束自己,不去照护病人。他们必须切断与疑似患病者的一切联系。他们必须停止按照传统方式向逝去亲人表达哀悼之情。邦巴区的人们做到了这些。他们驱逐患者全家,不照护他们。尽管很多人哀悼亲人的逝去,但似乎放弃了睡在死者身旁和拥抱死者的习俗。在几个案例中,他们烧掉整幢房屋。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对扬布库传教区医院敬而远之。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注意到疾病以医院为中心扩散,因此假如你不想得病,就该尽量远离医院。让弗朗索瓦·卢泊尔敦促人们做出最艰难的选择,告诉他们必须用铁石心肠对待病人和弱者,自己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因为一个婴儿而失去理智。

扫描左侧二维码下载,更多精彩内容随你看。(官方微博:新浪新闻)
推荐新闻
- 【 新闻 】 李克强:中国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
- 【 军事 】 C802为何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一枝独秀
- 【 财经 】 请杨幂赵薇代言椰汁要花多少钱?
- 【 体育 】 曝中超新赛季仍保留升降级
- 【 娱乐 】 仝卓自曝高考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 教育...
- 【 科技 】 FB等社交平台“打标签”是否必要
- 【 教育 】 整天刷手机的家长培养不出爱读书的娃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4000520066
举报邮箱:jubao@vip.sina.com
Copyright © 1996-2020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