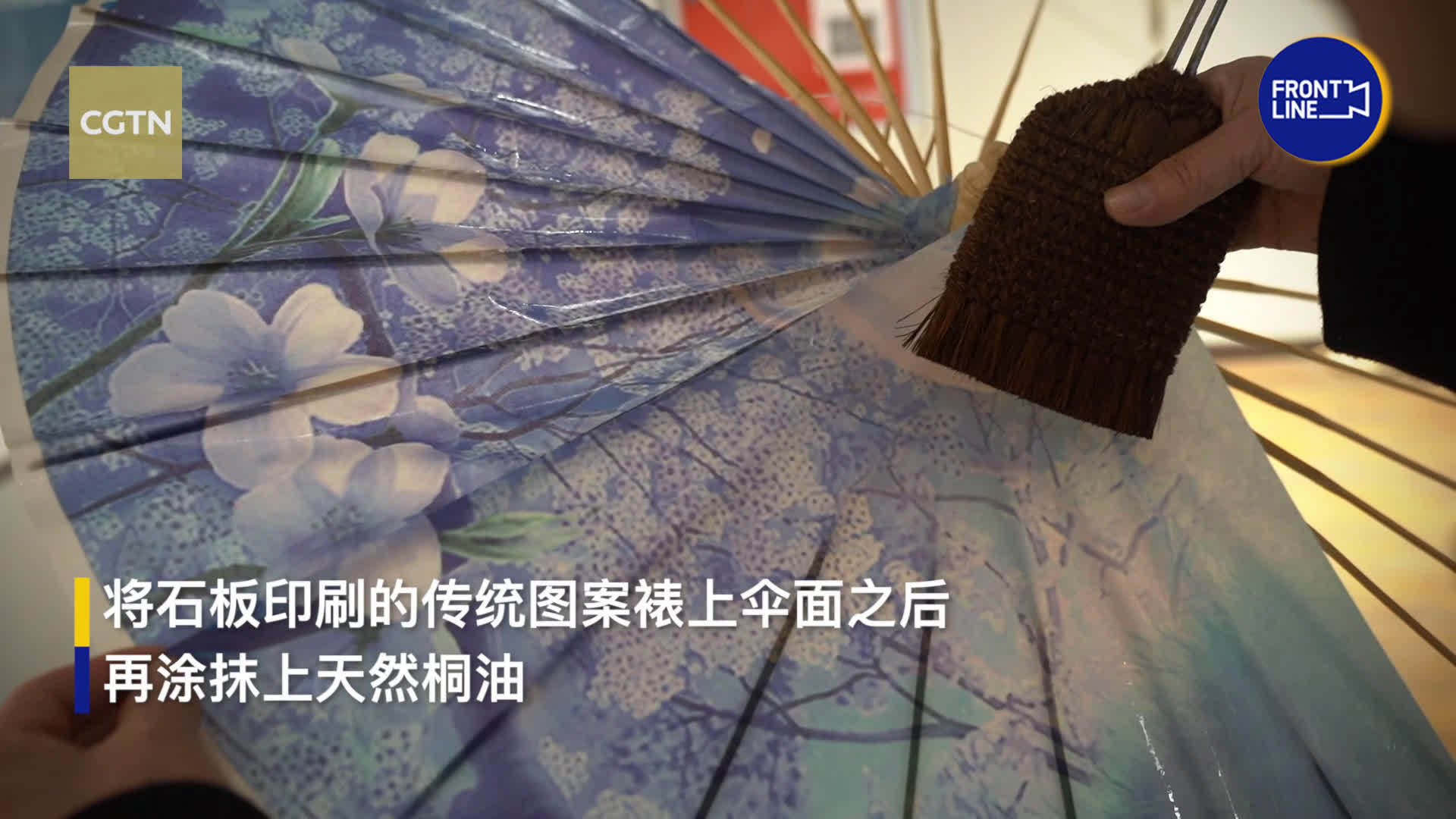华语著名影星王羽于4月5日离世,享年80岁。如果说楚原的仙去带走了半部香港电影史,那么王羽的离开则代表了一代人侠客情怀的谢幕。
影迷对于王羽的感知,是上世纪60年代老电影赋予的。在片中,王羽手持单刀,大侠质感自不必说。面对千军万马如砍瓜切菜,杀得敌人落花流水,完全释放了自我身体动能。在代表作《独臂刀》《独臂刀王》《大刺客》中,他和张彻多次搭档,证明了男性魅力之于当年大众审美的引领和加持。
 《独臂刀》剧照。
《独臂刀》剧照。要说王羽的银幕魅力,并非只在于对侠客的定义和书写。细观王羽的表演,是具备内生力的。内生力是动静之间的相互博弈,在内心中形成一股风暴。“静”体现于王羽的微表情。我们多用“冷面大侠”来定义王羽。王羽在银幕上不苟言笑,除了冷峻和淡漠,是很少愿摆出其他神态的。在为数不多的对白中,五官始终要保持强控制感,言语自然成了神情的辅助。
侠客的魂魄体现在王羽的静态表情,这或许让影迷想到了《黄昏双镖客》的李·范·克里夫,《座头市》的胜新太郎。只有完成对神态的控制,才能抵达侠客应有的内心境界。此外,“静”与后来的“动”形成了水火张力,可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盲侠”座头市,在动静之间侠客的“势能”得以保留。同样,在王羽的《追命枪》和《战神滩》中,动静形态的转换成了电影的重要看点。
 《独臂刀王》剧照。
《独臂刀王》剧照。“静”体现于王羽的控制欲。不同于胜新太郎,王羽的正义感是要溢出来的。由“静”到“动”的转换过程中,王羽对这一瞬间拿捏的尺度是极度用心的。通过对王羽银幕心理的察觉,于冷酷中的愤怒、于正义下的冷静,可以调动观众的紧张感。弦绷得越紧、发射的力道越强,打斗前的氛围控制,远景和近景的多次切换,重围之内侠客身份的强化等,均能把前戏渲染到极限。而动静转换的那一瞬间,预示着王羽身体动能的完全释放,当然最终的绚烂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在酣畅淋漓的悲壮大战背后,王羽饰演角色的死亡强化了侠客的悲剧意义。
武侠经典化的诞生,多借助于“反武侠”价值观的呈现,如英雄的消亡、身体的缺失、礼崩乐坏的世道等。即便如《神雕侠侣》类童话式武侠作品,也以杨过的断臂来成全。而上述三种特征,均在王羽的电影中得到印证。《独臂刀》中王羽被断臂有张彻和倪匡刻意为之的缘故;但残缺放置在江湖中意义几何?这值得我们探究。
 《独臂拳王》剧照。
《独臂拳王》剧照。英雄除恶叙事模式相对正统,但“断臂叙事”却自有它的叛逆。首先,上世纪70年代王羽饰演角色的身体残缺,反衬出了江湖世道之险恶。其次,王羽把残缺身体和超人本领结合在了一起。开篇主角便具备了打败所有人的身体技巧,神秘感和未知感因为“独臂”被完全释放。再次,叙事均以主角完胜作为终点,个体价值得到了无限强化的同时,英雄主义也被电影延展到极限。英雄主义和阳刚血性在王羽电影中实现了强关联,残躯却增添了王羽角色诡秘性和颠覆性。
王羽的“独臂宇宙”并非邵氏《独臂刀》这一部,独臂成了王羽的标签,成为他颠覆现有秩序的外在表征。接下来主演的《独臂刀王》《独臂拳王》《独臂双雄》和《独臂拳王大破血滴子》中,王羽构建起了一个“独臂宇宙”,在武侠的边界实现了对江湖二次的解构。
 《独臂拳王大破血滴子》剧照。
《独臂拳王大破血滴子》剧照。上世纪70年代王羽赴台后,作品气质发生了明显变化。邵氏片场的白衣大侠渐渐丢失了少年时的正义感。在1977年《神拳大战快枪手》中,王羽的银幕能量在衰减,毕竟当时已过35岁,那份少年侠客被中年的人情世故所掩盖,不再锋芒锐利。通过上世纪90年代的采访分析,王羽内心是愿意成为大侠的。不似尔冬升之于现实和江湖分界的“人间清醒”,王羽的角色呈现和自我侠情的高度契合,在之后的演员中并不多见。甚至抛开电影,在现实中王羽身体内的“侠气”依旧十分充分。
王羽出生于1942年的上海,在战后第二批南渡的浪潮中,王羽随着父母来到了香港。上海是摩登的,也是市井的。早前王羽养成的江湖气,承接了市井的侠义精神,但也不同于现代文明带来的规整。在自我的价值构建中,王羽是把道义摆在第一位的;之于秩序的反叛、之于礼法的遵从、之于同行的仗义和对待后辈的洒脱等,真性情融入了邵氏片场的制作模式中。由内而外的侠义感,一方面实现了武侠叙事的呈现,另一方面实现了自我的精神满足。
 《独臂双雄》剧照,王羽(右)。
《独臂双雄》剧照,王羽(右)。此外,王羽是反叛的。在电影内他以独臂姿态出场,在电影外他对电影自主权的掌控清晰可见。王羽不同于狄龙和姜大卫,他并不屈从于邵氏的大片场制度;在和张彻合作了多部武侠作品后,王羽认清了个人商业价值。从主演到导演,不到三年,王羽完成了身份上的转变,这背后是控制权的争夺。《龙虎斗》中,王羽实现了导演和主演一手包办的局面,背后则是自我江湖全过程书写欲望的展现。
邵氏完成片约后,王羽便移步嘉禾、远赴台湾。在李小龙大红大紫时,王羽排除纷扰,在台湾完成了心中的江湖构建。2019年,王羽获得第56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可以看成世人对独臂大侠一生的认可,也可以看成世人对理想江湖的尊重和期许。
李言(重庆移通学院三级作家,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