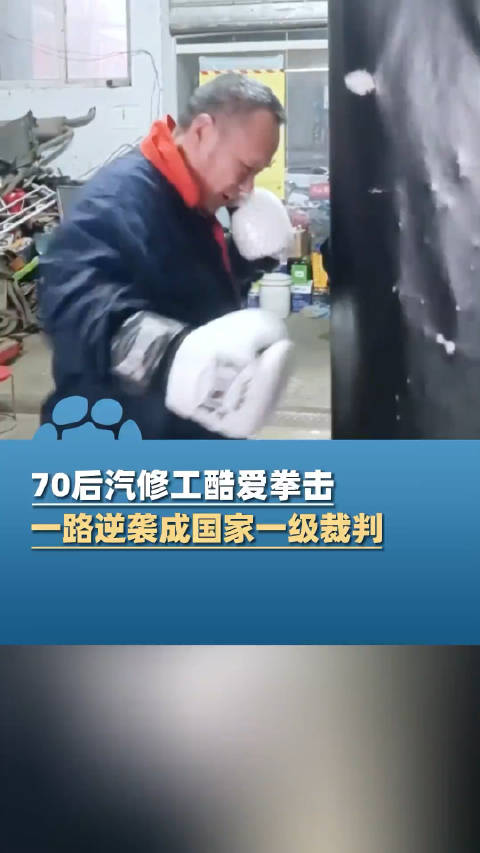《经济学家,请回答》是一本经济学家对话经济学家的集子。采访者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生于1924年,2023年去世,他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著称,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认为,索洛在20世纪是最懂得如何修辞、如何写作的经济学家。这本集子让读者知道了,索洛也是懂得如何提问的经济学家。
晚年的索洛决定向他的同行们发起征集,请他们从各自的研究专长回到一个经济学问题。得益于索洛在经济学界的号召力,此番征集的受访者阵容规模堪称罕见,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让·梯若尔、肯尼斯·阿罗、阿比吉特·班纳吉等。在年龄上,除了同龄人如乔治·舒尔茨,大多为索洛的晚辈。

《大空头》(The Big Short,2015)剧照。
遗憾的是,因为这本书的形式是征集,并没有展开连续的对话。不过我们仍然能在90组回答之中读到这些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当今世界,如何认识收入、女性、中产、工作等诸多议题正在发生的转变。除了与现实经济世界密切相关问题,索洛也向他们征集对经济政策以及对经济学这门现代学科的看法。下文摘选内容,即是关于经济学学科自身的看法。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经济学家,请回答》第4、41、69等篇章。
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文。
原文采访者|[美]罗伯特·索洛

《经济学家,请回答》,[美]罗伯特·索洛编著,许可译,文汇出版社·贝页,2024年10月。
为什么全世界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预测都如此不可靠?
以赛亚·安德鲁斯(Isaiah Andrews)
预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用实验验证。政策制定者通过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或改变利率,来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因此,当我们同时观察一段时间内的政策和经济状况时,很难确定究竟是政策的实施影响了经济走向,还是经济变化影响了政策制定。
为了解决这个挑战性问题,我们可以挑选出历史上一些政策变化与经济状况无关的时期,然后研究政策变化后的经济表现。然而,此类事件相对少见,本质上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以这种方法开展研究,只有较少的数据可供使用,而且可能会产生与正常时期的经济政策效果差异很大的预期结果。

《大时代》(1992)剧照。
另一种方法是,我们可以通过将数据拟合到一个模型中来估测政策的效果。如果通过这样的拟合模型 预测出的政策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与我们预期的经济自然演变的模式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模型出发观察数据,分析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但不巧的是,许多现代宏观经济模型并不能达成这一目的。即使我们假设这些模型是正确的,可用的数据量也不允许我们对政策的效果作出精确的预测。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类模型只能为我们理解因果关系提供十分有限的帮助。
由于模型充其量只是对现实的近似描述,因此,如果在估测政策效果时只追求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 度,可能会加大错误建模的风险。只有能在数据中捕捉到经济模式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模型,才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政策的效果。在实践中,宏观经济模型与数据的某些方面拟合得很差,而且通常我们并没有弄清楚这些建模误差对模型预测结果的影响究竟如何。这样一来,即使模型给出了精确的预测,我们也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这些预测结果。

纪录片《经济机器是如何运行的》(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2008)画面。
即便不考虑因果关系的问题,预测宏观经济的走向也并非易事。基于数据驱动的预测方法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从过往模式中观测出的信息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状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状况也会发生变化,同样的模式并不一定会持续下去。宏观经济学家必须认真思索应追溯多久以前的数据,这限制了可供分析的数据量。数据稀缺加大了宏观经济分析师面临的挑战。不过,最近的研究方法中使用了地区和个人数据,从而扩大了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可用数据的范围。
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困难程度,可以说即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数据,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预测 也乏善可陈。也就是说,这一领域在未来仍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一位心理学家在经济学领域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在我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4年左右开始研究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后,我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效用理论应用中一个奇特的假设所吸引,而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一假设都是风险决策领域的主流理论。
我们所质疑的假设是由雅各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在1738年首次提出的一项著名理论。他提出,在赌局中,人们是通过对可能出现不同结果的期望效用来评估选择的,而人们心中认为的“结果”即赌局结束后的财富状态。根据伯努利的模型,如果一个人有50%的可能性赢得100美元,或者确定能够赢得40美元,那么这个人会依据“我现有的财富”“比我现有的财富多100美元”和“比我现有的财富多40美元”这三种效用来评估赌局中的选择。
 纪录片《幸福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2011)海报。
纪录片《幸福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2011)海报。伯努利在构建这一理论时针对的是体量巨大的金融决策,他的理论在解决商人把一艘装满香料的船从 阿姆斯特丹运到圣彼得堡的风险决策问题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这个经典的船运案例中,已知损失船只的可能性为5%,商人想要计算出自己能接受的保险费用。很自然地,商人会首先比较自己当前财富的效用和船只沉没后自己剩余财富的效用。此例中,认为“财富状态”等同于“结果”的假设是合理的,但如果不同结果体现在财富上的差别十分微小时,这种假设就显得很牵强。
此外,在效用理论的应用中并没有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情况。因此,阿莫斯和我很快就决定提出一种全新的期望理论,将评估的对象定为“收益”和“损失”,并在小额或中等损失的情景下测试了理论的有效性。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也曾在同样的领域进行过尝试,但我们的探索更为全面彻底。

《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2013)剧照。
为什么伯努利的不合理假设能沿用如此长的时间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被我称为“理论诱导的盲目性”的现象。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学者是某一成熟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就很难承认甚至很难去思考该理论存在的严重缺陷。
另一部分原因是,如果不使用伯努利假设,而选择其他替代假设,人的选择会很快被导向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方向。如果人们从收益和损失的角度思考效用,那么特定财富状态的效用将取决于与之相比的参考状态效用。举个例子,如果现在赌局中的两个选择是,有相等的概率获得300万美元或400万美元,以及确定获得350万美元。这种赌局中产生吸引力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没有体现在效用理论中,那就是当前的财富状态。如果当前的财富为400万美元,那么相比当前的财富是300万美元的情况,选择冒险赌博的吸引力更大。财富状态的价值似乎取决于赌局的结果,会因结果是输还是赢而显得不同。
还有其他观察表明,损失的痛苦大于收益的快乐。但这合理吗?这种差异似乎是短视的:一个理性人在作出财务决策时,不应该由近期财富变化的情绪反应所主导。在标准的经济人假设中,理性的行为人是以财富状态作为预期结果,进而作出评估和选择的。
“理性人假设”在使经济学问题变得易于数学化处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行为经济学中,也有充分的理由继续使用“理性人假设”。当然,简化假设仍然适用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以理查德·塞 勒为首的行为经济学家在研究财富变化的短视效用时使用的竞争性假设就十分有趣,且令人耳目一新。以上,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却混迹于与自己不同领域的学者中。
市场和语言的相似之处
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
市场和语言都是古老的人类智慧的产物,是我们人类为了更好地合作、协调、竞争和组织各种活动而 创建的工具。就像语言有许多类别一样,市场和交易平台的种类也有很多。

纪录片《经济学大师》(Masters of Money,2012)画面。
一提到市场,我们通常会想到商品市场。在这类市场中,出售的对象已经被标准化为商品,你在市场 中交易时便无须关心自己在和谁打交道。举个例子,每块麦田都各不相同,但芝加哥期货交易(CBOT) 出售的是2号硬红冬麦的合约,这是一种无须进一步考察就可以买卖的商品。所以在商品市场中,所有工作都围绕价格来完成。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工作就是整天为它所销售的每一种商品找到能实现供需平衡的价格。
但不是每个市场都是商品市场。在某些市场中,你会关心自己在和谁打交道。在匹配市场中,你不能简单地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使你能负担得起价格),因为你也必须被选择。斯坦福大学在招生时, 不会采用把学费定得足够高,以使学生人数刚好等于教室的容纳量的方式;同样,谷歌也不会降低软件工程师的工资,直到刚好有足够多的工程师想在谷歌工作。
事实是,除非你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否则就不能在斯坦福读书;除非你被谷歌聘用了,否则也不能在谷歌工作。所以,大学录取和劳动力市场的本质是匹配市场。我们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些关口都会遇到匹配市场(如你不能简单地选择配偶,你也要被其他人选择……)
我设想,如果有一位火星科学家飞来观察地球人(假设这位科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人类)的活动,那么 其发回火星科学基金会(MSF)的第一份报告可能会这样写:人类总是在交谈,而且总是在交易、协调、合作和竞争。也就是说,火星科学基金会将了解到,语言和市场是人类的基本工具。
一旦我们把市场看作工具,就可以开始思考如何充分地理解市场,以便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修复,并建立起新的、更好的市场。这些都是市场设计的任务。
叙事经济学是什么?
罗伯特 · 席勒(Robert Shiller)
在1896年 的《 帕 尔 格 雷 夫 政 治 经 济 学 词 典 》 (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有一个关于“叙事经济学”(Narrative Economics)的条目,但词典中给出的定义并不是最新的,它写道:“叙事经济学或历史经济学中,不仅包括按纵向的时间顺序叙述的过去事件,还包括对同期或不同期社会的比较。”根据这个定义,叙事经济学与针对经济事件的年代学或地理学研究就相差无几了。
2017年,我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针对“叙事经济学”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定义:叙事经济学应该是将流行叙事作为经济力量本身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叙事经济学并不构建叙事,而是研究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叙事—这些叙事其实在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中一直有活跃的影响。叙事经济学应该关注广为传播的叙事,这些叙事通过口口相传或社交媒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开来,并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经济决策。过去重大经济事件的叙事可以在早期报纸数字化的材料、书籍、讲稿、日记、社交媒体和其他传播途径中找到。
我们应该记住,“叙事”这个词不能与“故事”画等号。叙事是叙述者从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出发,讲述故事、传达理论或动机的过程。一个单一的客观故事—比如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故事—可以从无数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述。
 纪录片《1929大萧条》(The Crash of 1929,1990)海报。
纪录片《1929大萧条》(The Crash of 1929,1990)海报。1929年之后,一些观点占据了主流,大家遍相信“股灾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糟糕时代”这一故事叙述,导致人们对自己的未来切实地感到恐惧,并停止了消费。1929年至1932年,福特新车的销量下降了近80%。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在几年内不买新车,直到不再恐惧。但由于人们普遍推迟购买车辆,汽车厂被迫关闭、工人遭遇解雇,大萧条局面因此产生。
上述“叙事”甚至被铭记至今。现在,电视新闻广播在每个交易日都会尽职尽责地报道道琼斯工业平 均指数的变化,而《华尔街日报》在每个头版的横幅下方都会刊登这一信息。在1929年之前,道琼斯指数并没有这样的市场影响—1929年的大萧条让道琼斯指数出名了。今天人们仍然认为道琼斯指数也许能够预示另一次大萧条。这是一种不会消亡的叙事,它在公众思维中根深蒂固。有关大萧条的说法在2007年至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再次出现,可以说,如果不是它重新点燃了公众的恐惧,萧条也不会如此严重。
与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相比,经济学家对叙事的兴趣要小得多,而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叙事的兴趣相对较大。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家很难确定叙事和经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想知道如何证明一些流行叙事是否真的有效地影响了经济行为。他们希望看到所有经济活动影响因素的量化证据,这样才能确定其在统计学上的意义。
而量化叙事影响的问题在于,叙事是复杂而模糊的。某一叙事的影响可能只取决于其中包含的几个关键词语。而叙事中细微差别的含义和对当时的人的意义,似乎需要依靠个人判断才能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和预测经济事件,尝试系统地研究不断变化的流行叙事是一条必经之路。
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的方式,假如可以改变
理查德 · 塞勒(Richard Thaler)
标准经济理论最基本的特征是,人们通过优化的方法来作选择。也就是说,消费者在面对所有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商品和服务组合中,会选择其中“最好的”一种。企业同样采用优化方法,选择最有效的生产过程并制定合适的价格,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除了对市场的关注外,正是体现在其关于优化方法的这一假设上。但经济学的这种特征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的核心:经济学家会将最优化假设应用于两项不同的任务,而它只适合解决其中一项任务。这两项任务分别是:(1)描述一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2)预测大多数人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实习生》(The Intern,2015)剧照。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考虑一个找工作的问题。假设查理失业了,开始找一份新的工作。他偶尔会得到 一些工作邀约,而他必须迅速地回复是否接受邀约。如果查理回复“是”并接受了这份工作,那么他会停止找工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为了使问题更易于处理,经济学家会作一些额外的简化假设,通过建立模型来确定查理的最佳策略。解决方案会根据当前的经济环境,准确地评估查理的市场价值。查理可以采取的一种策略是,确定一个合适的最低工资(在已选择了其他工作标准的基础上)后开始找工作,直到找到这样的工作机会,或者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应该降低期望值。为这类问题寻找好的解决方案是一项相当有成效的工作。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会经常面临类似的困境,例如,企业会面临招募新员工或寻找新的供应商的问题。
而预测查理在找工作时实际会怎么做,就是另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了。比如,查理可能过于在意对标 自己以前工作的薪资水平,即使他工作过的公司已经倒闭了,类似的工作选择也很少;或者他可能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有夸大(或贬低)的看法。再如,他可能会过分压缩自己的求职范围,错误地认为只要某一份工作与自己上一份工作差别很大,就完全不考虑,等等。在实际情景中,查理不采用优化方法而选择其他策略的可能性不胜枚举。但在一个仅仅基于最优选择的模型中,上述所有因素都将被忽略。
因此,我对经济学界的一个期望是,我们需要明确认识到一种理论不能同时满足两种目的。之所以存在锤子和螺丝刀两种发明,就是因为不同的任务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完成。研究描述性理论的学者仍然要掌握优化的艺术,但也需要发散思维,了解人们在实际中会采用的各种次优策略。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研究结果以及一些处理大数据的新工具(如机器学习)可能对完成这项任务有所帮助。此外,抽出一些时间,观察现实中人们的行为,也会对研究有所帮助。
原文采访者/[美]罗伯特·索洛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