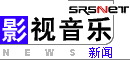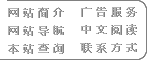每年参加“百花奖”和“金鸡奖”的采访,都面临一
个两难选择:作为新闻记者,无法不客观报道它的方方面
面,这就包括了它的消极、没落甚至丑陋;而作为个人,
由于曾经与它有过种种亲密关系、对它有着比较深入的了
解,又不能不为它的今天和明天感到深深的悲哀。
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抹杀“双奖”(我宁愿称它为“
双奖”,所谓“电影节”不过是它西装外套上的马甲)对
中国电影事业的功绩。百花奖自不待言,金鸡奖对于中国
电影观念上的刷新也是里程碑式的。陈凯歌有今天,张艺
谋有今天,无不得益于金鸡奖———或是评奖本身,或是
评奖过程,有时候,“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而“双奖”的现状,如媒介所言,是(主办者)级别
越来越高,档次越来越低,权威性越来越差。关于这一点,
任何传媒的任何形容都不过分。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
一线演员如果不是抱有其它目的,比如为新片做宣传之类,
就少人肯赏脸光顾了。现在更是成了珍稀动物。不再有人
对这两个“国家级大奖”心存敬畏。常有得了百花奖而未
得金鸡奖的人,一点也不客气地宣称“看重的是百花奖”,
言外之意是金鸡奖狗屁;得了金鸡奖的人偶尔会怯生生说
一句“金鸡奖专业水平最高”,也可能会公开宣称“更想
得百花奖”。其实私下里,谁也不以此为荣。也许中国没
有什么奖项是真正神圣的,但如此被视同儿戏的似乎也少
有。
这当然是“双奖”活该。一种奖项,既不能给人带来
财富,也不能给人带来荣誉,人家凭什么要敬重你?如果
得了金鸡百花奖能在票房上稍有裨益,能给投资人带来哪
怕百分之一的利润,它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再狂的明星,也不敢得罪观众。明星是冲着观众而来
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群众性,能给他一个现成的机会免除
拎着拷贝到处搞“首映”之苦,他干嘛不来?然而群众又
是冲着明星而来,越没有明星,就越没有群众;越没有群
众,也就越没有明星;这便是“双奖”陷入的怪圈。
在这个怪圈里,即使表面文章做得再热闹,也不会有
人承认它的“广泛性”(这种神圣的词语,也不宜用在这
里);签名的人再多,也说明不了它的参与程度。广东巨
星影业的邓建国,去年还雄心勃勃地想“承办”,今年连
脚都懒得抬。你承不承认私营老板的判断力?
没有权威性,也就不会有公信力。过多的失望,就会
构成鄙夷。中国影协的名声,离中国足协不远了。
那么,“双奖”走到这一步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有电影,就会有电影的评奖;有什么样的电影,就会
有什么样的评奖。你不能指望一只鸭蛋能孵出天鹅来。
中国电影如今正是一只这样的鸭蛋。
戛纳和柏林代表了欧洲人(至少是欧洲影人)的电影
观,奥斯卡则代表了美国人的电影观。但我们可不可以说
百花奖代表了中国人的电影观?或者说金鸡奖代表了中国
影人的电影观?我相信没有人首肯。百花奖评出来的最佳
影片,决不是中国观众最想看到的影片,而只是“你能够
看到”的影片中比较喜欢的一部。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这个“不同”是致命的。这个“不同”使观众觉得它
与自己的“影事”毫无关系,这个“不同”使中国电影失
去了对它的衣食父母(也称“上帝”)的真诚,当然也换
不回真爱。“双奖”的演化过程,就是国人对本土电影从
热爱到冷漠的过程。当我们不无庆幸地回顾改革开放二十
年这个古老国度的巨变时,发现在那个大座标上,电影这
条线是逆向的。
透过“双奖”,我们看到的是一支七零八落和基本上
低素质的制作队伍,一些颟顸的理论家和不着边际的评论
家,还有,一些并不老迈的电 影官僚和一个腐朽的电
影体制。据报道,有不止一家的电影制片厂是靠“卖厂标”
谋生的。何谓厂标?就是可以转卖的特许经营权。没有这
种特权,你就必须花钱去买,否则哪怕你有再充足的资金、
再完美的剧本也是白搭。改革开放二十年,连一些国家部
委都不再拥有这种特权,小小的电影厂却仍能靠它维持“
寄生虫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双奖”也有它“幸运”的一面。只要它愿意,几乎
每次都能找到政府给它出钱出力。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不
用征求纳税人的意见,没有人来追问你这钱花得值不值。
一方面,政府的“指令”限制了电影业的发展,另一
方面,政府的权威又维持了电影业的生存,真所谓“成也
肖何,败也肖何”。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弊端。
中国的电影体制不改变,“双奖”难有辉煌之日。
本报记者 朱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