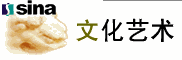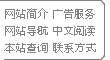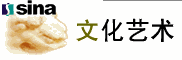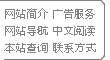崔永元1963年生于天津,小学头三年就读于北京郊区
一农村小学,至今记忆深刻,后以北京重点中学12中最低
分数线考入该校。1985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随后
就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5年底开始为中央电视台新闻
评论部服务,1996年3月起主持该部《实话实说》节目,
1998年6月,调入中央电视台。
△你正式调离中央广播电台了?
○调离了。我把档案关系都放到中国电影乐团了。我
在电台时是兼职干,当时觉得兼的状态比较好,在这边当
记者,经常采访,了解一些新鲜事情,然后到那儿主持还
用上了,挺配套的。现在这么干着,真是个事儿。关键是
没有什么积蓄了。现在我脑子里闪现出来的,还都是过去
的一些东西,没有新东西往里装,挺可怕的。我看过自己
的节目,很多招势,有很强的模式感,一看就是我自己记
忆中的东西。
△你的同事讲,你录制节目的头天都睡不着觉?
○现在也是,录像前一天就睡不好觉,录完像当天也
睡不好。前一天夜里脑子里一直打架,各种声音、各种议
论,全是自己设想的;录完了,不管录得好坏,都是非常
强的刺激。我甚至试过,在录像完了回来,追忆现场的内
容,几乎都记着,每个人的每句话都记得很清楚。
△你一星期录几次?
○至少一次。
△那你一星期下来,休息时间前后没多少?
○我脸色通常都是灰白的,长期缺觉。化妆能弥补一
点。
△你很注意人的心理。
○我想节目主持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先把别人调整好。
但是可能不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没有调整好自己。就是
太在意自己了,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媒介形象,爱护自
己的每一根羽毛,所以他很自然就和现场观众有一种距离。
△这个节目的方式,与你个人有很接近的东西,当初
找你当主持人也考虑到这一点吗?
○我觉得所有谈话类节目都需要平等朴素的方式。你
请人来,不是为着表演,而是要和他们交流,交流确实需
要关系平等。现在我和领导说话也不是那么容易,每个人
和领导说话可能都会有点心理障碍,毕竟上下级嘛。在不
民主的家庭里面,跟家长谈话,孩子也会心有余悸。这种
情况常能遇到,你有心理压力,才会有变形的动作和语言。
△不能说真话跟心理压力有直接关系。就你自己,作
为主持人,压力主要表现在哪儿?
○目前我最大的压力,就是对所谈话题没有足够把握。
每一个话题在录像前,我都不知道今天会谈得怎么样,谈
得好不好,这是我压力最大的地方。而且呢,我们录的节
目大概有80%以上都被认为是不够成功的,不能令人满意
的。
△80%是谁的标准呢?
○节目组的标准。每次录完像,大家就聚在一起,说
说今天怎么样,大多数情况都是不满意。大家真不满意,
我也不满意,说出今天的问题,比如你参加的《百年衣裳》
上集,那天下午一录出来大家就不满意。话题很虚,不实
在,我们讲服装史、讲理论吧,观众不爱听,现场有点尴
尬似的。到了晚上就好了,那是录的下集,大家从全国各
地来,每人拿一件衣裳,讲一个故事,运作也非常简单,
现场状况好,谈得也不错。同样的“衣裳”,怎么能谈出
两种效果来大家就要分析分析了,也会找主持人的原因。
△你接受电视这种方式,有没有障碍?
○我现在在现场几乎意识不到了。有时候我非常投入,
情不自禁地说某些话,做某些动作。还有,精神放松以后,
我会注意配合摄制人员和观众,比如我能注意到会不会挡
住正在说话的这位朋友,观察一下机位,把位置闪出来,
能拍到他,别挡着他的脸。比如我站着,是不是太高或者
太低,这样都会让画面不好看。我已经能自如地调整这些
事情了。
△刚开始有没有影响?
○刚开始非常紧张,我就担心紧张了无话可说,下句
接不上来怎么办。张到什么程度呢我努力去听,还是听不
懂,进不去,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理解他说的呢怎么
给他归纳、总结出来呀心里非常慌乱。不过,紧张有时条
件反射,它使你努力去听别人说,歪打正着,紧张就释放
你的潜能,强迫的呀!
△在那个过程,有没有出现特别尴尬、特别令人棘手
的场面?
○那种时候还真不多。那时候嘉宾和观众比我还慌乱
呢,中国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一般的节目都是
观众在家准备好,到这儿轮到他他说;这个地方,都没有
、不知道什么时候话筒就杵到你面前了,所以他们更紧张。
现在好多了,他们放松了,经常在现场给我出难题。比如
黄月,她说现在调试好了,她跟丈夫的状态都非常好。我
问她:“那是不是你的标准降低了”她看着我说:“你这
样认为吗你以为我的标准降低了吗”这种情况是以前从没
出现过的,嘉宾反问我,没有。一般都是被我问住。
△谈话有了递进,你怎么回答?
○我愣了一下,转身问观众:“刚才是谁问的”转移
一下,大家一笑,就过去了。然后我给她总结:“比如有
的人,说他现在婚姻凑和,还行,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降
低了标准,实际上他是找到了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能够使谈话纵深发展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策划帮我找
出来的,我以前的毛病是现场遇到这种情况,开个玩笑就
结束了,后来他们说这个谈话没有继续下去,还没有谈清
楚,你怎么能就这样放弃呢这话给我印象非常深,我就改
正了这个问题。在现场,我还会跟你开玩笑,笑声落了以
后会接着把它说完,接着把它探讨下去。
△《实话实说》在形式上,不同于各省市以及中央电
视台其他节目的地方在哪儿?
○就是它的装饰感非常弱。上了电视就要有装饰感,
你要打灯光,要化妆,要换衣服,要用话筒把你的声音扩
大,现场有那么多摄像机盯着你,五颜六色,这都是外部
环境给你造成的装饰感,你没办法克服它。这个节目装饰
感相对弱,我们用许多技术手段把这些装饰感给消除了,
包括我前面说的掌握呀什么的尽可能消除掉。另外,我们
追求即兴,它是保证谈话生动的一个重要基础,对一些电
视人来说,会认为这很担风险,他们会在前期准备上、操
作上加一些可控的成份,但是这个可控的成份就让谈话失
去了鲜活,失去了灵魂。还有,我们在平衡参与者的心态
上,做了很多文章,其实这个我不愿意说,我也有点保守,
不愿意所有人把它学到手笑。比如现在我看别的电视节目,
请来的人都要加上“著名”,是著名吗你说的名不符实,
对观众和演员本人都不尊重,也不诚实,这种大话很有点
可疑。可是在《实话实说》谈话现场你就会发现,这里从
来没出现一个“著名”,演员就是演员,学者就是学者,
作家就是作家,谁就是谁,不虚饰。你参加的那期《百年
衣裳》,黄宗江也在,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头,那期没有
嘉宾席,大家都坐在下边,事先安排一位年轻演员坐在他
旁边,那位年轻演员说:“我怎么坐在这儿啊能不能跟年
轻人坐在一起”我说:“你知道这是谁吗他当明星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黄宗江就坐在那儿,说两句老百姓
的话,大家谁也不觉得谁比谁怎么样。
△和别的主持人比较,你的优势是什么你对自己怎么
评价?
○我很拒绝这种比较。我认为不是一样的。不是一个
行当,他们有他们的专业,有他们的专业知识,按他们的
习惯方式操作,我这个是另类,更多的是体现日常做人吧,
技巧上,现在掌握的、挖掘的还不太多,越发展会越好。
我老觉得不是我个人不断挖掘内心的潜力,调整自己的状
态,让它做得更好就万事大吉,而是时世造英雄,当我们
把这种形式摸熟了,摸透了,也有更多人去理解它了,这
时候很多平民会跳出来主持这个节目,来做这个节目,他
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因为他们踩在我们肩上,我想那时
候我该退出,去做幕后的策划。
△你对那些有兴趣吗?
○有兴趣,我就是干那个出身,我在电台干记者时,
业余时间就帮别人策划,电视台他们知道我,完全是因为
策划。
△最早怎么找到你的?
○都是同学。当时特神,在学校时没有差距,差不多,
但是他们到了电视台以后,文笔就不行了,就来找我,让
我写,当时我误认为是我的文笔比他们强,等我到了电视
台一看呀,是这个环境把人全耽误了,用进废退,不用这
个功能它就退化了,我干了两年再写东西,发现真是不如
以前了,写东西越来越生涩,也开始退化。做电视工作,
很容易让人浮躁,又编又写又什么的,好像很滑稽似的,
理论上它也成立,叫工业化生产嘛,分工明细,各司其职,
你干好你的就行了。我是主持人,我都不用写策划案,专
有人写,主持好你的节目就行了,他有他的指标。所以你
身上很多东西衰退了,也有的地方强化了。这么个原因,
那时候我的文笔显得比他们好。动笔动脑子的,《东方时
空》《焦点访谈》很多特别节目都是我策划的,我撰稿,
比如《焦点访谈》周年时,做了两个特别节目,一个叫《
寻找英雄》,我是策划,另一个叫《在路上》,我做策划
和撰稿;《东方时空》一百期,我的策划和撰稿;《东方
之子》两周年特别节目,做策划和主持,那是《实话实说》
的雏型,时间在1995年5月,效果挺好,挺像现在的《实
话实说》,那时还没摸着门呢,事先得沟通,类似彩排,
还有这个程序呢。
△最早尝试主持就是在《东方时空》?
○这是第一次。
△这次经历以后,你是不是就对主持有兴趣了?
○哎哟,一点兴趣没有,简直难看死了样子都难看,
我觉得惨不忍睹,没办法接受。
△你觉得你适合上镜吗?
○不适合。两年了,我才慢慢看着自己有点顺眼了。
△两回第一次,你都是怎么上的?
○做《东方之子》时有临时心态,他们也连蒙带骗,
说实际上就是弄个记者现场采访,那次是讨论见义勇为的
事。《实话实说》开始上,是时间正式跟我提出来的,他
说让我来主持这个节目。时间非常有意思,我们是同学,
特别熟,他当时给我打电话,一句话是说:你可以来试试,
来主持这个谈话节目,第二句话说:你小子出名了,别忘
恩负义。现在想想,他好像特别有底气似的,好像我一干
就能干成。后来我了解到,最早想办这个节目,乔艳琳、
杨东平、关秀玲,他们三人筹备,想到要用我,去跟时间
说,时间说:咱就没别人了干什么事儿都想他。他们就把
我放在一个最低限,先找别人,实在找不着就凑和用我,
时间那时候也像得了魔症似的,出去跟人家吃饭都问:你
能不能帮我们主持节目见着谁问谁。我觉得他心里也是有
一个平民心态和标准,他根本不问你的学历,你的背景,
他跟你谈话,觉得你谈话方式好,就认为你可以干这个节
目,和我们的想法是非常吻合的。我当时不想干,主要是
对自己的形象没有信心,我说过,我大部分年华还是当电
视观众,在选择节目时,我也有非常传统的心态,愿意找
俊男靓女看,我就没有同意。时间和我年龄一般大,但他
成熟得多,他做工作很有方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
跟我说了一句:我可告诉你,这个事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
的那意思是说:这个事干成了,是很需要实力的。当时我
作为一个男人,内心很有一种冲动,所有男人的潜意识都
有这种冒险精神,愿意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都希望能写
进吉尼斯,那么既然不是所有人能干得了的,那我就要试
一试。我当时想,大不了就丢回脸,做一期不行就下来,
两期不行下来,三期不行下来,随时准备撤,不行就走。
我在电台当着记者,也有退路嘛。就这么做起来了。一直
做到现在,我也是这样想,明天需要我下来,就明天下来,
不会因为这个伤心,没有关系,我做别的一样可以做得好,
一样可以做得出色。
△你在电台时,是个什么样子的记者?
○我觉得是个很棒的记者,我写的稿子很有人情色彩,
我也能感受得很深。有一次,我到山西一个村子住了一段
时间,了解一个年轻支书和老支书的纠葛,我把这件事情
写得非常清楚,很有人情味。老支书在那个“极左”的时
代,只能昧着良心干一些事儿,比如要整人什么的,可悲
的是,他自己并不认为有错。年轻支书上来,已经是拨乱
反正了,村子也有了新风,村子里各方面都在发展,人们
惟一不能理解的,还是这个老支书,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个
村里一下子地位非常低下。年轻支书很大度,他就重新树
立老支书的地位,不是他领导的地位,而是他一村之民的
地位,他依然有在这个村子里做一个普通村民的权利。所
以年轻支书把老支书的功过说得很清楚。到老支书死了以
后,年轻支书在村子最高的地方,给老支书建一个碑,就
是说让他继续看着村子里的变化,他是这个村的功臣:绿
化,有他的功劳;村子里的规划,有他的功劳;各家娶嫁,
生儿育女,也有他一份功劳,谁也不该忘了他。年轻支书
当初对我说了一句话:“那时候他犯错误,能赖他吗?那
时候天安门城楼上都有坏人。”说的都是农民的语言。这
些东西经常打动我,让我的情感得到升华,对我做人特别
有好处。
电台我见到的老编辑里,也有我特别尊敬的,他们的
为人,能让我悟出很多道理。我们的老编辑,有不在乎职
称,只在意自己工作的;有一肚子学问,仍然平易近人的
……这些我都见过。比如珂云,他改我的稿子,从来不说
你这儿错了,古汉语这地儿错了,他用铅笔画一个道,说:
“我好像记得我看的那个版本是那么说的,咱们查一查。
”查的结果他的对,我的错,他说:“可能那个版本更可
信,咱们用那个吧。”他都不说我错,给我留足够的情面。
这些东西是非常教育我,也非常打动我的。除了在那儿有
很多社会实践机会,接触很多生活中最朴实的人,了解他
们内心的想法,我也学了一些做人的道理。现在这些有益
的东西在我主持《实话实说》中,还在继续起作用。
△你平常对着装在意吗?
○不在意,我现在穿的衣服,有时候他们说搭配得还
挺好的,全是我爱人给我弄的,她弄什么我穿什么,我说
该换衣服了,她头天晚上就把换洗衣服给我放到床边。有
时候她出差不在,我自己搭配,她回来就说:“哎哟,真
差!这个怎么能和这个穿在一起呢”这些事儿,我好像不
过脑子似的,不爱想。
△你接触观众时,观众对你的着装是不是合适会有想
法,这时候着装就不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这就是公众人物面临的问题。
△你在现场穿的服装是规定好的吗?
○我们有一个服装师,她给准备的。她都搭配好,去
了就穿。别人说,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其实我看哪个
都合适,我一概没感觉。平时和在节目中,都没感觉。有
时候走在大街上,观众碰到我,说:“你就穿这个”我说
那还穿什么呀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多难受呀,我从来不
打领带。
△有内容的人,取向往往偏内,而不是走外,不管是
干什么的,好像这是一种规律。
○我在沈阳机场,遇到一个辽河油田的人,说:“哎
呀,我们觉得你们的节目什么都好,就是衣服不行,哪天
你到我们辽河油田来一趟,我们这儿挺有钱的,大家给你
做一身。”他说,“你的衣服是不是全是家里自己穿的那
个衣服不能上电视啊”有时候我去饭店吃饭,一大帮人过
来跟我喝酒,我说我不能喝,他们说:“不喝你是看不起
我们啊”那我就硬着头皮喝。我想,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
享受到的,真是一个大明星去了,人家可能远远观望,未
必要来跟你喝杯酒,跟你说两句心里话。这也算个晴雨表
吧,衡量目前自己的状态和位置怎么样。这些东西失去越
多,说明我的负面影响就越大,消极的内容就越多。观众
见了你有了别的反应,你就要警惕了,反省自己,在生活
中、节目中去调整自己。实际上这也挺累,就跟别人有意
识要往大明星那边靠一样累。但我既干这一行,又不想拿
那种不应该属于我的姿势,观众接受我的也是这种跟他们
一样的努力活着的样子,我有什么可说呢?冯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