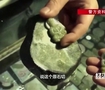本文节选自《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以下为正文部分:
我出生于辽宁沈阳,生日是1929年元月7日,至少后来的户口本是这样记录的。懂事后,我一直记得我的生日是1月8日。解放后,派出所发来的户口簿,不小心弄错了,变成1月7日,只能将错就错了。出生时的细节,父母没告诉过我,只晓得是在沈阳城里的一家医院。
1929年,中国东北的局势非常紧张。1928年6月发生皇姑屯事件,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会处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当日不治去世。少帅张学良为报杀父之仇,决定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1929年,国民政府对中国部分省市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我出生时,辽宁还叫奉天省,沈阳叫奉天市。几个月后,奉天省更名辽宁省,奉天市变成了沈阳市。
当时父亲金涛就在京奉铁路(北京—奉天)做铁路工程师。奉天更名后,随之变北宁铁路。1931年,我已经两岁,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军炸毁了日本修建并管理的南满铁路,而后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机炮轰并占领了沈阳。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把北宁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撤回到北平,包括我们全家。沈阳虽然是我的出生地,但只待了两年多,还在摇篮里,完全没有印象。
我父亲名叫金涛,本名义涛,号旬卿,祖籍浙江绍兴湖塘,1888年生于绍兴。他曾跟我提起,祖先原本姓刘。五代十国时,吴越的开国之王叫钱镠,因镠与刘同音,为了避讳,该国的刘姓人,皆去掉繁体字刘字的卯头刀旁,改为金氏。我查过书,真有这事。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岁,人到中年。回北平后,父亲仍在北宁铁路谋事。不久转到平绥铁路(北平—绥远)出任工务处长,那是铁路上的要职。平绥铁路,由中国最早一批留美幼童、耶鲁大学毕业的铁道专家詹天佑设计。詹先生人称中国铁路之父,父亲到任时,他已过世。
我没见过祖父、祖母,他们去世很早。古时候,祖上在绍兴是酿酒的。历史上,绍兴酒一直很出名。绍兴另一个出名的是师爷。我祖上后来改行做师爷,在衙门里给人写状子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在清华填表。家庭出身一栏,他填的是“前清刑幕”。所谓刑幕,即刑名幕友,是清政府机构中专门办理司法诉讼的幕友,简称刑幕。到我父亲这辈,他们四兄弟多半还是做师爷。后来不兴叫师爷了,但还是在官府、法院做文书。最后只有我父亲跳出了行当。他先去了东吴学堂念书。那是1900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的,也是中国最早以现代学科创设的大学。读完后,他考上唐山路矿学堂。该校创办于1896年,前身是北洋铁路官学堂,也就是以后的唐山交大。1906年,他是路矿学堂首期学生。据说一直是班上头一名,拿最高的奖学金。当时还是清朝,学校规定,奖学金只凭成绩颁发。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不满,闹学潮,要求全公费,并推选我父亲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校方非常恼火,但父亲不肯认错。虽然他是优等生,校方还是毫不留情地把他开除了。之后他辗转到了上海,进了南洋工学。该校1896年由洋务派人士盛宣怀创立,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大。
1909年,父亲在南洋公学只待了短短半年,即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公费留美,他是庚款第一届学生,也叫首批清华公费留美。1909年10月12日发榜,同届录取的有梅贻琦、程义发、金邦正、胡刚复、王士杰等四十七人。父亲名列第三名,去了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学士。当时工科博士、硕士极少。大学一念完,他就回国了。他的同学金邦正、梅贻琦后来都做过清华校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小儿子纪湘清华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他联系了康奈尔大学校史馆,找到他爷爷当年的毕业留言册。毕业那年,我父亲二十三岁。毕业照右边有段英文描述,说他“不远万里(英里)”来到康奈尔读书,回国后,他最大的愿望是建造一座打破世界纪录的双铰拱桥。
父亲给人的印象比较严厉,不爱讲笑话、很少开玩笑,对小孩更是严肃,几乎不跟我们说笑,也很少跟我们一起游戏玩耍。传统的中国严父,只是耳提面命,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他很喜欢散步,去北海一定带上我们。说话时,他有绍兴口音,夹杂着上海话,可能与当年在上海读过书有关。在北平,他往来的朋友多是南方人,江浙一带的,听得多了,我对上海话也能听懂七八成。在公务场合,他完全讲北京官话。在南方人里,他的国语还算标准。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作为平绥铁路工务处长,他陪同当年留美的老同学金邦正、任叔永、陈衡哲、胡适等走了一趟平绥铁路。同行的还有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他很少谈及当年的留美经历。记忆中,他说过几个似乎并不重要的故事:在康奈尔读书时,他要自己开伙做饭。有一天,他去当地的店里买米,一旁的美国人面露惊讶,这个中国人怎么买那么多的米!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吃米饭的,不吃面包,都这样买米。
赴美留学,是他一生很重要的经历。当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使他坚信科学才能救国。留学时,他很刻苦,学了很多。当年,胡适先生跟我父亲在康奈尔是同学,也是好友。胡适起先读的是农学,但完全不感兴趣。有一阵子,胡适打牌上了瘾。父亲是中国同学会主席,又比他年长,时常提醒他。胡适日记中有一段记载:“今日,迁居世界学生会所,初次离群索居,殊觉凄冷。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在这之后,据说他的日记中再无出现打牌的记录。胡适后来转向了人文学科,成为思想大家。
归国后,他先去了北京大学短暂任教,教化学。他曾经提起,当年在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张国焘,是理工预科班的,“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出席过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不过当时没有什么印象。父亲是学工的,更希望为国家做工业、实业。离开北大后,他就进入了铁路业。清朝晚期,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使列强取得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权利。他一心想为中国修建自己的铁路。
我母亲是湖南长沙人,名叫张孝劬。我的小儿子名叫纪湘,就是纪念祖母的湖南故乡。母亲父母早亡,很小就过继给了伯父张伯熙。他是清末重臣,教育家,晚清新派人物,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的章程就是他起草的。二十世纪初年,还曾短暂出任过北大校长。母亲在长沙度过了童年,后来移居北平。娘家办银行,做金融,家境优渥。她比父亲小十二岁,是个新派知识女子,不裹脚,北师大女附中毕业,是所名校。北师大女附中毕业后,经好友做媒,也算自由恋爱,认识了我父亲。结婚后她就一心持家,做了家庭主妇。父亲归国后结过一次婚,但因为夫妻间脾气不合,经常口角,关系不睦,也没要孩子,很快就分手了。父母结婚是在北京,1926年或1927年的光景,婚后生了四个孩子,我哥哥、我、我弟和我妹。
家境虽好,父亲薪水也高,但母亲特别节俭,很能持家。除了用厨子、奶妈、保姆、车夫,其他能省即省,从不铺张。她穿着也不讲究,很少绫罗绸缎。旧的内衣,缝缝补补再穿。家里的奶妈、保姆,多半在家里做了一辈子。好几个都是我们送的终。最后一个保姆,是魏奶妈。年轻时生完第二个孩子,她就从乡下逃出来了,因为丈夫家暴。在农村,婆婆通常特别厉害,总希望儿子找机会惩罚媳妇。儿子觉得媳妇没错,干吗打她。儿子不听话,老太太就发脾气,儿子没法子,就找茬打老婆。后来打习惯了。老太太一不高兴,她就挨打。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奶水好,给我妹妹当奶妈。后来她全家都从乡下搬到了北平。
在家里,母亲跟湖南的亲戚说长沙话,跟我们说国语。她也喜欢散步,经常陪父亲外出遛弯。有时到北海、后海、王府井,就在家边上。她是个知识妇女。如果父亲训斥孩子,她会心疼。不过,她当面不说父亲,给男人留面子。事后会偷偷给车夫塞点钱,让他带我们去外面玩,避一避风头。父亲待人很好,但脾气有些急躁。母亲明白这个理,也不跟他吵。记得有一回,两人闹矛盾,她一生气,就让车夫送自己回娘家了。她不理父亲,也不吵。父亲觉得没趣了,赶快上她娘家说好话,道个歉,再接她回家来。
我童年的回忆,都在北平。父亲在铁路局待遇优厚,我们家至少是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准。从沈阳迁回北平后,父亲买下一个大院子,安了家。宅子在地安门,北京皇城四门之一,鼓楼南面,景山以北。地址是地安门东板桥酒醋局13号。宅院很大,有五十来间房。我们一家子独住太浪费,就只住后院,前院租给了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是他从前的同学,名叫嵇铨。后来出任过北平的建设署长。后来家境不宽裕,把后院一些空房也租了出去。那栋大宅,原是清朝一个富姓大家族的。后来家道中落,被迫出卖房产,成了我们家。
我兄妹四人,三男一女,或是受了父亲影响,最后都学了工科。按照家谱,我们是“国”字辈。大哥,金国幹;我是老二,金国藩;老三,弟弟金国梁;老四是女孩,妹妹金国芬。三兄弟,各有名号,我是仲屏,哥哥、弟弟的名号忘了。大哥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石油专家,毕业于辅仁大学,专长是煤化油。弟弟金国梁,清华毕业,读土木工程。毕业后,他在中科院哈尔滨地震与力学研究所工作,二十年前因高血压去世。他很聪明。金国芬,也是清华毕业并留校,是清华自动化系的教授。她丈夫也是清华教授,叫陈允康。他们都已退休。好几个孩子也是清华毕业的。我们家与清华有三代渊源,有人说我们是清华世家,也不为过。
我们四个兄妹,家里最忙时有三个奶妈或保姆,帮母亲照看我们。我的保姆是一位老太太,其实是我母亲幼年时的奶妈,后来又把她从湖南带到北平,跟了一辈子。保姆非常疼爱我,后来患了脑溢血,瘫痪在床多年,一直住在我家,直到病故。我哥哥也有个保姆专门带他。回头看,虽然当时中国很动荡,我的童年还是安宁、舒适的,和同辈人相比,我可以说是幸运的。
我们家的摆设比较新派,没什么老式红木家具,多是西式的沙发、桌、椅、床。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已很新潮。我家的宅子很传统,充满中国味道,雕花刻工非常讲究。两间主房的顶上都有个小阁楼,不让上去,以前专门放置皇帝赐封的物品。几个屏风、隔断都是中式的。父亲学的是工科,但古文功底深厚,字也写得漂亮。他买了全套《二十四史》,装在四个玻璃柜子里。
院子的布局,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北屋,是正房。东西厢房,西厢房是客厅,很大的三间,内有卫生间。我家是中西合璧,现代的洗手间、浴室都有。北屋,三大间,两个耳房。耳房有一间比较大,也有卫生间、抽水马桶和盆浴。另一间耳房,后面有个走廊,通往外面一排房子。父亲买下宅子后,安装了当时还是奢侈品的自来水。用抽水马桶,必须得有自来水。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父亲怕打起仗来没水喝,专门在院子里打了一口手压机井,用水管直接通到厨房。当时,只有少数人家用得起,得专门接水管。北平最早的自来水公司成立于1908年。据史料记载,三十年代中叶,北平城里的自来水私家用户有两万多家。一般人家,都得靠外面送水。我们住的胡同,每天就有送水的。一个独轮车,两侧各挂着一桶水,挨家挨户送去。小时候,我们淘气,看到送水人来,就把他水桶的塞子一拔,一侧漏水,两边就失去平衡,独轮车就倒了。记得离我家不远,拐个弯儿,是黄花门大街,那里就有个送水站。
东厢房,是饭厅。里面还有个小房间,当客房。亲戚朋友来了,就住那儿。有个堂兄,名叫金贵铸,当时在北大念书,就住在客房。解放后,他当了上海耀龙化工厂的总工程师。东厢房背后,是个大厨房,有三大间。家里的大师傅在那里做菜。他只管做菜,食材多半由店家送货上门。我家的餐桌上,主要是苏杭江南的风味,合父亲的口味。母亲很小离开湖南到北平念书,已基本上不吃辣。
三十年代,家里还没用上煤气,全是烧煤。厨房的炉灶,两个大火眼,煤直接放在下面,用柴火点着。不是蜂窝煤,是一块一块的煤,多半来自山西,很容易燃烧,火苗大,厨房顶上有个天窗通风。如果煤不够,就要买煤粉做煤球,有专门摇煤的帮你摇成煤球。每户人家都有个小煤堆。屋里取暖,都用大炉子,挺高,有烟筒直接通出去。卧室、客房,都要装上取暖炉,铁的,放在房间中央。排烟管的管子是薄铁皮的,直接通出室外。冬天,佣人会帮助点火。晚上,得把炉子给焖上,一大早再挑起火来,加煤。每到冬天,就得把取暖管道装上,过了冬再拆下来。
记得还有个门房,在我们家待了几十年,快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离开的。他年轻时在平绥铁路当茶房,父亲挺喜欢他,就把他弄到家里做事了。他的家境困难,后来把老婆也从乡下接来了。他们没孩子,就住在门房里间。
那时,私家电话还很稀罕。北平的电话号码只有四位数,分区,各个区局不一样,都是邮电局接线员人工接驳。我家的电话,黑色的机子,就装在堂屋,一进门就是。印象中,使用率不低。比如,要买个面包,打个电话,附近的面包坊会送上门。母亲在家,寂寞时喜欢打个电话,跟闺蜜、朋友聊个天。当时,北平的家庭用电已比较普及。除了照明,收音机也开始时兴。当时,中国还没有国产收音机,父亲用的是一台RCA(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America)电子管收音机。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严令禁止收听短波。若搜查到短波收音机,则将短波装置剪断。事后,父亲又把短波接上,在家偷偷地收听。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我们很早就从短波那里知道了。收音机放在堂屋,正面有一个炕,木板的。父亲休息时,喜欢躺在炕上听收音机。有时母亲也躺着,听当地的电台。父亲英文好,常听BBC新闻。“文革”抄家,这台老收音机也没了。
三十年代,北平的现代邮政设施已基本健全,我家不远处就有个邮筒。如果要汇款,就得专门去地安门的邮局。邮差每天上门送信。父亲还订了些报纸,如《大公报》,还有份专业的英文杂志《美国工程评论》。
周末,家里常有客人拜访、餐叙,多半是父亲的下属,还有他留美时的同窗友人,包括康奈尔时期的老同学胡适。胡先生住在东厂胡同,父亲也去他那里走动。父亲有些医界的朋友,都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后来当过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也来过家里。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也是家里的座上宾。后来他当了美国驻华大使。毛主席曾为他写过“别了,司徒雷登”,我们这代中国人都知道他。
四岁时,我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父母把我送进一家幼儿园——孔德幼稚园。去幼稚园前,我在家里就是玩耍、游戏,有保姆看着我。不记得父母对我有过什么学前教育。我自小喜欢动手,喜欢把东西拆了再装,乐此不疲。过年时,一放炮竹,我就特别兴奋。当时北京有个中法大学,前身是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创立的法文预备学校。孔德幼稚园就是它创办的,在东华门。家里雇了人力车,每天送我和哥哥上学。哥哥比我高一班。每天一早去,下午两三点钟接回家。幼稚园里没有外国老师,都是中国人。除了各种游戏,就是跳舞、唱歌,也不念什么书,就是玩。听父母说过,我在幼稚园很爱哭,是出了名的。我不喜欢那里。一年后,我升上了孔德小学,那里教法语。父亲是留美的,觉得法语不那么有用。小学三年级后,就把我和我哥转到了育英小学,一所教会学校,就在灯市口。
我在育英一直读到初中毕业。育英是一所很有名的男校,完全采用新式教育。每班三十多人。小学四年级开始教英语。我后来英语较好,跟小学打下的基础很有关系。老师都是中国人,但英语都不错。课程有语文、算术、英文、常识,常识包括历史、地理。还有音乐、美术。除了唱歌,音乐课上还教过五线谱。老师弹钢琴,我们唱中外歌曲,包括圣诞歌、弥撒歌。可惜我天生不太喜爱音乐。父亲对西方古典音乐好像兴趣不大。他更喜爱中国的京剧。
育英学校对体育特别看重,玩各种球类,培养了我终身对体育的爱好。近些年,我喜欢打网球,就是受当年小学体育课的影响。日本人占据北平后,经常玩垒球。我们在院子里也学着打,把玻璃都打碎了。
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很严格。每逢寒暑假,他都专门请家庭教师为我们补习英语和古文。虽然受过西方教育,但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总想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超人”。如果成绩考得不好,我们在家里有时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记得有几次,他读完我们写的作文,大骂“狗屁”,把文章撕成碎片,撒了一地。他对我们的教诲很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宁人负我,勿我负人”,“不怕胯下之辱”。他做事认真,对我一生有极大影响。
小学毕业,我直升育英中学,后改名叫北京二十八中,旁边是贝满女中,也很有名,186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著名的校友包括曾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作家冰心、复旦校长谢希德、话剧演员孙维世等。因是私校,学费很贵。育英曾出过“双元金榜”,也就是初中、高中会考,冠军都出自育英。我的同学大部分家境优越,不少是富商、教授、医生、外交官的子弟,也有些留洋学生的孩子。当时北京的中学有四大名校,育英、贝满,汇文,还有慕贞女校。
1937年,日本入侵北平,我们家境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父亲回到北平已七年,在外资和华商银行有不少存款。上海的存款,因全部换成日元,加上手上的股票大跌,损失惨重。家里的佣人只剩下一个,车夫也没了。所有家产,只剩下北京这栋老房子。北平沦陷前,父亲还在平绥铁路局做事。他告诉家里,出事了,日本兵要进来。由于国民政府需要运兵,他被留在了北平。日本人占领北平、接管铁路后,他仍在铁路上做事,当了个参事的闲差。因为他不懂日文,反而避开了日本人。那几年,他很清闲,于他不全是坏事,趁此机会念了很多书。日本人不让中国人插手管理铁路,不信任他们,怕出纰漏,把华人工程师一旁晾着。父亲很郁闷,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只求谋个闲差,薪水减了不少。他仍然每天上班,消极怠工,自己找书看,研究钢结构。后来写了两本专著《钢构解法》和《超定结构解法》。
日本兵进城后,父母一度很紧张,我们还搬到北京饭店躲了一段时间。市面上的供应基本断了,没啥吃的,只有一种混合面。家里仅剩的一点面粉,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坑,埋了起来。
有件事值得一提。父亲毕生最大的愿望是为中国造桥。他的康奈尔校友、桥梁学家茅以升主持的钱塘江大桥工程,是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其中的钢结构部分就是他参与设计的。茅以升学的是桥梁工程。该桥的铁路桥和公路桥于1937年9月和11月分别落成通车,全长1453米。大桥通车后八十九天,日军逼近杭州,为抵御日军南下,保护杭州百姓,茅以升先生不得不亲手把桥炸毁。当时,茅先生立言:“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将来。”抗战胜利后,开始修复,1948年完成。
高中时,父亲把我转到了北平河北高中。部分原因是家况不如从前,教会学校学费太贵。后来我哥哥上了辅仁大学,是私校,学费难以凑齐,还是找我舅舅借的钱。北平沦陷后,学校里驻有日本教官,教日语。我从没念过日语。转学后,坐在教室第一排。日本教官让我起立念日文,我念不出来。他以为我不理睬他,差点挨了耳光。有段时间,父亲觉得我们应该学点日文,就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找了一个日本青年,教我们口语。但是我心里仇视日本人,根本学不进去,八年下来毫无长进。为什么仇日?因为切身遭遇。譬如,我们出西直门,日本兵要搜身。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聊聊时事,就给日本人抓走了。我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一直持续到现在。世界五大洲,我跑过不少国家,但只去过两次日本,不愿意去。虽然我有不少日本朋友,但还是不想去。对日本缺乏好感,是我们这代中国人的集体情结。
北平沦陷期间,我家有位常客,名叫方亮,本名方观赫,朝鲜族,是协和医院的年轻医生。后来他投奔了解放区,又偷着跑回北平,寄宿在我家,就住在西厢房。家人碰巧在沙发缝里发现一些中共宣传品,才确认他是地下党员。他留起了小胡子,使自己显得老成些。此人胆子奇大,开着三轮摩托车到处跑,偶尔也带我外出兜风。他对外的身份是协和医学院讲师,后来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我父亲受他影响挺大。1949年,解放军进城,父亲有些害怕。那时有传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是方亮打消了父亲的焦虑。解放后,他成为著名的医学微生物学家,出任西安医学院副院长,还是中国抗美援朝反细菌战检验队副队长,奔赴朝鲜前线。他是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最早成员之一,跟创办人许德珩一起,把我父亲介绍进了九三学社。
河北高中离我们家很近。它建于1902年,前身是顺天高等学堂。当年,河北的乡绅名门,对当地学校不满意,凑钱兴学,为子弟们在京城建了这所学校,校园很大。1933年改名河北高中,出过很多人才,成了名校,后来更名北京一四四中,现在没了。
上中学时,我不是个好学生,爱玩,不关心政治。班上有很多富家子弟,京剧名家马连良的儿子与我同班,还有一些名医的孩子。上了高中,我发现一些教师很可能是共产党人。比如,我的英语教师,常在课堂里跟同学聊国家大事,同学们都爱听。突然,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又放回来。事后,我们再让他聊时事,他说不聊了。还有我们的生物教师,挺好的,至少也是亲共的,学生都看出来了。班上也很分化,一部分同学靠近三青团,另一部分人思想比较激进,亲共。后来上了大学,就更明显。一个班里,哪些亲共,哪些亲国民党,哪些逍遥中立,阵营分明。争论政治问题时,观点很是不同,已形成明显的派别。
对考试,我不太在乎,成绩在班上居中游。那年头,考试成绩单都由邮差送到家里。一看考得不好,父亲就会惩罚我们,狠狠骂一顿,也不带我们去北海公园了。他希望子女出人头地。我心里很明白。
对身外之物,父亲看得很轻。他父母的遗产,他一丁点都没要,只留了母亲一只金手镯,作为纪念。他相信个人自立。那个金手镯在抗美援朝时捐了出去。四个孩子中,父亲最喜欢我帮他张罗做事。大概是我处人接物还不错。父亲最偏心的当然是我妹妹。她排行最小,小我四岁,又是唯一的女孩,学习还特别出色。我哥跟我的成绩都一般。他考大学时,工科学校只有一所,也就是“伪北大工学”。他没考上,最后去了私立的辅仁大学,学化学。因为他没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害得我也紧张起来。
高中时我曾想过,毕业后去陪都重庆投身抗战。毕业那年,抗战胜利了。父亲偷听VOA(美国之音)短波,第一时间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新闻,我们都非常兴奋。日本投降后,在北平的日本侨民狼狈不堪。父亲后来在帅府园还买过一处大房子,三十多间屋,租了出去,有些房客是日本侨民。当时,他们逃难似的,家当都扔掉了,分批撤离回国。在东北,不少日本人把孩子留在了中国。印象中,日本侨民撤离时,北平还比较稳定,没出大的乱子,也没听说日本人遭报复或被杀的事件。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我目击了国军接管北平的情景:大街上,都是欢呼的市民,挥舞的标语,我也上了街。四年后的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我看到了同样的欢呼景象。国民党接收大员进驻后,认为父亲这批人都在日本人的机关工作过,想扣他们汉奸的帽子。他决定不干了,离开了工作二十年的铁路业,转去北大工学院教书。国民党接收大员很跋扈,自认是胜利者,很多事情没处理好。
1946年,我考入北洋大学北平部,攻读机械。北洋大学,1895年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就是现今天津大学的前身。后来,它的北平校区并入了北大。我的大学时代,正值国共内战,民心浮动,经济低迷,后来又是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不得人心,民间怨声一片。我和同学就曾上街游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
大学一年级,不分系,只分甲乙丙班,上基础课。我在甲班,三十余人。记得教数学的是王永皋教授,留日的。教中文的是徐凌霄教授,曾是《申报》驻京记者,他是个名记者,也是个剧评家。英语老师是一位姓陈的教授,一位官员夫人,使用的教材是燕京大学陈福田教授编著的。很多课程由清华教授担任。那时,教授工资微薄,为了生计都愿意到其他学校兼课。“工程力学”“材料力学”是屠守锷教授上的,浙江人,麻省理工毕业,讲课条理清晰。“工程制图”“热工学”是董树屏教授,水力学是李丕济教授。钱伟长教授当时也在北大兼课。电工学是唐统一教授。唐是育英学校校友,北京会考的“双元”金匾获得者,其父唐悦良是我父亲庚款奖学金的留美同学。水力学是夏震寰教授。内燃机是宁幌教授。记得还有两位德国教授,William教授教“机械设计”,Beister教授教“机车设计”。因为师资阵容很强,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考试很严格,出题难,及格都够呛。最后老师无奈之下,只能用“开方乘十”来打分,否则就很少人及格了。
念完一年级,正值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CC派与中央争夺日伪时期北大工学院的校园,即端王府——那时已被北洋大学占了。北京大学工学院刚刚创建,校址很小,原来是一所日本人的小学。1947年,北洋大学北平部的归属让学生们很不安。多数学生希望并入北大。北大工学院校友刊物中提及:有学生知道父亲与胡适先生是康奈尔留学时的好友,就找父亲陈情,希望他说服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父亲答应转告。后来,北洋北平部如同学所愿,并入了北大。事后他表示,因为他为合并之事找过胡适,所以不能出任合并后的土木工程系主任,避免利益冲突的嫌疑。不过,据我的了解,合并事父亲似乎没有介入。我们北洋大学北平部的学生可自由选择,或留在北洋大学,或选北京大学。因家在北平,我就选了北大。我住在家里,每天走读,同学间来往甚少,上完课就回家了。
当时中国的知名大学是严进严出,考进去不易,毕业也很难。我读书时,北大的淘汰率很高,两门不及格就得退学。进校时同班有三十个同学,毕业时只剩下了十二个,还包括几位是上一届留级下来的。除了学业成绩,也跟当年国家处于危亡时期有关。部分同学因为对共产党有好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弃学投奔延安解放区。
1947年至1948年间,在北大任教的父亲被清华借聘两个学期,就在土木工程系,主讲高等结构学。借聘报告由时任系主任陶葆楷先生呈报叶企孙先生,时任理学院院长。第一学期,每周授课四小时;第二学期,每周授课两小时。校史馆还存有当年聘书的原件,月薪是现大洋二百八十元。聘书由梅贻琦校长最后签发,他是父亲当年同期赴美留学的同学。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进步学生开始到中学做宣传,动员大家出来迎接解放军进城。我也去了。傅作义将军跟共产党人谈妥后,城外毛泽东的军队就开进来了。我们上街迎接解放军。清华在北平城外,先解放。北大在城里。清华很多学生跑到我们城里做宣传工作,迎接北平城和平解放。虽然,清华比北大更早解放,但是北大学生的政治民主意识比清华活跃,最早接触新的思潮。这是有历史的。
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我还有印象。学校组织师生参加开国盛典。大家排着队,大清早就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同学们都很兴奋。那是很特别的一天,我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我们从底下往城楼上看,很清楚。这是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以前读进步书籍时看到过他的相片。解放时,父亲仍在北大教书。他的日常起居并没有明显变化,以前他喜欢穿长衫,现在改穿新派的中山装,都是服装店里现成买的,灰色毛料的那种。那时只有灰色和蓝色两种。原先他一直留着胡子,显得很老成。解放后不久,他把胡子剃了。我也穿上了中山装。建国初期,国家崇尚节俭,穿着都不讲究。毕业留校后,我在清华上四百人的大课,裤子屁股上破了,贴个补丁,学生也不觉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