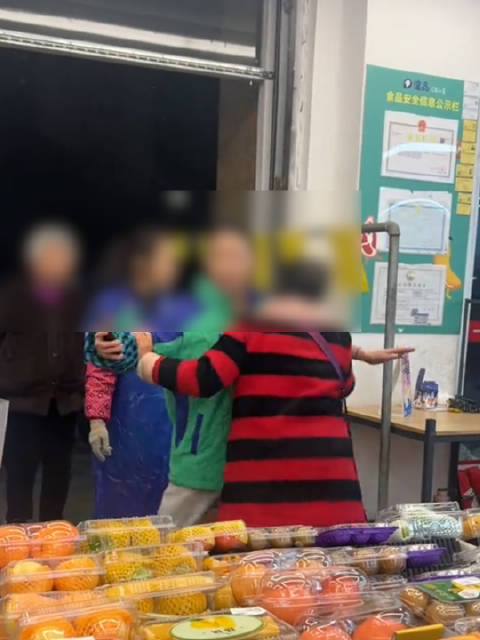林登在云南喜洲喜林苑“小小图书馆”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
布莱恩·林登,1962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84年获中国政府奖学金到中国求学,2004年定居云南喜洲,致力于保护与修复中国物质文化遗产,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10月底,云南大理喜洲入秋,成片的绿色稻田多了一抹金黄。喜洲位于洱海西岸,是一座白族古镇,白族居民占80%以上。镇上保留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白族古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
美国人布莱恩·林登已在喜洲定居多年。“我是林登,来自芝加哥。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4年,现在住在大理喜洲,在这里度过了非常快乐的20年。”这是他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时的开场白。
“林村长好啊!”
林登在喜洲开了一家民宿,名叫喜林苑。在整个大理,这家民宿名气不小。
采访当天早上8点,《环球人物》记者一行来到喜林苑。记者刚进大门,林登就热情地打招呼:“哈喽,欢迎欢迎!”林登是个大高个,跟记者挨个握手时,他会微微弯下腰。为了迎接“从北方来的客人”,他甚至准备了一壶二锅头,“要和你们聊个痛快”。
走进喜林苑,穿过长长的回廊,林登开始跟记者讲解宅院的各个角落,如数家珍。穿过大厅时,林登会和每一位住客问好:“Good Morning(早上好)!”“睡得好吗?”“今天的咖啡很香哦。”来到餐厅,恰巧遇到一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林登又拉着她跟记者介绍:“这是张大姐,我们喜林苑的元老。”张大姐立马放下手里的碗碟,笑着拍拍林登的胳膊,对着记者的镜头说:“欢迎欢迎。”
林登带记者参观了喜林苑的“小小图书馆”。这间约10平方米的屋子是林登的得意之作。走进屋子,中间是张大木头案几,案几上放着制作大理“非遗”甲马的木制刻板。案几后,书柜占满了整整一面墙,书架上摆放着各种文字的书,都是讲中国故事的。当初开设喜林苑时,林登特地腾出了这个房间,免费对喜洲村民和游客开放。“我们经常在这里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邀请大家来玩。”


林登与助手一同制作大理“非遗”甲马。
总之,在喜林苑溜达一圈,处处是美景,林登骄傲地介绍个不停。
喜林苑所处的四方街也常有林登的身影。四方街是喜洲最热闹的商业街,人来人往,商户叫卖声阵阵。每天下午四五点,林登都会穿过这条街,往街尾的喜林苑分店赶。
因为去得多了,林登成了商户们的老朋友。路过一家奶茶店,他停下来朝店里挥手:“嘿!兄弟,今天生意好吗?”溜达两步,来到一位白族老奶奶支起的水果摊旁,他用白族话问好:“niqiuniqiu(意为你好)。”而路上的喜洲人见到林登,都会这样跟他打招呼——“林村长好啊!”
时间回到20年前,林登刚在喜洲落脚。那时的喜林苑还是一座无人问津的老宅,四方街也远没有今天这般热闹。那时的林登从没想过会在喜洲扎根,更没料到会成为喜洲人的“村长”。
2004年的一天,林登在昆明登上午夜的火车,在蒙蒙细雨的凌晨抵达大理。第二天,林登走进喜洲的一家面馆,交到了他在这里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林登坐下,要了碗酸辣面,闷头大快朵颐。邻桌的食客和他打招呼,先是隔着桌聊,后来干脆端起自己那碗面,和林登拼桌聊。面馆老板娘见状,递上一壶自酿果酒助兴。就这样,第一次见面,文化背景相去甚远的两个人把酒言欢。那食客名叫杨龙,是喜洲当地的画家,后来成了林登的挚友。
“我去过非常多国家,游览过许多地方,喜洲给了我独一无二的亲切感。”林登说,“走在路上,每个人都跟我咧嘴笑,每家小店都欢迎我。喜洲人看着我,根本不觉得我是个‘老外’,而把我看成了又一个少数民族——‘美国族’朋友。”这种“包容性”让林登无法抗拒。
喜洲的生命力不止于此。在一座座白族传统院落中,林登触摸到延续数百年的文化内核。
到喜洲后不久,杨龙带林登参观了一座白族古宅。林登跟记者聊起他第一次走进那座宅子时的震撼:“宅子大门处的回廊上的木雕和石雕,看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那天晚上,他就想着要修复这座古宅,“兴奋得睡不着”。在杨龙的介绍下,林登认识了喜洲镇政府工作人员。一番商讨下,双方达成协议,修复正式启动。
林登对古宅的修缮遵循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他给宅子铺设了自来水管,修建了蓄水池,还请专家修复了那些精美的木雕与石雕,用发酵后的猪血制成打底用的腻子给木器刷上。但宅子原有的木质结构丝毫没变,就连采光不佳的小窗也被保留了下来。林登认为,“这是最真实的中国的美”。
两年后,宅院修复完成。这便是喜林苑。
“中国比美国更像家乡”
林登和喜洲的故事始于20年前,他初识中国则更早。
1962年,林登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家境不好,父母识字不多。来中国前,他是一名地毯清洗工,打零工之余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对当时的中国,林登一无所知。
 上世纪80年代,林登(左一)第一次来中国,与中国孩子们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林登(左一)第一次来中国,与中国孩子们在一起。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登在夜校公示栏看到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的消息。他写了一封申请信,成功获得奖学金,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求学,后来又去南京大学深造。一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就这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那年,22岁的林登第一次出现在北京街头,穿着芝加哥小熊棒球队背心、短裤和皮凉鞋,戴着中式军帽,被身着白背心的北京“的哥”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那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围观人群对“老外”林登表现出“天真无邪的好奇”。
文化的差异没能挡住北京人对林登的热情。林登跟记者回忆,他曾在一家游泳馆的水池里丢过一片隐形眼镜。当时在北京很难买到隐形眼镜,林登说自己成了“独眼龙”。就在对找到镜片不抱任何希望时,他被通知去游泳馆“认领”。“我到了游泳馆,只见3个人围着一片透明小圆片,就像惊奇观望着大峡谷的游客”。
到中国后,林登开始疯狂地学中文,“一开始没有什么长进,只能边比划边说”。不过,即便中文说得蹩脚,但丝毫不影响他探索广袤的中华大地。在中国的这几年,林登去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也曾游历西部的农村——“那里有最古老的中国”。也是这几年,林登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学业,参加了一部中国电影的拍摄,还加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团队,完成了几十次关于中国的报道。1988年,林登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时,已经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了解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并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了。
 林登与妻子瑾妮。
林登与妻子瑾妮。在中国,林登收获了爱情。1987年,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遇见了瑾妮。瑾妮是出生于旧金山的华人,当时在南京大学作交换生。1993年,他们在美国结婚,后来有了两个儿子——沙恩和布莱斯。2003年,林登带着妻儿回到中国。2004年,他和瑾妮做了个疯狂的决定:卖掉美国的所有房产,带两个儿子定居喜洲。
林登说:“瑾妮和我一样,她太爱喜洲了。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在中国长大。刚来中国时,老大沙恩8岁,老二布莱斯5岁。沙恩现在已经订婚,未婚妻是个美裔荷兰姑娘。他们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美国。布莱斯学环境工程,喜欢武术,中文说得比我好,现在正在参与喜林苑的改造工程。他们都觉得,中国比美国更像家乡。”
 林登行走在喜洲稻田。
林登行走在喜洲稻田。村民有hope(希望)
这两段“中国生活”带给林登的最大感触是——“变化实在太大了!”
林登记得,他第一次来中国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要坐1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要坐10多个小时的大巴。当时,能接待外国游客的旅店也不多。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旅游市场尚未成形,游山玩水的人不多,更别提外国游客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林登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从昆明到大理,曾经10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坐两个小时高铁就能到。在喜洲,有各种酒店和民宿供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选择。即便在中国农村,人们也不再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长得不太一样的‘老外’。在21世纪初,这种‘聚光灯效应’就已经消失。现在,外国人在中国已经非常常见了。”
“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持续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喜洲的医疗和教育越来越好。比如,以前我看牙去上海,现在就在大理的医院看,大理医院的机器同样先进。”林登说。
林登还认为,这种发展带给人们的改变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我看到,喜洲的老人们过得很幸福。他们会自己网购,去快递站取包裹。老爷爷老奶奶们有时候也会偶尔‘抱怨’几句,因为旅游业发展得太好,游客太多太拥挤,这听起来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我还看到,前些年一些大理年轻人跑到外省打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又回来了。他们带回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帮助自己的家乡发展得更好、建设得更美。”
“如果用一个英文单词形容村民的精神面貌,那就是hope(希望)。这个hope非常重要。我喜洲的朋友有hope,隔壁石龙村的村民有hope,我作为一个长住中国的‘老外’,也有hope。但我必须要说,在美国乡村,并没有看到这么多hope,也感受不到这么多乐观的情绪。”林登说。
当初开喜林苑时,林登有一个想法,希望将这座白族院落打造成“讲述真实中国故事的平台”。“许多西方人从未来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他们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加深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这些描述跟我和瑾妮所认识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爱中国,我们想帮助美国邻居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
于是,这些年,在喜林苑的住客名单上,有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在内的官员,还有《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的记者团。“昨天,我带领一个荷兰旅游团走进喜洲村庄,其中有个人激动地跟我说,‘真没想到,中国农村这么富裕,中国人民这么热情!’”
林登说:“中国从不缺改革的勇气。这份魄力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激励了我和家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踏实奋斗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