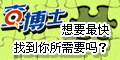| 一位非典感染者的口述实录:我与非典相伴的日子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19日11:52 青年参考 | |
|
相关专题:< 各地周密部署严防非典反弹专题 > 假设SARS再次爆发,我会去做志愿者,到发热门诊的一线去救助感染者。即使身体里没有抗体我也会去! 口述:某杂志采编部主任礼露 采访并整理:本报记者吴珊 时间:2003年11月15日 感染了SARS却没有医院收治 我是国内第一个以真实姓名发表意见的SARS病患者。今年4月7日我陪朋友去人民医院看病, 10号就开始发烧。13号我去人民医院检查,白血球低、淋巴低,但肺片没有改变,16号我又去复诊,当时胸透肺部已出现阴影,但是医生还是不给确诊,……那时整个北京的SARS防治应急体系还没建立,对SARS病人特别排斥。 在没有医院收治而自己的身体状况又越来越差的那段时间里,我想到了自杀。我把遗嘱都写好了,也和寄养在外地的儿子通了电话告了别。我可以上医院去打吊针,这样我身上才会有点劲,但是打针会传染别人,那时就觉得自己是社会的祸害,自己都厌恶自己,所以就想到自杀。我后来去厨房看我那把刀,刀很锋利。现在我想,我是住在一楼,如果我住在高层可能就真的自杀了。 在这期间我也上网查找大量的关于SARS的信息,读到的资料都说感染SARS之后如果肺部出现阴影5-6天就会死亡。从我发病到意识到死亡降临,那种恐惧无以言表。 濒死时爬上120救护车 后来事情有了转机。我有个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在《人民日报》做记者,叫常莉。她马上找了报社的同事白剑峰,白剑峰半夜加班写内参在《人民日报》上反映我的情况,还亲自联系了佑安医院、地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的院长,但是他们还都答复无法收治。应该是《人民日报》的内参起了作用。第二天,人民医院的院长吕厚山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我家向我道歉。上午副院长王吉善(音)就亲自到我家里来了。开口就说“你对我们医院有什么意见吗?听说你把我们给告了!”。……我说不出话来。以我5进5出人民医院所见所闻,我清楚,医院是最大的传染源。 常莉帮我查到我的小学同学在协和医院做副院长的于晓初。4月20日,于晓初知道我仍然高烧不退,明确打电话指示我,“你叫120救护车马上来,实在不行打出租车,到协和医院来,我们收治你。”大概两个小时之后,120救护车开到我门前,我几乎爬是着上了车,当时嘴唇和手心都已经发黑,已经是濒死状态了,我就这样被协和医院收诊下来。 “25条建议”和捐献血清 进入5月,全国的SARS防治就越来越得到重视,感染者也得到了很好的救治。但是我住院期间也亲眼看到6个人死去,最近的是邻床。 5月20日我给沈阳市长写了一封信,因为我是沈阳人,我不想北京的悲剧在沈阳重演。这封信后来被《沈阳今报》的编辑编成了“25条建议”发表,被沈阳市民一抢而空。5月26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是怎样染上非典的——九位SARS患者的自诉》,以口述实录的形式谈当时大家特别关注的SARS感染源问题,但没有谈我自己。 我出院后恢复得很快,8月13日我和我的病友苏庆国和姜成营为WHO(世界卫生组织)和北京市卫生局合作的一个SARS研究机构去献血清,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检查出来有SARS抗体。我知道不是所有的SARS感染者身上都能产生抗体的,要高烧8天以上的重症患者才会有,而且听说抗体半年之有可能会自动减弱甚至消失。我产生了那种献身的冲动,也因为是协和医院的王仲医生和我联系的这个事,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开始说是献150毫升。但是等到了献血的前夜,又改口说要献300毫升。我想了一下还是献了。我们领到了3000块钱营养费,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血清是无价之宝,仅仅为钱,我们都不会冒这个险的。我们是不想让别人再遭我们这个罪了。 回家之后我就感觉身体开始出问题,头晕,血压高,两个月体重增加了16斤。站着脚后跟就疼。有时候也会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去献血?”后来了解到全国大概有70多位SARS痊愈者捐献了血清,北京有20多人,我可能是年龄最大的捐献者,因为他们规定45岁以上的一般不让献,而我已经49岁了。 出院后病友们的三次聚会 出院后我们病友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经常联系,还组织了几次聚会。 第一次是我出院,先出院的病友和她的家属来给我接风。我们6个人到东来顺聚餐,那时都还带着口罩,大家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说话,态度很谨慎谦卑。 第二次是我给出院的同屋的病友接风。第三次是11月2日在我家里的大聚会。来了20多个病友,有农民、出租车司机、民工、学生和公司职员。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才20岁,这是我们出院后最大的一次聚会。那天的气氛非常好,我弟弟在给我们照集体照的时候手都在发抖,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病友之间会有这样的感情”。 协和医院当时一线救助我们的急诊部主任王仲医生和呼吸科的许文兵医生也来了,之前王仲给我EMAIL说,“你们病友的活动非常有意思,以后能带上我吗?”在聚会的现场,王仲医生说,“今天我们能在这这么快乐地聚会,是因为我们都是活下来的人。”我们病友和王仲医生的关系都非常好,出院之后还经常联系,我就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像王医生许医生这么好的人。 那天很多病友带来了鲜花,我在大家面前把当时救助我们的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名单念了一遍,大家都热烈鼓掌,发自内心地感激。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医护人员长什么样。我们这些人对医生的感情很特殊。因为我们都是早期的SARS感染者,很多人都有十几天发高烧住不了院的经历。所以大家在谈到那段时间的感受时,都不约而同地会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最后,协和总算收了我”,我想,得了这样的传染病,没人收治,这是北京防治SARS前期的耻辱。 未来,我还想组织一次更大的个人聚会,邀请在我感染SARS之后最困难的时候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在国内外都有很多朋友,为我住院的事他们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还有人给吴仪写信,在网上发帖子。我住院期间很多朋友以各种形式帮助,鼓励我……我孩子的同学的妈妈,至今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被我染上的,她在我刚发烧的时候就来给我送水果,放在厅里就走了,根本没和我照面,但她后来和和她儿子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又来一次,把包好的馄炖送到我家门口,放在外面地上,铺着报纸,人也并没有进来。那时我还没住院,一个人在家,几天没吃东西了,那几个馄炖还真救了我的命。后来是我在还没出院的情况下给她叫的救护车。她给我送馄炖时他的儿子龙龙还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感人。我到现在还保留着患病期间所有朋友给我写的信,只有这一封当时留在家里不见了,很可惜。 帮帮这个20岁的孩子 出院后,周围的人对我们这些感染过SARS的人抱有戒心,现在也一样。很多人丢掉了工作,包括他们身边的亲人也受到牵连。……很多人因此没了升迁的机会,说到这些他们非常难受。 那个20岁的民工小伙子,原先在北京金港101工地打工,出院之后回去一看,他的锅碗瓢盆行李等等都让人一把火给烧了,工钱不给发,工作也丢了。他们那个工地共有11个人感染了SARS,都一样的遭遇…… 当时他找不到工作又没有钱的时候就只有找病友帮忙,衣服、被子甚至裤衩都是我给他的,很可怜。这个孩子在家也是独生子,我就在想,别的20岁的孩子在家还很是娇惯的吧,而他已经经历了这些!就是这样的孩子也曾捐献血清救助别人救助社会,可社会对他怎样?。我们这些感染过SARS病毒的人,至今为止只收到过香港工商界“关怀非典受难者基金”的一次捐助——活下来的给2000块钱,死去的给1万。这是我们得到的唯一的救助款。 SARS是种比任何传染病都可怕的病,我自己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我还得考虑周围的人。 ……我去献血清其实也就是不想再有人去承受这种痛苦了。肉体上的痛苦形形色色,很多濒死的人都经历过,SARS也不例外。但是最痛苦的还是精神上的,SARS病人在社会、心理、感情上所承受的压力甚至比艾滋病人更大。回想我爬上120救护车的那个场景,我就会想,SARS病人是最可怜的,就是死囚犯走上囚车时站不稳旁边都会有人扶你一把,但是不会有人去扶SARS病人的。 但是SARS不会再来一次了,我认为不可能重来了。王仲医生也这么认为。北京的医院当时的那种表现太可怕了,所以才会出现后来SARS的泛滥。当然,即使再来一次,我也不怕,我认为社会上也会相对理智的对待它。我表示过,假设SARS再次爆发,我会去做志愿者,到发热门诊的一线,帮助救助感染者,因为我太知道了,一个人在那种时候需要什么,即使身体里没有抗体我也会去。 声明:《青年参考》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各地周密部署严防非典反弹专题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