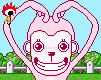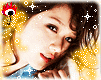| 我国对免费治艾滋人群作规定 聚焦疫区药物试验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14日01:15 东方早报 | |||||||||
|
东方早报特派记者 高英雄 发自河南商丘 昨天,卫生部、财政部公布了《艾滋病及常见机会性感染免、减费药物治疗管理办法》,对免费治疗艾滋病的适应人群及免、减范围作了详细规定。 事实上,在艾滋疫情高发区,我国政府正在极力推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对农
昨天颁布的《办法》实际上是对我国既有艾滋病防治政策的一次细化,其中不乏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对疫情较重地区经济困难的艾滋病病人常见机会性感染治疗药品费用给予适当免、减等等。对于挣扎在贫困和生死线双重边缘的艾滋病人来说,我国政府的这些举措无疑是雪中送炭。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艾滋病疫情高发区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由于政策的扶持,使得艾滋药物的生产可能成为一块利润巨大的蛋糕,现在,很多双眼睛正盯着这块蛋糕,他们也将触角伸向了艾滋疫区。 一次典型的艾滋药物试验 2004年2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属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伦理委员会的一纸调查结论,让河南省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的18位艾滋村民有一些心凉,调查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双庙村艾滋村民朱茂龙和朱瑞华的死亡与北京某大医院进行的药物试验有关。 去年2月20日,双庙村村民朱进中领着北京某大医院的几位医生来到村子里,那天晚上,北京来的医生在村卫生所抽取了120个村民的血。10天后,村里的广播通知其中的18个村民到朱进中那里交钱,以购买到北京去的火车票。 双庙村是一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全村3800多村民,已有150多人死于艾滋病,已经检测出来有480多位艾滋病感染者。这18个村民正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此行将到北京那家大医院参加一项药物试验。 第二天,18个村民来到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医院,做完体检后,他们被安排在一区病房。在这里,同他们一起参加药物试验的,还有来自河南睢县艾滋疫区的10多名感染者。 张国胜是参加试验的18个村民中的一个。他回忆说,村民们在医院接受了10多天的观察,然后,医院让每一个村民在一份复印好了的材料上签了名,然后又收上去。张所说的“复印的材料”其实是一份“患者知情同意书”。这份患者知情同意书确认,每一个参加药物试验的村民将接受16针的药物注射。 李凤兰是另一位参加了此次药物试验的村民。她说,在打针前,医院里的一位医生曾告诉她,这一针值1000多块钱,“至少能将你的生命延长20年”。 昂贵的针剂来自美国。实际上,这次药物试验是美国一家病毒基因公司与北京某医院联合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目的是对胸腺核蛋白制剂用于治疗艾滋病HIV-1感染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试验。 参加试验的村民们每周注射两次,一般是在周四和周五,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观察。试验一直持续到非典爆发,医院安排专车将村民们送回了家———实际上,他们在离家10多里地的一个地方隔离了近半个月后才真正回到家里。后来,村民们每个月还要去医院一次,抽血化验,一共又去了3次。 在药物试验进行到观察阶段期间,18个村民中有2个相继死亡,他们是朱茂龙和朱瑞华。2004年3月,另一位参加了这次药物试验的村民———张国胜的妻子也黯然去世。 张国胜说,在参加药物试验前,他妻子“身体状况较好”。他感到很疑惑,“总不能说她的死与试验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艾滋疫区成了药物试验场? 双庙村艾滋感染者参加药物试验始于2001年4月。 当时,村子里阴云密布,每隔一两天就有人死去,有时甚至一天死好几个人,“死得让人胆战心惊”。村民们没有办法,只好到北京找医院求援。 村民们没有钱,他们寻找着各种各样能够减免治疗费用的机会,这些机会少得可怜———只有医药厂家找医院试验艾滋新药时,幸运才会降临到村民们的头上。 2001年11月份,朱进中到北京某医院参加了一次药物试验,和他同去的还有6位村民,其中包括朱进中的父亲。不过,那次试验的是中药,每个试验者还交了500元钱,后来,医院将这些钱作为路费返还给了村民,也没有收村民们的生活费和住院费。 从那时起,能够参加药物试验逐渐成为了村民们的一项待遇,甚至是一种荣耀。“管吃管住,治病还不要钱,这么好的事,谁不愿意去?”一位51岁的艾滋村民说。 朱进中描述了村民们争先恐后参加药物试验的场景。去年8月,北京某中医研究所让他帮忙在双庙村找50名药物试验者,没想到一下子来了500多个报名者,把朱进中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双庙村的村民外,附近十里八村的感染者也闻讯而来,而有限的试验名额却让那些落选的感染者怅然若失。 双庙村共有40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一位村民说,村里没有参加过药物试验的人少之又少,有的感染者甚至参加过多项药物试验。 在双庙村进行药物试验的主要是北京的几家医院,有的医院已经在双庙进行过三四个试验项目。 一般情况下,药物生产厂家先找到医院,医院然后再找到村民。有意思的是,北京的这几家医院在双庙村都有自己的联系人,这些联系人大多是村子里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活跃者,他们与北京这几家医院的艾滋病治疗方面的医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而一旦这些医院有药物试验项目时,这些联系人就能很快地组织起一批试验者队伍。 有村民怀疑这些联系者是不是能从药物试验中捞到什么好处。一位村民说,为某医院联系药物试验者的谭德良“以前是血头”,就是他的抽血机器给村子里的乡亲们带来了艾滋病这一灭顶之灾。 谭德良的血站被取缔后,他被判了有期徒刑,后来保外就医。现在,谭每次带领10多个感染者到北京去试验药物,他每次也可以从医院支付给病人的报酬中赚取一些钱。不过,尽管如此,村民们对谭德良仍然充满着感激,因为“他能为村民们找来不要钱的药”。 丞待规范的艾滋药物试验 2003年下半年,参加北京某医院胸腺核蛋白制剂药物试验的双庙村18位村民,与该医院打起了“官司”,他们希望医院方面支付药物试验期间的生活补助费、误工费,以及试验观察期间对症治疗费用,总计每人1.2万元。这一“官司”最后不了了之。 不过,正是这起“官司”,使艾滋病疫区混乱的药物试验状况呈现于世,其中所潜藏的药物试验伦理道德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对于临床用药和艾滋病治疗,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除了《中医药条例》、《药品管理办法》等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明确规定,“受试者的权益、安全和健康必须高于对科学和社会利益的考虑”,而且,药物的临床试验必须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核。 然而,据中国CDC下属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伦理委员会对北京某医院胸腺核蛋白制剂药物试验的调查,这次试验事先并没有通过伦理审查。 “这是对人的生命和伦理的极大不尊重。”一位长期从事艾滋病权益保护的民间人士说。在艾滋疫区进行的药物试验,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伦理审查。 据了解,各种各样的艾滋药物试验不仅在河南省柘城县双庙村存在,在我国其他艾滋病疫情高发区均不同程序地存在着。试验的组织者除了北京等地的正规医疗机构外,还有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私人制药公司和一些江湖“游医”。 双庙村的村民们告诉记者,半个月前,一位来自山东的“游医”夹着包走进了双庙村,他自称能根治艾滋病。其方法是让病人躺在床上,将水银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药物混在一起加热,然后用蒸气熏病人的身体。双庙村五组的两个感染者参加了这次“药物试验”,试验还没结束,人就发烧,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医生检查说是“汞中毒”,那个山东的“游医”事发后也不知所终。 然而,即使没有经过伦理审查,艾滋疫区的村民们对艾滋药物试验仍然趋之若鹜,对他们来说,一次试验就是一次机会,而多一次机会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4月12日,记者到双庙村没有见到谭德良,当天一大早,他包了一辆面包车,拉着10多个村民又到北京去了,听说这次试验的“是一种胶囊”。 相关专题:中国积极防治艾滋病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积极防治艾滋病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