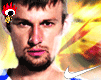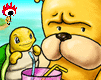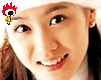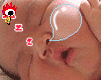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新民周刊特稿:杭州“回炉药”之祸(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9日11:24 新民周刊 | |||||||||
 过期药地下市场已非杭州城特有现象
撰稿/杨 江(记者) 过期药“还魂”再生,已经不再是几个无良商贩的小打小闹。 在一些城市,记者发现过期药地下市场已经出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帮派的药贩通过各种渠道回收过期失效药,在地下仓库翻新后贩卖至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在药厂,有人告诉记者,把退回的过期药品“还魂”后重新包装上市,已经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一些医院和药店的业内人士自曝黑幕:他们会帮助合作伙伴——药厂,在病人身上“消化”过期药。 三条黑色产业链触目惊心,违法者在利益驱动下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药品“有效期”是指药品在一定的贮存条件下,能够保持质量的期限。一旦过了这个有效期,按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就将成为劣药。借用一位药学专家的话说:从严格意义上讲,过期药物已经是一种医疗垃圾。药物过期不仅会导致药效降低或失效,甚至可能增加毒性。 一组数据令我们无法轻松:国家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推算,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病人达250万。在住院病人中,每年约有19.2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更可怕的是,审视三条黑色产业链时可以发现,过期药“还魂”过程中鲜见强有力的监管力量。 篇一:聚焦杭城药贩帮派 撰稿/杨 江(记者) 药贩被擒 “过期药地下市场就像牛皮癣,很难彻底治理。”杭州市药监局局长郭泰鸿回忆端掉最大两个制售假劣药窝点的经过,脸色很不轻松。 2004年4月29日上午10点,杭州市徐家埠。 一对中年男女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在附近转了一个大圈子后,终于在1弄3号门口停下脚步。两个人四处张望一番,神色紧张地走进大楼。5分钟后,十多名药监人员与公安干警开进了二楼一间出租房。那对中年男女已经不见踪影,只有一个男子愣在那里,苍白面孔上写满惊愕。 这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仓库,闷热潮湿,地面上凌乱堆放着一大堆“络活喜”、“阿莫西林胶囊”等散装药品,一些需冷藏的注射用胰岛素污迹斑斑。经查,仓库内的药品几乎都已过期失效,药监人员在现场还发现大量药品包装盒以及批号印章等工具。 郭泰鸿说,这是一个过期药贩窝点。逃跑的中年男女是一对名叫董孔坚、何东琴的夫妇,被抓获的那个男子是他们的亲戚叶大春。 一个小时后,在杭州市近江花园七苑,过期药贩於友兵的地下仓库也曝光了。他煞费苦心地将药库隐藏在居民区里,还用报纸糊住了窗户。一堆过期药品包装盒、一台打包机、一个批号印刷机清楚地供出了他的身份。执法人员在仓库内查获了数百种已被翻新、包装待发的过期药品。 於友兵是上述三人的亲戚,同是浙江乐清人。现场缴获的销货记录表明,他在4月29日之前的5个月时间里,销售过期失效药的金额至少有189万。根据药监部门估计,贩卖过期失效药的平均利润高达300%,也就是说,於友兵在短短5个月里攫取了近250万元的非法收入。 郭泰鸿介绍,这是杭州迄今为止捣毁的最大两个制售假劣药窝点。虽然数额巨大,但於友兵并非杭州过期药地下市场的大鳄,他也不过是一个二道贩子。 一年半前,郭泰鸿上任杭州市药监局局长。正是在此前后,杭州医药贩子迅速实现了帮派化。如今杭州过期失效药地下市场从收购至贩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令郭泰鸿颇感头痛。 “浙江乐清”与“江苏宝应”在帮派化的过程中“胜出”,成为两个最大的派系。於友兵便是“乐清帮”的成员。据了解,他在药贩帮派三级金字塔网络结构中属于第二层。 郭泰鸿说,在杭州,目前至少还有五六十个於友兵这样的二道贩子,他们一年的累计盈利可以达到上亿元。 乐清人与宝应人在两三年前就开始进入杭州过期失效药地下市场。当时,一部分在杭城做服装生意的乐清人和一些做水产生意的宝应人,嗅到了医药市场的巨大利润空间,在生意淡季纷纷转做药品生意。最初,这些人不过是小打小闹,但随着杭州“吃医保”人群的不断壮大,他们也由“兼职药贩”逐步转化为“专职药贩”。 两大帮派对峙的局面在2003年逐渐明朗。靠贩卖过期药实现“率先致富”的乐清人与宝应人,将这种“致富”模式带入各自家乡。更多的乐清人与宝应人从老家奔赴杭州,加入贩药行列。两大帮派声势日隆。 郭泰鸿说,两派人丁最为兴旺时,加起来有一千多人。红眼于巨大的利润,安徽、河南一些药贩也曾试图建立自己的帮派,无奈“乐清帮”与“宝应帮”已经形成垄断,他们再也不能形成力量,于是转为与两大帮派合作。 “乐清派”与“宝应派”各有固定地盘,前者多在汽车南站一带活动,因为从那里前往乐清最为方便,更重要的是,那里有大量民宅、仓库,可以作为掩护。而后者的地盘则是市区一些繁华的地段,他们在那里租下店面,以卖香烟、回收保健品作为掩护。 过期药贩派系间一般恪守“江湖规矩”,不轻易侵犯对方地盘,但随着竞争的愈加激烈,帮派间的地盘之争也时有出现。 有时一个帮派成员会跑到对方地盘用抬高价格的办法抢夺生意,解决帮派争斗的方式很简单:拳脚模式。但斗殴一般都在夜间进行,双方均担心在白天行动会引来警察。 帮派内也会因利益冲突发生内讧,失利者一旦扬言要向药监局举报,必定引来家法惩治:暴打清理出户。 郭泰鸿介绍,两大帮派均有严密的组织规律与成熟的组织结构: “马仔”是帮派内的最底层,每派均有五六百个,他们分布很散,都有固定的“蹲点”,一般都在小区、公园、医院等附近收购过期药,网络遍布杭州每个角落。 “马仔”是二道贩子雇佣的,因为地位低下,他们无论下雨还是烈日都要在各自“蹲点”“克尽职守”。等他们收购的过期药到达一定数量后,二道贩子就会开着摩托车前来取货。 一个二道贩子一天要跑十几个蹲点,只有他才有资格见到组织最上层的“药枭”。二道贩子汇总从“马仔”处收来的过期药,然后在各自的窝点翻新,重新打印批号后包装成箱,大批量运往“药枭”手中。 於友兵的被擒,对“乐清帮”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创,於友兵身后的十多个“马仔”没了“主子”,这意味着断了他上面那位“药枭”好几条“财路”,“至少有好几个居民区!”郭泰鸿估计。 “杭州两个派系大概有十几个药枭,狡兔三窟,每个药枭都有一两个窝点。”郭泰鸿说。 马仔购药 杭州市中山中路某小区门口,七八个老人正围在一起下象棋。一个30多岁的女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女子坐在距老人们不远的一张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叠报纸,但她的目光始终盯着过往行人手中的袋子。 马路对面一家商铺的老板说,这是一个药贩子,几乎每天都来这里,一坐就是一整天,附近居民大多知道她的身份,时不时会有居民拎来药品卖给她。药贩子开价很低,19元的吗丁啉收购价是6元,17.5元的达克宁是4元,13元的康泰克是3元。 一些老人说,自己年老体弱,是个“药罐子”,家中难免会有一些剩余的药,甚至是过期失效的,放着也没用,倒不如换几个钱。 这是过期药的一大来源。药监官员告诉记者,一些居民家中年代最久的过期药包装盒上甚至还印有毛主席头像和语录。还有一些居民扔进垃圾箱的过期药品已经发霉,长出绿毛,药贩子发现后依然捡走。 “马仔”满大街跑,在各个居民区无孔不入。两毛钱一袋过期感冒冲剂,药贩子翻新后以五毛钱卖出去,150%的利润,诱惑大得很。 一个7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他们喜欢将药卖给宝应人,因为他们相对厚道一点,而乐清人太精明,价压得很低。 一度,杭州城里药贩子吆喝声不断,高架桥下、小区内到处可以看到摊着牌子明目张胆收药的药贩子。郭泰鸿说,他们一个星期可以接到十多个举报。但监管相当艰难,“马仔”一旦察觉有药监人员出现,往往会舍小保大、弃物而逃,生怕暴露自己的组织。即便被抓住了,接受讯问时也总是避重就轻,不肯说出背后的“大头”。 根据店铺老板的指点,记者在女子身后的草丛内发现了一只黑色的拉链包,杭州药监局工作人员朱宏说,这是“马仔”的典型特征。“马仔”很“敬业”,即便太阳再高,他们也会坚持坐在太阳底下,最多将报纸顶在头上。 2003年,杭州市药监局抓了65个药贩子,加上今年上半年的穷追猛打,药贩子收敛了很多,几乎都转入地下,小区内再难听到吆喝声。 但朱宏说,只要掌握了技巧,“马仔”还是很容易被辨认出的。他们一般多在老年人聚集的地方活动。比如公园,老人们都在活动,就那么一个中年人坐在一边,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一直在关注行人。一旦看见有老人拎着东西,便会迎上去:“有药吗?”“但他一般不敢问年轻人,生怕是我们伪装的。”朱宏笑道。 令朱宏忍俊不禁的是,马仔面对身着便装的侦查人员竟也会理直气壮地要求:“有证件吗?给我看看!”过期药地下市场出现过“黑吃黑”的情况。而这所谓“黑吃黑”,倒不如说是“黑吃灰”更加确切,朱宏说,杭州曾有一个十几个人的犯罪团伙,专门假冒执法人员敲诈“马仔”。 “贩卖过期药是犯法的,你知道吗?!你说吧,私了,还是公了?”马仔吓懵了,当然愿意交一笔钱私了,后来,马仔们逐渐发现自己上当了,但“灰社会”拼不过“黑社会”,只好吃哑巴亏。“吃一堑,长一智”,现在一旦有人查抓,马仔们都要求对方出示证件。 “这是一个很戏剧化的场面,我们一亮证件,对方马上就蔫了。”朱宏说。 药品来源 郭泰鸿说,1998年杭州警方在一次整治行动中时,推开一间住宅大门,偶然发现了一个药贩窝点,涉案60多万元,满屋都是过期药品。此后几年不断有一些整装好的过期药在公路检查站等地被查获。 过期药的地下市场在杭州几乎已是路人皆知。“吃医保”人群是药贩子的一大药源。 郭泰鸿说,杭州有一些有能力从医院拿到大量医保药品的离退休人员,起初将吃不完的药卖给药贩子,后来发现有利可图,有部分人索性专门吃起医保,开取大量医保用药,转手卖给药贩子。据郭泰鸿介绍,去年一年杭州市某一类享受医保的人员,只有3000人,医药费却高达2.1亿元,是杭州14万参保人员医药费的总和,平均每人7万元。 杭州日前逮捕了一个“吃医保”者,涉案20多万元,他持着父亲的医保卡,一天可以跑10家医院,一个月骗取医药3万多元,然后以原价20%的价格卖给“马仔”,“马仔”再以原价40%的价格卖给药贩。 郭泰鸿说,这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每年都以亿元计。而且,危害不仅仅限于经济损失,关键在于,“吃医保”人群滋生了地下药市。从他们手中回收的药品本身并非过期失效药,但在转卖过程中极易因保管不当造成失效。 郭泰鸿说,药贩一般都有各自“吃医保”的老客户,定期到“老客户”家中取货。杭州市去年抓了10个吃医保的人,这些人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不怕罚款,就怕曝光,于是杭州市药监局在媒体上公布了其中两个人的住址,震慑作用立马显现。 过期药的另一大来源是一些医药代表处,按规定,医药代表处是不允许保存药品的,但不少医药代表处都有大量被厂家核销的过期失效药。 药贩子闻嗅而来,原先十五六万元的药品,收购价五六万元,药贩子一本万利,对医药代表处而言,反正药品已经核销了,卖给药贩不但省却了处理过期药的麻烦,还换到了一笔钱,何乐而不为? 杭州市药监局稽查支队支队长李尚明说,一部分合格药由于渠道管理不善,很容易造成过期失效,也成为药贩窥视的一个目标。2003年杭州曾截获一批失效狂犬病疫苗,按规定,狂犬病疫苗必须在冷库中保存,某医药公司的杭州代表处从东北厂家进货时,疫苗也的确是按照规定保存的,但从东北运往杭州途中的保存温度竟一直保持在30多摄氏度。这批疫苗实际上已经失效,药贩子也闻风而来。 李尚明说,药贩子在收到过期失效药后都会重新包装一番。工序实际上很简单:对于药片,将包装盒统一换掉,打上新的批号即可,过期胶囊则剥开重新包装。包装设备没有监管,市场上很容易买到。对于注射剂,药贩们则在地下仓库里用水洗掉旧批号,再打上新批号后重新包装,外人很难看出猫腻。 李尚明说,翻新后的过期失效药一旦流向市场,后果不堪设想。 流向农村 过期药贩很想“产地销”,无奈城市监管力度相对较大,大医院也比较正规,“渗透成本”较高,而杭州市民对这种“马路药品”也是相当谨慎。因此过期药贩只能在城市边缘寻找销路。 他们将一部分翻新后的过期药推销至郊区的地下黑诊所,那里的求诊者主要是一些外来民工和周边农民,用一些药贩的话讲,“民工好蒙!”为打击这些私人小诊所,杭州药监局的30多个监察人员忙得焦头烂额,但依然无法根除。郭泰鸿说,一两百元过期药金额甚微,但危害不得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对药贩只能以经济处罚为主,抓了又放,他们的犯罪成本太小。 更令郭泰鸿的是,很有可能一些过期药已经通过主流渠道进入了个别平价药品超市。而更多翻新后的过期药则被运出杭州。郭泰鸿说,杭州只是过期药的一个加工基地,“乐清派”在乐清汽车总站附近一个旅馆的地下室交易,而后销往浙江、福建、江西一带。“宝应派”则将过期药运至江苏、上海,最终销往安徽、河南等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 过期药之所以在农村泛滥,一大原因是药材缺少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郭泰鸿说,浙江一些县基本只有200多家村卫生所,平均三个村才有一个卫生室,如果以自然村计算,就是10个自然村才有一个卫生所。药贩到乡镇卫生所推销药品,而那里的医务人员多是过去的赤脚医生,专业水平不高,难以辨别药品真伪;当然还有些医务人员在利益驱动下,故意购进这种翻新药。 过期药不但疗效大打折扣,甚至会导致病情恶化,但农民如果吃药出了人命,一般不会怀疑到药物本身,总会认为是疾病导致,最多也只是怀疑医生的医术欠佳。 郭泰鸿说,农村医药监管不力,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监管,也是过期药大肆泛滥的一大原因。他举例说,目前药品监管只设到县一级,杭州淳安县有五六十万人口,但药监局只有10个人,管理力量薄弱,有效监管力不从心。 “这并非个案,在中国乡镇是非常普遍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农村两网建设,就是加强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建设,促进农村药品供应网络建设。”郭泰鸿说。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