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洋:与共和国法制事业一道成长(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6日17:24 《人物》杂志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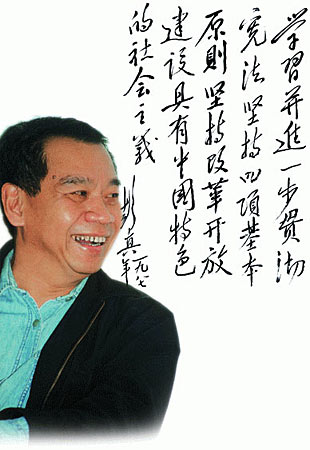 傅洋  彭真夫妇和子女(后排右起傅彦、傅锐、傅洋、傅亮) 2004年3月14日,新的《宪法修正案》正式通过,中国的法制事业在“尊重人权、以人为本”的新思想新理论的引导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于是,带着梳理我国法制进程的想法,我到新中国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同志的家拜访。 这所院落位于北京市委斜对面的台基厂头条,青灰色的对开大门和稀少的行人让我感觉到了这个院落的肃穆和神秘。院里的三层小楼据说已逾百年,彭真在这里住过三十多年
我这次要采访的傅洋是彭真(原名傅懋恭)同志的四子。彭真在1979年恢复工作以后,殚精竭虑于中国的法制重建工作,曾经做出了三个月时间主持制定七部基本法的骄人业绩。在他的几个子女中,只有傅洋自1979年以来一直从事着法律工作,他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9年,现在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和全国知名的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父亲的精神血脉。 新中国的法制事业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初期,1954年宪法的制定保障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整个中国进入法制的真空期;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9年开始重新修订宪法并重建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中国的法制建设走上了快车道;第四阶段是十六大以后,中国的法制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注入了人性化的新思想,标志着中国的法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并与世界接轨。 在这四个阶段中,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前面的三个阶段,而傅洋25年的法律生涯则直接与后两个阶段相联系。可以说,父子两代人伴随了新中国法制一波三折进程的全过程。 彭家的“逍遥派” 1949年11月26日,刚刚接任政务院政法委副主任的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件喜事:爱妻张洁清为这个幸福的革命家庭再添一子,并取名傅洋。 接下来的时间里,彭真对新中国的法制进程一直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傅洋出生后不到一个月的1949年12月21日,彭真在主持了北京封闭妓院行动后给中央和华北局起草了《关于封闭妓院的情况报告》,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余毒画上了句号。如果说这只是一个“个案”,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彭真为新中国《宪法》的制定和基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1953年9月1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会议上,他提出了“我们的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逐步实现比较完备的人民民主法制,来保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思想,为新中国的法制发展提出了任务和目标;次年9月在出席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时,他又指出:“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此成了他的口头禅和思想准则。 没有刑法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到“文革”被“打倒”前,彭真一直领导着新中国刑法的制定工作。“文革”前,《刑法草案》已改到第九稿。而“文革”对法制的彻底破坏,使我国《刑法》的制定延误了十年以上。直到1979年,它才在彭真亲手培育下诞生。这部《刑法》的主要架构内容,基本与“文革”前的草案一致。它的新特点,在于根据“文革”的惨烈教训,写进了“非法拘禁”、“诬告陷害”、“刑讯逼供”等新罪名。 彭真从来都是以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为准,常常是凌晨两三点被叫到中南海商量工作。工作如此繁重,父亲和傅洋的直接交流自然不多,但是父亲的精神指引却在傅洋心中深深地扎了根。那时,父亲常到工厂或农村去视察,只要可能,几乎都要带上傅洋。四季青、首钢、一渡河、开滦煤矿,这些被当时的中国视为先进典型的工矿乡村留下了傅洋对父亲工作的早期印象。彭真难得的娱乐是看京戏,吉祥、广和、长安等剧场是他常去的地方,于是,一些传统剧目成了他教导孩子们的教材。傅洋记得当时看过不少孙悟空的戏,父亲几次对他说:大闹天宫前的孙悟空有斗争精神,到了保唐僧取经,就没意思了。孙悟空想斗争还是让人戴上了紧箍咒。 一天晚上,彭真将傅洋叫到身边问道:“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傅洋笑着对我说,当时他回答得太“客观”,总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说:“不知道。”谁料,父亲一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人,怎么连这点决心和意志都没有?!”也许这是一生中父亲惟一一次对他发火,所以很难从记忆中抹去。但是,他却朦胧地晓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意志的磨炼,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验。未雨绸缪,不断思索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在考验来临的时候才能随时以坚韧的意志从容应对。这不但在艰苦的岁月中是必需的,在平静安逸的日子里,对付娇慵浮躁的滋长、惰性任性的销蚀更是必不可少。 傅洋上初中和升入高中的几年间,正是新中国形势风云骤变的时期。高中只上了一年,“文革”即告开始,从此,学校成了“革命”的园地和“派系”争斗的战场。刚刚走上正轨的新中国法制事业被毁于一旦,而亲手创建了新中国法制基础的彭真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停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于1966年12月3日被正式监禁。半年后,一直作为彭真秘书的张洁清也被关押。整个傅家只剩下几个孩子被无边的阴影笼罩着。傅洋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无缘“革命”,不得不成为名副其实的“逍遥派”。 1967年11月的一天,一个通知下来,傅洋和姐姐傅彦被赶出了位于台基厂的家。一辆小平板车载着两卷单薄的行李和孤零零的姐弟俩踽踽行走着,目的地是大约一公里外的苏州胡同北京市委宿舍的两间小平房。我后来去寻访了这个旧迹,在崇文门北大街路东,距现在的崇文门饭店只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一个连巷牌都被拆光的小胡同。进胡同大约150米,几栋粉白相间的旧楼围成了一个环型,崭新的门牌上写着“苏州胡同101号”。我进去打听时,才发现当年供傅家姐弟栖身的两间小平房现在由一个老人家看管,牌子上写着——存车处。傅洋和我说:“那个晚上,空空荡荡的小平房里只有两块用板凳垫起的木板。我和姐姐因为不会烧炉子双双煤气中毒。睡到半夜我去上厕所,一下摔倒在门口。姐姐闻声爬起将我弄醒,却一下子晕倒。我当时忍着剧烈的头痛将姐姐连拖带抱地弄到马路对面的同仁医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好像费尽了毕生的力气。” 回忆《矿产资源法》的诞生 从这时到下乡插队,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傅洋不能再依靠父母的照顾来生活,甚至没有了兄弟姐妹的相互依赖(此时当兵的大哥傅锐实际被软禁,姐姐傅彦不久即去河南农场,弟弟傅亮被抓到北京市少年管教所),他惟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父亲曾经对他的谆谆教诲。 “可以说,父亲的思想,尤其是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对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期间法制的‘礼崩乐坏’有着深刻的感受,我作为一个耳濡目染着父亲法制思想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感受尤甚,因此我一直存着为中国法制贡献一份心力的愿望。1979年父亲恢复工作后,我和父亲回到北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 1979年3月,傅洋成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即后来的法工委)最初的工作人员之一,投入到他将要一生从事的中国法制事业当中。 全国人大法工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一个工作机构,承担着改革开放后几乎全部新法律草案和旧法律修订案(包括所有国务院提交的法律草案)的立法调研工作。作为一个开始只有十几人的机构要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每一个法律草案,傅洋和同事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熟悉该草案的专业领域和专业知识,其次是要召开一系列由执法机构、学术机构、守法机构组成的座谈会,另外还要进行实际的考察调研,因此,一部法律从草案到最终出台往往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漫长过程。 “我刚到法工委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多少法律知识。那时中国也没有几部法律。我的法律功底是在立法实践中边学边干边积累起来的。比如《矿产资源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草到1986年3月正式颁布,我几乎参与了全过程。对于这方面的法律我也就从门外汉变成了内行。” 1980年底,傅洋和同事们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的各个部委去搜罗正在进行中的立法计划和相关进度,环保委、交通部、卫生部、外经贸部……到地质部的时候,他们得知,《矿产资源法》正在起草当中。第二年,《矿产资源法》草案送达法工委。从此,傅洋开始了对这个完全陌生的立法领域的认识和研究。 他先是找了本《采矿学》,翻了翻,太专,连最简单的术语都看不懂,接下来,他又找到《辞海》(未定稿),其中的“矿业篇”中对很多专业概念进行了一些解释,这让懵懂的傅洋似乎大致了解了自己案头这部沉甸甸的法律文本在说些什么。其实,不光是傅洋,当时整个法工委也没几个人知道《矿产资源法》要说些什么和解决哪些问题。 1982年夏天,傅洋带着立法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来到黑龙江勃利县一家小煤矿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不巧的是,到矿里的时候,正好赶上矿上停产一段时间。于是傅洋只能在一个工人的带领下到停工的矿井里走了一遭。黑洞洞的巷道一直蜿蜒到地下,除了头顶微弱的矿灯简直就是一个地狱般的世界,令人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还要走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出来后,领路的工人向傅洋介绍说:这个矿虽然小但是还有通风井,而许多这样的小矿只是条件恶劣的独眼井,根本没有通风的风井,地面空气不能形成循环回路,在井下作业的矿工就像时时处在一个充满了瓦斯,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里,危险的发生只是迟早的问题。回到北京以后他查阅了相关资料,才发现当时国外先进矿山的死亡率一般是以百万吨分之几为单位的,而当时中国的采矿死亡率却是万吨分之几,是人家的一百倍。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矿产资源因为立法的不健全时刻受到威胁,傅洋由此真正感到了矿产资源立法任务的沉重。 傅洋在对《矿产资源法》进行立法研究的时候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当时矿产资源的勘察、开采和保护是由国务院诸多部门分管的,除地质部外还有国家计委、石油部、煤炭部、冶金部、有色总局、建材总局、二机部(核工业部)、水利部、化工部等,而且很大一部分工作还由地方负责。条块如此复杂,因此法律的制定既要保障当时的产业发展,又要适应体制改革的需要和各部门的协调,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1985年春,傅洋和同事们到山西和云南等地进行系统调研。在山西,他了解到,许多小矿根本未经批准,乱采滥挖,不仅侵害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而且由于没有合理的开采顺序,还造成了矿业资源的极大浪费。许多小矿甚至还随意进入大矿矿区开采,甚至将大矿的通风井拦腰贯通,造成回风短路,不但给正常采矿造成安全隐患,甚至导致大矿整体报废。 在云南,一个国营露天放电锰矿的情形更是令傅洋触目惊心。这是一个含量极高的锰矿,采出的矿粉甚至不经提炼就可以直接用于电池生产。一路上,傅洋看到无数的农民用驴车在运矿石,在国营矿山已经建成的广阔的采矿平台上,农民更是漫山遍野地胡乱挖掘,不少高压电线杆歪倒在一旁,很多铁轨已经悬空,真可谓满目疮痍。为了维持生产,国营矿山只得在建好的平台上划出十分之一的地段让给农民采,但农民们认为这十分之一已经是自己的了,仍然在剩下的十分之九的地段遍地开花。看到这里,傅洋与几个农民闲聊起来:“国家看到你们这样乱采肯定要管,你们还是组织好,回到自己的地段去采。”没想到这话惹了祸,傅洋等人刚下山,山上就发生了械斗,甚至动了大刀和火枪。原来,在那里采矿的两个村的人听说中央来人要限制乱采滥挖,又跑回去争抢原来分给他们的地段。 这次调研深深地加重了傅洋心中的危机感,他清醒地认识到:在立法过程中,一方面要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矿业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和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还必须保护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大生产安全的保护力度,并解决资源、勘察和开采的权属含混不清的问题。经过无数个昼夜,傅洋和同事们在昆明写出了最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的《矿产资源法(草案)》(修改稿),并在立法中首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等新概念。 1985年秋,就在《矿产资源法(草案)》将交付人大常委会表决的前一天晚上,傅洋和参与《矿产资源法》研究工作的其他同志为即将大功告成而欢欣鼓舞时,却风云突变。中央某位领导同志对这一草案提出了严厉批评,不赞成上会表决。这位中央领导认为草案和他大力提倡的“有水快流”(即认为许多贫困山区要脱贫致富只能靠采点矿,有矿就要快让农民去采,农民采点矿不过是给地球挠痒痒)的原则相悖。一切似乎都不在傅洋的意料之中,难道他和同志们几年的努力就这样轻易地被否定了?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彭真同志本着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委婉地说服了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决定对草案继续进行慎重的研究,暂时不付表决。 于是,傅洋和他的同事们又投入到对草案的反复研究中,最后,在草案中加了一章《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将原来散见于草案各章的这方面的规定集中写到一章里,并加进了一些鼓励、扶持、指导集体和个体采矿的政策性规定,以体现“开放、搞活、管好”的方针。终于,1986年3月,《矿产资源法》在经历了5年的磨砺后在六届人大十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听傅洋讲述《矿产资源法》的诞生过程,我真正领会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法律走向正轨的艰辛,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让我体会到了他在立法研究过程中那种“痛并快乐着”的复杂心境。在法工委工作期间,在傅洋直接参与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海洋环境保护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十多个法律的立法工作中,这种心境一直伴随着他。他说,“那一段时间虽然我一直身处立法研究的最前沿,体会着那种战胜困难后的成就感,但是,平心而论,紧张和压迫感是始终围绕着我的。闲暇的时候,我会回忆起在黑龙江插队时自由的空气和美好的时光,也正是因为那段时光的锻炼,我才会具备后来从事法律事业所必须的精神和意志。” 一个民办教师的莫力达瓦 “文革”时,没有高考,没有当兵、当工人的权利,在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潮中连农场傅洋都不能去,因为农场是挣工资的,像他这样的家庭最多只能到偏远的地区插队挣工分。1969年的一天,他的初中同学文斯(楚辞专家文怀沙之子)从黑龙江插队回来找到他,兴冲冲地向他介绍了自己插队的黑龙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现属内蒙古)风景如何优美、历史如何传奇、食物如何充裕等等。于是,傅洋邀上几个“同类”一路杀向莫力达瓦,向着自己的遁世之地去了。 在傅洋眼里和心中,莫力达瓦是神奇而美妙的,在这远离喧嚣血腥的革命漩涡的地方,没有人问出身,没有人问家世,更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又红又专,在这里,人就是简单的人、唯物主义的人。傅洋似乎真正找到了自己心灵归属的地方。 莫力达瓦风景如画,伟岸的山崖下流过碧玉般剔透的嫩江,温柔的丘陵间摇曳的是妩媚多姿的白桦林,初夏,如茵的草甸上怒放着嫩黄橘红的百合,深冬,涤荡胸怀的是尺厚的积雪上精细纤巧的野兔的足痕。 莫力达瓦生活如歌,傅洋和当地的老乡们一起耕地、播种、收割、打场,劳累后的一桶沁凉的井水犹如天使将爱情之剑穿透心坎……但是,莫力达瓦的时光对于傅洋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在这段时间大量品读了能找到的马恩列斯毛、费尔巴哈黑格尔尼采卢梭、李嘉图萨缪尔森凯恩斯、巴尔扎克雨果曹雪芹的著作。知识使他成熟,让他开始认识这个时代并选择自己今后的道路。 从初中开始,傅洋就有打篮球的天赋,身高膀大的他当时就是北京市少年队的主力。很自然地,他三天两头地被拉到旗里甚至外地打球。球打得多了,活自然干得少了。这下生产队的乡亲不干了,纷纷反映道:“你在旗里打球,凭什么让我们给你记工分,发口粮?打球能打出苞米茬子吗?”最终协调的结果是,旗里将傅洋调到莫力达瓦首府惟一的一所中学尼尔基中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就这样,一个高中只念过一年的学生开始教起了中学语文、数学、物理还兼班主任。 我曾经不解地问傅洋:“你高中只念过一年,怎么教得了初中的学生呢?”傅洋笑着说:“还行,我的基础是在四中打下的,只要自己学过,再转卖给学生还不至于误人子弟。再加上‘文革’中老师们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他们自己连课堂秩序都难以维持,我这个‘球星’却深得学生的崇拜。” 让傅洋自鸣得意的是,他试着用辩证法去指导物理教学,给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戴上对立统一的帽子,为能量转换守衡定律贴上否定之否定的标签。这种听起来有些云山雾罩的课程在当地教育界竟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旗里甚至组织各校的老师到尼尔基中学听傅洋的课。 一边为旗里打球,一边教书,转眼间就是三年多。到了1975年夏天,彭真和张洁清被释放并流放到陕西商洛地区,傅洋被允许和姐姐去照顾。到了商洛,他先是被安排在商洛县中学师范班教物理,次年初又被安排到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不管怎样,经过了近10年的阻隔,傅洋终于和父母重新生活在了一起。 一个没有出过庭的律师的使命 到1987年,傅洋在人大法工委已经工作了整整9年。时代在发展,中国的法律事业也逐步迈向正轨,此时的傅洋对自己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考虑。他钟情于法律事业,但是并不仅仅满足于高高在上的立法工作,他希望自己能走到法律生活的第一线去体会法律在实际的社会执行当中的问题。他觉得律师职业很有挑战性,同时对中国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的现状也充满了焦虑。于是,他向父亲征求意见,希望能做一名普通的律师。对于儿子的选择,彭真没有过多地干预,只是意味深长地说:“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权力。” 中国的律师行业从1957年到1980年是一段空白,到80年代末期发展程度仍然很低,当时的事务所都是国营,全国律师不到2万人,而且在法律事务中的地位也一直得不到重视。 1988年初,傅洋离开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着手组建康达律师事务所。 傅洋曾经接触过欧美一些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其律师人数往往达到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并拥有几十家分所。傅洋觉得作为泱泱大国,中国在这方面也必须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于是,在事务所组建之初,他就为之制定了发展成为大型综合性事务所并与国际接轨的目标。但是,鉴于父亲在中国法制界崇高的地位,他不愿意让别人以为自己在利用家庭背景打官司,因此,他默默地当起了一个从没有出过庭的律师,他的基本工作是事务所市场的拓展、案件的协调研讨、内部管理的健全,以及处理一些非诉讼法律事务。 2000年,根据国务院和司法部的要求,康达律师事务所面临着两个变化,一是所有制的变化,二是管理体制的变化。许多原本结合不紧密的事务所不得不解散或者重组,而由于傅洋长期以来注重长远的发展思路,使康达在面临这种处境的关头反而更加稳固。到今天,康达已经从创建之初的十几个人的小所发展到今天拥有律师二百余人,每年接案近千件,在全国设有11个分所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1985年,第三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改革方案,正式成立中国律师行业自己的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傅洋被选作副会长,并一直连任到现在。从原来只考虑康达的发展,到现在要考虑整个律师行业的发展,傅洋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他不断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提出旗帜鲜明的建议。 傅洋参加全国律协领导工作之初,我国制定第一部《律师法》的工作正处于关键时刻,他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工作经历这时派上了用场。他为《律师法》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直接推动了这个法的立法进程。他回忆说,这个法的草案中原有一条“律师不得规避法律”的规定。他在和同事们研究时发现,“规避法律”的提法是个含混的概念,在我国的法律中从未使用过。如果在立法中用这个概念去约束律师,不仅会使广大律师觉得无所适从,容易造成执法误区,而且会加剧社会上某些认为律师就是钻法律空子的偏颇观念。这对于律师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于是他多方反映意见,并直接给法工委写信陈辞,使“规避法律”的概念最终没有写入《律师法》。 律师,由于法律赋予的特殊职责,与一些执法机关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刑事辩护工作中很容易产生一种感情上的冲突。傅洋改做律师后,他过去在执法机关的有些朋友当面对他说:“你怎么干这个?专门给我们找麻烦!”傅洋认为,律师与执法机关间不存在感情和根本立场的对立,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一致性,是社会主义律师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不论是在他主持事务所的工作中,还是在全国律协的领导工作中,他都大力宣传这一观点,希望不仅全体律师要坚持这种观点,全社会也要支持律师在这种观点指引下努力实现法律赋予他们的庄重职责。 傅洋通过他从事立法工作和律师工作的两个阶段的实践深深感到,律师由于其在我国法制体系中的特殊职责和地位,对于法律有一种比较超脱的特殊视角。他主张律师不但应当在执业中是法律的遵循和实践者,也应当积极总结自己实践参与立法,成为我国法律与时俱进的推动者。他在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和全国律协机关刊物《中国律师》上大加呼吁,推动了全国律协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了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 傅洋在全国律协工作期间,曾率团到日本、韩国、埃及、印度、土耳其、泰国等国家进行交流访问。在巴基斯坦,穆沙拉夫亲自接见了他,并长时间仔细询问中国在司法改革和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傅洋在这些交流和访问中,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感受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中国律师在国际上受到的重视感到骄傲。 本文即将脱稿之际,各大媒体报道 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要从学习教育、依法管理、严格监督等方面入手,扎扎实实地抓,坚持不懈地抓,并与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结合起来,务必取得实效。”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傅洋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自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热爱,来自对人生信念执著的坚守,亦来自父亲的精神指引,正如2001年在父亲逝世4周年时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父亲的思想,永远不会离我而去!”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人物》杂志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