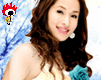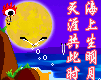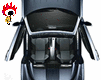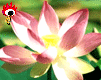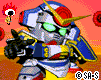戒毒者谈心屋:中国民间自发戒毒第一步(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2日10:55 新华网 | ||||||||||||
 戒毒后与村民的关系也和谐起来,“过年还有人送东西给我们,以前躲我们都来不及。”吴顺国说。  吴顺国向记者展示他的《戒赌必读》书稿 1968年,12名戒毒成功的原吸毒者在纽约城租赁了一幢建筑物的顶楼住下来,并将其取名为“凤凰之家”。 凤凰村的大部分职员都是从前的吸毒者。他们相信,吸毒者之所以滥用和依赖药物是因为人格上发生了问题。其治疗的目标是帮助吸毒者重新建立人生和价值观,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凤凰村的居住者均相互关心,若有其他人感到烦恼,情绪不好时,大家都会主动地
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为吸毒者服务的治疗集体——凤凰村。 2003年3月,居住在贵州省贵阳市三江农场的一对已戒毒数年的夫妇两人,开通一门“戒毒谈心屋”热线电话,帮助其他吸毒者摆脱毒品,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些自愿戒毒者开始聚集在他们周围,迈出了我国民间自发戒毒的第一步,成为民间自发戒毒较为成功的范例。 从新添寨到三江农场大约10公里路程,这个农场占地19000多亩,成立于1958年,员工加上家属有1000多人,俨然自成一个社区。 34岁的余红芳是三江农场的子弟,她和33岁的丈夫吴顺国长住在自己的五哥余红祥家里。 余家的生活节奏缓慢。晚饭后,邻居会来打牌或者下棋,到十一点多钟人逐渐散去,便到了吴氏夫妇和三个暂住在这的朋友的谈心时间。 这是很特别的谈心。因为,每天晚上促膝而谈的五个人,都曾经有过或长或短的吸毒史。 最初之所以收留小许、小曾、晓伟三个朋友,吴氏夫妇有他们的想法,“我们两个都曾经是吸毒人员,深受其害,现在,她(指余红芳)戒了9年,我也戒了5年。今年三月份,我跟五哥和余红芳商量,想多装一部电话,搞一个‘谈心屋’,帮助那些想戒毒的人们。消息传出去以后,陆陆续续有人找到我们,或是电话交谈,或是上门咨询。后来,有人提出,能否让他们暂住一段时间,让我们夫妇俩帮助他们戒毒。我们找到很多相关部门咨询后,得到许可,决定尝试一下。” 就这样,余红祥腾出几间空房,把许荣跃、小曾、晓伟三个人安顿下来。 “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谈心,相互鼓励。有共同的经历,交流起来非常容易,也愿意谈一些掏心窝的话。”吴顺国说。每天晚上,几个曾经的瘾君子围坐在一起,谈不堪回首的过去,谈戒毒的决心,谈将来的打算,谈高兴的事,谈后悔的事,谈遗憾的事……话题总离不开毒品,却能让人逐渐忘却“那种感觉”。 吴氏夫妇 吴顺国夫妇的卧室梳妆台上,贴着几张照片,余红芳指着其中一张说:“这是在交际处原来的那个天桥上拍的,差不多有十年了吧。说起来不好意思,就在拍这张照片后刚刚三天,我就因为吸毒在这个天桥上被抓了。” 余红芳是家中的幼女,因交友不慎染上毒瘾,前夫也因吸毒过量,“一针把自己打死了”。1995年,余红芳从戒毒所出来后回到家中,迄今已经九年了。 吴顺国吃饭使筷子用左手,但他并不是天生的左撇子,他的右手食指短了一截。“1994年,当时我还跟前妻在一起,在一家卡拉OK厅,我向她发誓说再也不吸了,一发狠,我冲到厨房,把手放在案板上,拿起菜刀,一下子就把指头给剁了一截。” “你能下得了手?疼吗?” “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说实话,吸毒的人一天到晚都是浑浑噩噩的,感官是非常麻木的。” “戒掉了吗?” “没有。” 吴顺国真正下定决心戒毒是在认识余红芳以后。“1999年,我从中八劳教所跑出来后,一直在社会上晃荡,不敢回家,干脆就住在澡堂子里,余红芳那会正好在浴室打工。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余红芳还记得很清楚两人认识的情景:“当时我发现,吴顺国总是买两包烟,一包好的,一包差的,然后把差的那包拆开来,留下锡皮纸备用。我以前吸过毒,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人。接触久了,我慢慢了解到他的经历,就开始劝诫他,然后,我们走到了一起。吴顺国后来回劳教所补完了刑期。” “谈心屋”的“帮助方程式” 刚来的时候,小许的样子把余家兄妹吓了一跳:一米七几的个子,只有70来斤,“瘦成一个‘条条’,走路都是飘的,脸上也是木的,不会笑。”小许的母亲杨阿姨说。 为了这个儿子,杨阿姨操碎了心。“我感谢他们(指吴顺国夫妇),是他们帮助我儿子‘走出来’。” 小许的吸毒史有整整11年,——因为感情遭遇挫折,他开始吸海洛因,后来慢慢发展到静脉注射——细瘦的双臂上,满是针眼,“起码要一两年才能痊愈。”他说。 身体上可以痊愈,内心的伤痕却没有那么容易。“至今我们都还在戒毒”,是吴顺国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这调理了一个月后,小许长了二十来斤,每天要和吴顺国、小曾一起,走半个小时山路,提一桶山泉水回来,“泡茶喝,特别舒服。”小许说。 “以前看什么都是灰色的,人的七情六欲都消失了。现在,能看见山,能看见水。”小荣说:“以往从来不会说要考虑什么未来,有时候甚至想到干脆一针打死算了。现在我会想,既然‘走出来’了,我需要干点什么……” “没有家人的帮助,余红芳不可能戒毒8年,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坚持到今天。我们夫妇俩再帮助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四个,四个人就能再帮助八个人,这样下去,这种‘帮助’的能量会越来越大。”吴顺国说。 “帮助别人,也是为了帮助自己。”余红芳是这样认为的,“最开始来到三江,也许是为了换个环境逃避,但你终归还是要去面对生活,面对社会,我很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经历和努力,能够让更多的吸毒者醒悟过来。” “门开着,我却不想走” 余家旁边有一片高墙围起来的建筑,这是三江劳动教育改造所去年新建的监房。 小许曾经在三江劳改过三年,围墙里头的滋味,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我记得中央电视台以前播过一期节目,主持人向一位接受戒毒治疗者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出去以后,还会不会复吸?老实说,我前前后后戒毒不下20次,每次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目的地——找到毒品吸上一口。但在这里,门随时都 戒毒过程是痛苦的,这样的互相搀扶不可缺少。 是开着的,我也随时都可以走,但我却没有这个念头,我甚至有很强烈的感觉——如果有人找我卖毒品,我肯定会动手打他。”小许说。 小曾也有类似的感受,“即使是到戒毒所自戒,总觉得别人要高我们一等,感觉压抑,没有空间,没有自由。在这里不一样,我们在戒毒初期,情绪有些什么波动,他们特别清楚,随时会给予关心。说真的,在戒毒所里面,和那些毒友在一起,半句真话都不得。” 来三江呆了一个月,小曾自嘲说,自己“长了一个砂锅肚”。农场的生活平淡却很实在,早上,小曾总是最早起床,“先散散步,等大家都起了之后,弄点早餐吃,然后便约在一块游泳、钓鱼什么的,有时还帮五哥(指余红祥)做点活。你能够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很大的乐趣。” 吴顺国们在农场交了不少朋友,场工老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吹牛,前两天还买了50斤杨梅,100斤包谷酒,泡了一大坛子,够我们几个喝两个月了。” 再过一段日子,农场打算匀出一些生产资料分给吴顺国夫妇,让他们栽种果木,搞一点养殖业,自给自足。 “为了我们的目标” 住了一个多月后,晓伟的舅舅来了一趟,要把他接回去住几天。趁着舅舅收拾东西的间隙,晓伟跑过来,和余红芳再唠叨几句—— “六姐,我要走了。” “回去自己一定要坚持,要记住我们说过的那句话。” “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吴顺国开始筹划未来。他和小荣、小曾约定,等到他们过了恢复期,就开始骑车或步行走更多的地方,帮助更多的吸毒人员“走出来”——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今年的国际戒毒日前夕,记者再次来到吴顺国家,发现来此自愿戒毒的人又换了一批,吴顺国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个月还相约去尿检。对了,小曾刚结婚,真为他高兴。” 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戒毒拨打“戒毒谈心屋”的热线电话,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坦诚交流,获得鼓励,树立信心,了解方法。余红芳说:“明天,我们还得起个大早,去接一位武汉的‘开仓’(即直接动脉注射)吸毒者过来。” 贵阳市公安局禁毒办科长何敏一直关注着吴氏夫妇,“据我的了解,他们搞这个‘戒毒谈心屋’并不是为了牟利,住宿是免费的,只收很少的一点伙食费,完全是个人自发的行为。我们将长期追踪,定期为他们做尿检、与他们谈话,如果持续一段时间后,他们能够巩固下来并确有成果,我们会考虑给予更多的支持。” 何敏把“戒毒者谈心屋”定义为——民间自发的戒毒行为。 “民间自发”当然是针对官方而言的,贵阳市现有10家强制性戒毒所,总的收容能力为3000人,“像小吴他们这样的吸毒或有过吸毒史的人员,全市登记在册的约有15000余人。”贵阳市戒毒中心主任谈明宗说,“小吴他们的自发行为,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进行,我们不会过多干涉。” 更严峻考验还在未来 最近,吴顺国完成了一本三万余字的《戒毒必读》书稿。他说,这本书总结了自己几年来自我戒毒和帮助别人的心得,“我把它称为‘心理戒毒法’。我希望,这本书能在思想、精神上的鼓励和诱导戒毒者。” 对此,贵阳市戒毒中心主任谈明宗感到由衷的高兴。“书如能出版,将会成为珍贵的戒毒教材。”据他介绍,贵阳市现有10家强制性戒毒所,总收容能力为3000人,吸毒或有过吸毒史的人员,全市登记在册的约15000余人。多年来,强制戒毒虽能在短期内控制毒品蔓延,但实际戒毒效果并不好。 谈明宗说:“主要还是方法问题,过去不重视心理治疗,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和经验。我们一直在反思,目前也正在应用行为医学进行心理戒毒方法的研究,而吴顺国他们的尝试恰好顺应了这一趋势。” 西南政法大学毒品犯罪预防与打击研究中心副主任邱镛怡说,吴顺国的“戒毒者谈心屋”可能是一种并非自觉的尝试。已经比较成功的戒毒者又把染过毒瘾的人聚集到自己身边,无疑是一个更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样一种模式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在西方国家,是没有强制戒毒所的,比如美国,常常就是由这些戒了毒的人把其他试图戒毒者团聚在一起,通过娱乐、游玩、劳动等方式,帮助他们逐渐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下,这种结构相对松散的戒毒模式有时甚至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经济援助。 35岁的小兵曾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是家人的骄傲。“毒品把一切都毁了。对于戒毒者而言,最难的是戒毒后重新面对社会,一个有吸毒历史的人,他的道路要比正常人艰难百倍。”他说。 对此,邱镛怡说,几乎所有戒毒者都会经受“牵引性”的戒毒综合症的折磨,所以吴顺国他们的戒毒成效还需要时间来考验,要真正做到不复吸,还要迈过四道关口:对个人而言,要解决巩固戒毒成果的问题;要能得到亲人、朋友乃至社会的关爱和支持;要有生活来源的保障;要远离毒友。 “吴顺国们已经初步证明了‘谈心屋’能够帮助别的戒毒者。实际上,这是一种并非自觉的尝试,更严峻考验还在未来--社会能不能接受他们,包容他们--在这个意义上,‘谈心屋’只是一个起点。” 邱镛怡说。来源:焦点网谈 新华网贵州频道 图文:徐波 周之江 相关专题:我国保持对毒品犯罪严打态势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我国保持对毒品犯罪严打态势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