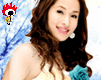探访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没人离婚也没人谈恋爱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3日17:48 南方周末 |
 “陕西村”无论大人小孩都能讲一口地道的陕西土话,但汉字在这里已基本失传  东干人打着横幅欢迎前来串亲戚的陕西乡党  一位阿訇对陈琦那辆飘着中国国旗的自行车很感兴趣 在毗邻我国新疆地区的中亚哈萨克斯坦,至今生活着一群说陕西方言、沿袭晚清陕西风俗习惯的“陕西回回”。他们是一百多年前西北回民大起义失败后流落境外的义军残部后裔,自称“东干人”。 骑着自行车去哈国串亲戚 2004年4月10日,在祁连山主峰之一乌鞘岭风雪交加的山口上,一个青海的货车司机下车正在小解,忽然,一个穿着古怪、留着长胡子的黑脸男人站到他旁边说:“师傅,能不能帮我照张相?”司机惊愕地打了个寒战,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大个子,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小便没撒完就跳上旁边的车逃也似的走了。 冰天雪地的荒山上,这个人搬了一块石头,把相机搁在石头上,给自己和自己骑的一辆变速自行车照了张相。这个独自出现在乌鞘岭上的人就是陕西临潼人陈琦,一个在人事局上班的普通干部,他于4月6日从西安丝绸之路群雕前出发,骑着单车,准备远征万里去哈萨克斯坦探访“陕西村”。 上世纪80年代,陈琦从《参考消息》上得知苏联有个“陕西村”,居住着100多年前从陕西关中迁移过去的一群回回人,至今顽固地保留着陕西的风土民俗。“陕西村”人被迫离开家乡的年代距今并不久远,是清同治年间,也就是陈琦爷爷的父辈那代人的事情。当年,他们在义军领袖白彦虎的率领下,一边抵挡着清政府的民族镇压,一边拖家带口,背着锅灶瓢盆,赶着牛羊畜口,于1877年12月翻过天山,躲过了清军的追剿,在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西边约200公里的楚河岸边扎下“营盘”,播种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白彦虎被后人称为“东干人之父”(“东干”即陕西方言“东岸子”的转音,东面的意思)。100多年过去了,离家在外那么长时间,他们还固守着家乡的传统,在思想上、道德上都传承得很好,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这些都吸引着陈琦,他想弄清楚。在了解东干人被迫背井离乡的苦难历史后,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去看他们,就像亲戚串门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并且沿着他们当年西退的路线,体验他们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与苦难。 这个长相酷似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瓦西里的关中汉子一路坎坷挫折并不亚于瓦西里。他这样做,就是想告诉那里的人们:老家的乡亲没有忘记你们,这不,骑着自行车来看你们来了。同时,还要告诉陕西的同胞:那里离我们并不远,你看,骑上自行车轻轻松松地就能到。 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 陈琦在哈国境内遇到的第一个陕西村的人是马赖赖。过境后刚到第一个城市潘菲洛夫,陕西村的人们就打发体育教师马赖赖骑车来接陈琦。从潘菲洛夫到陕西村有700公里的路程,马赖赖全程陪他。东干协会主席安胡塞亲自开着小车为他们俩做后勤保障。马赖赖人高马大,脸色黝黑,言语、动作都显得有些粗放,讲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见了陈琦,他高兴得搓着手,嘿嘿直笑。马赖赖骑的是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做工精细,构造却很简单,没有变速器,显然不是上长路的车子,加上他没有做好长途骑行的细致准备,第一天120公里骑下来便有些自顾不暇,作为主人,他还要照顾已有4000公里骑行经验的陈琦,疲累不堪。一到住处,马赖赖脸色蜡黄,上气不接下气,车子撇到房外也不管了,躺在床上喘了足有半个小时的粗气,说自己的心脏很难受,想吐。陈琦给他打了一大瓶自来水,马赖赖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一大半,差点虚脱了。陈琦一再告诉他,骑不动了就吭声,不能这么拼命。为了体谅马赖赖,陈琦有时建议歇一歇,马赖赖就强打精神顽劣地笑笑:不怕慢,单怕站,慢慢骑。一路上再苦再累,马赖赖都没叫过一声苦,让陈琦打心底里佩服他。 陕西村所在的县叫库尔代,县城离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不到100公里,顺着阿拉套山下的丘陵地带从县城往东60公里,就是中亚陕西村的中心村落、陈琦此行的目的地———营盘。这里的道路大都是苏联时期修建的,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已成了沙石路,风景却是格外优美。他们在一个高高的山梁上小憩,俯瞰前方的楚河平原,马赖赖给陈琦指点:这是营盘、这是新渠、这是托克马克(即古代的碎叶城)、米粮川、卡布隆、哨葫芦……这一带都是咱回回的地窝儿(地方)。 6月9日,陈琦他们终于到了东干人的根据地营盘,人们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的,一口陕西土话让陈琦感到就像回了家一样。他对人们高声说:“乡亲们,伊特拉斯吐维奇(俄语,你们好)!陕西老家的乡亲们打发我来看你们来咧,你们好着哩么?老家的人都想念着你们呢……”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琦的嗓子有些哽咽,在场的很多回民淌下了长长的泪水。 村里的老年人对陕西感情很深,能说出一些至今仍存在的关中地名,说着说着就落了泪。他们对现在的陕西不甚了解,好多人都保留着过去的观念,说陈琦是从“清国”来的,问左宗棠的人还在不?来的时候,陕西衙门批准不? 离开故土已120多年了,东干人对陕西却怀有一种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感情。马赖赖家隔壁一个叫马兹涅夫的东干老人,将他于1959年在莫斯科买的一幅《老鹰抓小鸡》的中国年画保存了四十多年。东干诗人大吴说,百年来,我们就像离群的羊,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年轻人把陕西叫“我爷的省”,见陈琦高兴得很,问陈琦西安城是个啥样子?见过成龙没有? 在人们的盛情邀请之下,陈琦参观了陕西村的村史纪念馆,馆中收藏有白彦虎的眼镜、玉佩、腰刀等遗物,有东干战争英雄马三奇的巨幅画像和雕塑,前苏联各个时期的纪念章,有东干先民使用过的兵器、农具,有当今东干人的生活用品、刺绣品和装饰品。 陈琦在安胡塞家里住着,没在安胡塞家吃过一顿饭,每天这家请了那家请,杀鸡宰羊,一吃就是一天,还领着他到处看,弄得陈琦甚至没有静下来的时间。 到了陕西村就和到了关中任何一个村子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大人小孩都是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和马赖赖交谈,国骂省骂时时都会冒出来,而且非常地道。孩子们都把陈琦叫“陈琦大(爸)”,都喜欢“陈琦大”的自行车,只是推出去没过十分钟就回来了,车子给摔得骑不成了。陈琦比马赖赖小三岁,就叫他“赖赖哥”,马赖赖则叫他“碎舅”(东干人把陕西认作是舅家)。对于原来陕西老话中没有的新生事物,他们有自己的叫法,把电脑叫computer,电话叫telephone,飞机叫“风船”,自行车叫“骑着的车子”。小孩刚开始学说话就是陕西土话,大了才学俄罗斯、哈萨克语言。孩子有时就会问大人,“镢头用俄语咋说呢?” 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国的,一个当地俄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东干文,就是用俄文字母拼出来的陕西土话,这种文字,俄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但它毕竟是一种文字,一个小小的民族能有自己的文字,这在全世界还为数不多。东干人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而到过中国见多识广的安胡塞积极主张推广中国的普通话,说这样才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思想,才能提高语言的生命力。但这种观点与大多数东干学者相冲突,他们认为:老话是咱的母语,要一代传一代,贵贱都不能丢。安胡塞感到奇怪,今天的陕西甘肃人都在学讲普通话,你还跟着学方言,岂不太落伍了。几次大会上,都是安胡塞跟他们从争论到争吵,不欢而散。从2000年开始,安胡塞陆续送了几个村里的孩子到中国的西安学中文,“等到他们学好了,再回来教其他的人。”陕西省政府对这些孩子全部按国内的学生同等看待,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家长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不知他们是太留恋家乡还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把所有的传统都看得特别珍贵,只要是陕西带出去的,只要是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任何一点改变都是对他们信仰的背离。 庄稼地里最苦莫过于东干人 陈琦所看到的东干,还是普遍闭塞、保守、落后,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没有多少商品意识。村里孩子很多,这可能和他们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有关,东干妇女把生养孩子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生育了十个孩子的“英雄母亲”比比皆是,马赖赖和安胡塞都是七个孩子的父亲。马赖赖既是教师,又要种庄稼,陈琦在他家里发现了一台手摇缝纫机,竟然是上海产的“无敌”牌,家里女孩子的衣服都是从这台缝纫机上手工做出来的。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私有化,随之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陕西村也不例外,个别有钱的人家有花园式洋房和宽敞的大院,好几辆高档轿车,贫穷的人家则住着摇摇欲坠的陈旧木房,有的窗子上还蒙着塑料纸,下地、赶巴扎还是套着传统的四轮马车或是驴车,成天盘算的是今年蔬菜能否卖个好价钱。 营盘人告诉陈琦,沿楚河平原从东往西走,以种地为生的维吾尔族越来越少,其他民族都以游牧狩猎或做买卖谋生。土地里刨着吃的,就只有回回了,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一半种小麦,一半是蔬菜。据说全哈萨克斯坦80%的蔬菜都来自东干人的生产。淳朴厚道的东干人没有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习惯,一年中从春分到深秋的大半年时间都辛勤地劳作在田间地头,从早到晚,中午就在树荫下或凉棚下休息吃饭。庄稼耕作上最辛苦的莫过于东干人。马赖赖说,住在楚河南岸吉尔吉斯斯坦的多是甘肃回回,和东干人很少来往。 东干人几乎家家都有小车,这里就像小车博览会,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且都是原装货,当然最多的还是俄罗斯的伏尔加和本国生产的。在这里,小车不是身份的标志,也不属于奢侈品,而是人们生活生产的必需工具。营盘、新渠都是四五公里长的村子,步行串门子的确不方便,庄稼地近的几公里,远的几十公里,没有小车是难以想象的。因而就常常能看到,一辆高品位的“沙漠王子”,后面却拽着一架四轮拖拉机的车厢,一辆豪华的“梅塞得斯-奔驰”,里边取出的却是刚从地里收回的莲花白。 因为没有环境污染,这里的农业是货真价实的绿色农业,一眼望出去都是大片大片的绿地。家家房前屋后都种有各种花草,东干人说,从这些花草的生长状况,可以看出主人的心境和理家水平。而且这里真正保持着那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朴民风,很多家都没有院墙,如果有也是象征性地用栅栏把院子围起来,个别有院墙的也不高,院门一天到晚很少关过,大街上的店铺也没有一家装防盗门的。小车开到街道上随便一放,主人就办事去了,大多连钥匙都不拔,有的车门还大开着。 在哈国,公民看病住院、学生大学前的教育、一个地区内通电话都是免费的,有的地方水电甚至热水都是免费的,六十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也可以领到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元左右的养老金,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公路边也隔一段就建有一个汽车站,是一种用水泥统一预制的小房子,外面画有各种艳丽的民族画,里边有供旅客休息的长凳。哈国大路上、闹市区、公务员的办公室、学校的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领袖纳扎尔巴耶夫的画像,陕西村的乡党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稳定、和睦、美丽的国家里,陈琦感到很宽慰。 最大的愿望是去麦加和陕西 东干的乡村都像中国过去的农村一样装着有线广播,不同的是,这些高音喇叭不广播新闻,不呼革命口号,也不播送天气预报,说的净是阿拉伯语。陈琦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专门用来组织人们做“乃玛斯”(祷告)的。东干人虔诚信仰伊斯兰教,每天的五次礼拜看得比吃饭睡觉还重要。马赖赖和陈琦在骑行当中,时间一到,水都不喝,也要找个僻静地方做“乃玛斯”。 这里的人们一生最大的愿望一是赴麦加朝觐,二是回陕西看看。 村里人也和周围其他民族互相来往,但严守教规到了苛刻的地步,让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其他民族也信仰伊斯兰教,但大多执行不严格,生活方式也日益西化,男人抽烟喝酒非常普遍,女人着装也很随意,生活得很自在。但东干的男人不动烟酒,陈琦说自己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有时实在憋不住,就背着他们偷着过把瘾。有几次让安胡塞发现了,他就严肃批评陈琦,甚至让陈琦从维护中国人形象、维护陕西人形象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安胡塞不止一次地劝陈琦入他们的教,说他们的教是世界上最好的教,马赖赖也在一旁使劲煽火,说如果陈琦入教,他就负责在当地给陈琦找个女人,以后生个男娃,想在中国在中国,想在哈萨克斯坦就过来。陈琦推辞了,光抵挡这事就费了很大的神。 相比之下,东干的女孩子就显得太清苦了。女人哪怕天气再热,也是长衣长裤,头上还要包上头巾,不能串门,走在大街上见了男性不能打招呼,在家里吃饭从不上桌子,对男人绝对的服从。陈琦到马赖赖家去过三次,第一次见到马赖赖的老婆,开玩笑说:“嫂子,一路上我赖赖哥老跟我念叨庄稼,其实他是想你了。”没想到他老婆憋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陈琦再去,她竟然不敢回家,做好饭也是让女儿端上来,直到离开村子,陈琦再没见过她。 没有人离婚也没有人谈恋爱 陈琦在哈国的日子,不管是在大街上转悠,还是在屋子里上网、出门上厕所,安胡塞都要热心地陪在左右,他不在时就让在兰州留学过的外甥苏力克作陪。陈琦在林子里解手,苏力克都要不停地张望,陈琦告诉苏力克不要老这样跟着他,说了几次也无济于事。这使陈琦深感疑惑,这俩老兄是不是也像普京一样,以前在“克格勃”上过班?东干人做事有时执著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如此。 2003年冬天香港凤凰卫视在这里摄制了《营盘日记———陕西村记事》,以第一人称作解说的就是白彦虎第五代嫡孙白伟华。白伟华22岁,正在楚河那边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人民大学学中文,普通话讲得很漂亮,他的文化程度在村子里算是屈指可数的,和陈琦特谈得来。他和马赖赖陪陈琦到马赖赖所在的学校、著名的马三奇学校参观,一位蒙着面纱的女教师非常热心地给陈琦做介绍:哈萨克斯坦实行的是11年国家义务教学,村里的学校书少孩子多,有的班上是两人念一本书。上课的教室太拥挤,只能让孩子们分三拨,8点钟来上一拨,11点钟来上一拨,下午2点再上一拨。一个星期上六天课,11年上完后,就可以像白伟华一样,到附近的城市上大学。 不管陈琦到哪个学校,学校都会送陈琦一份礼物———一本书,或者一本画册,穷的学校干脆就是一本三年级的学生教材。现在陈琦家里还有十几本学生教材呢。 令陈琦不可思议的是,看似现代前卫的白伟华骨子里依旧有东干人固守传统的一面。他说读完书后准备回村子教中文,白伟华读大学的地方离家很近,只隔着一道楚河,“可是我每次离家的时候,都有一点不舍得。营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牛羊粪的味道,炊烟的味道,锅盔的味道,奶茶的味道,天山的味道,老陕的味道……不管我走到哪里,这些味道都会留在我的头发里,留在我的身上。” 这里有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小孩,而且对象都在回民圈里找,白伟华就是先结婚再念的大学,他的妈妈和妻子罗莎的妈妈是亲姐妹。白伟华快20岁的时候,家里人觉得他该结婚了,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孩,他说没有。他们问罗莎妹妹怎么样,他说可以先处处看。于是家里就打发了媒人去说亲。去年4月,白伟华当上了爸爸。 白伟华说他和罗莎在一起的时间不多,爱不爱她,也说不好。不过他在做一个好学生的同时,也想做个好丈夫。 100多年前的3000多人发展成现在的12万人,现在那边家家户户都是亲戚了,奇怪的是这里近亲结婚生的孩子却都很健康聪明,大有一代比一代强的趋势。在这里,没有一家离婚的,也没有一对年轻人谈恋爱的,都是父母做主,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长期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读过书的也不例外。 东干婚丧嫁娶的风俗都没有变,娶亲得先说媒。还固守着“姑娘不外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早已被陕西人摒弃的旧风习。一旦婚事确定,女方就开始准备嫁妆,衣服都是手工缝制,最少得准备半年到一年。结婚的时候,新郎穿手工绣花的袍子和靴子,新娘要穿绣花鞋、红绸衣服,挽着清朝的发型,头上插着簪子,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来庆贺看热闹,婚宴要持续十几天。陈琦在陕西村时恰巧赶上一场婚礼,他给新郎新娘送的贺礼是从陕西带过去的一包茶叶。 有一天安胡塞的大舅子嘎金非得请陈琦去他家吃筵席,席间陈琦问今天过的啥事?嘎金说是他爷爷去世三十周年纪念日,陈琦惊奇地问那三十一周年过不过?嘎金憨厚地说:过呢。过到啥时候?过到想不起了为止么。经历过这些,陈琦对东干人的热情、传统、厚道、铺张感慨得不得了。 签证的日期到了。临走时,陈琦将家乡人送他的一条锦带留在陕西村的村史纪念馆,红底上绣着黄字:家乡的父老乡亲和你们在一起,署名是陕西南陈村。捧着这条锦带,很多人都哭了。在陈琦的眼里,陕西村的人们就如同那条从他们聚居地穿越而过的楚河一样,流淌在欧亚内陆风云多变的原野上,自然而从容。□王蕴茹/文陈琦/图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