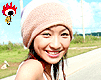青海乌兰县鼠疫死亡事故真相:生存遭受困境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1日17:23 三联生活周刊 | ||||||||
|
10月的某一天,李海(化名)死了,没人知道他确切的名字。他得的是鼠疫。那种致死率极高曾经夺去几亿人性命后来又几乎绝迹的疾病。他原来住在青海省湟源县,那个地方没田种,没工作可做,他独自一人迁去乌兰县,帮人放牧。这个秋天,李海和他的同伴打了几只“哈拉”(旱獭,“哈拉”是当地人的称呼),顺便卖皮子挣了十来块钱,平时他没钱买肉吃,哈拉肉肥味鲜,他当然尝了,结果就中了这致命的病。乌兰县卫生局和防疫站的人紧张地把他的尸体烧了,这个偏僻的地方为此封城两周,所有店铺关了张。不过关心这件事的人并
去年冬天来的时候,乌兰县发生了雪灾,这里许多稀有物种出现大面积死亡。这个脆弱而忧郁的地方,人和其他生物一样,要面对随时可能的意外 记者◎朱文轶 鼠疫是个单独事件 李海是在身体出现异常的一个星期之后才去的医院,他没钱。10月18日,乌兰县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陈瑛和他的手下接到县医院“疑似鼠疫”病人报告后半分钟都没有耽搁,赶过去的时候,李海已经不行了。陈瑛看到,因为痛苦李海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一边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里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到的第一眼,我们就有数了,这是个什么病”,疾控中心的副主任陶国维说,病人当时的体温持续在39.5摄氏度,脉搏每分钟120次,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极度肿大,侧腹部位发现几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们记得,李海满脸布满泪水,在这个地方,他还没有亲人。 李海死后的第三天,乌兰发现另一起鼠疫患者。这个住在乌兰西关村的村民是湟中人,也是移民,就在李海走的那天,他在街上走路,一只全身湿漉漉、看起来半死不活的哈拉摇摇晃晃从他面前走过,几步之后倒地不动了。他高兴地把这个差不多有20斤的肥家伙拎回家,当天就剥了皮。他完全没有在意自己右手不久前割草时划的一道口子,哈拉的血弄了一手。他很快出现体温飙升,呼吸困难,家人送治得早,捡了条命。不过,11月3日,他仍然被关在家里,勒令禁止出行,没人敢到他家串门,虽然在乌兰的大多村子,家与家的间隔其实不过是一道道半人高的土围子。他对我说,村里人最近一直愤愤地骂他。 陈瑛们还是有劫后余生的感叹,他们觉得万幸的是,这两起“人间鼠疫”只是“腺鼠疫”。用专业术语说,区别于肺鼠疫,不会通过空气扩散。那个湟中人的家10米开外,是近30亩的大片墓地,当地回民死后埋葬在这里。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寂静村子上空飘荡着清真寺传出的诵经声,这才让这个人丁稀少的疫区不那么让人恐惧。 海拔接近3000米的乌兰是我目前到过最高的地方,有辽阔的草原牧区,是国内最主要的鼠疫疫源地之一。陈瑛和防疫站地方病研究机构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抗这里的鼠疫,数量很多的哈拉是乌兰牧区最常见的动物宿主。陈瑛说,哈拉每年4月份出蜇,10月份进入冬眠,这段时间是它们体弱多病的时候,“我们也就在这个时候进山去做鼠疫防疫调查”。 虽然乌兰的农民和牧民并没有意识到,但对这种疫病的监控的确是这个地方的头等大事,鼠疫流行季节,陈瑛手下不到10个人一个星期内要三次进山,“山很大,进去再出来,就是四五天时间”,陶国维说,发现死哈拉是经常的事,一般提取标本带回去化验,结果都是死于鼠疫,接着,他们会把发现地的方圆几公里内划为“疫区”,组织清查、消毒。“不过,这种东西传到人身上,我们这儿已经50年没发生过了”。 陈瑛说他们要不断监控疫原动物的地区密度,“通常来说,每公顷活动系数0.1是正常的,高于或低于这个值,生态链就不稳定了”。他的一个手下跟我解释说,他们在山里步行两个小时,如果看到两三只旱獭,这基本表示系数在0.1左右。几年前旱獭突然多了起来,两个小时内会看见六七只,“这就意味着进入疫情警戒状态了”。据说,为了防止疫情出现,乌兰政府这几年几次组织人手对旱獭进行过大规模的捕杀。 季节性围杀旱獭的不光是卫生部门,还有包括李海在内的乌兰县农民,10月份正是农闲季节,他们多数在家无所事事。旱獭偏偏又是种可以创造价值的“经济型动物”。有人告诉我,这两年旱獭皮价格暴涨,小个的一张能卖个十块钱,大个的可以卖到四五十块钱,这种利润刺激着附近县市的农民,他们傍晚开着手扶拖拉机过来捕猎,半夜再偷偷地把抓到的旱獭运回家。因为任何一只旱獭极有可能携有鼠疫细菌,所以尽管旱獭不在保护动物之列,捕食它仍被当地视为非法,但禁令似乎阻止不了这个生意的蔓延。当然,也有人是纯粹因为口腹之需,像那个染上鼠疫的湟中人。在他家里,他向我详细描述过农民们猎捕哈拉的方法:先找到洞穴,把铁丝扣放进洞口,用一块木头或盖板盖住入口,边缘小心地用土封闭起来以防止漏光,一切就绪后就等着它自投罗网了,如果一段时间哈拉还没出来,就用一种自制的毒药熏进洞穴,这种药能弄瞎哈拉的眼睛,不一会儿它就奔突出来了。“不能用枪打,也不能用叉子刺,这样,皮子就不值钱了”,他说。 “哈拉早就所剩无几了,空手而回的人很多”,防疫所的人跟我说,今年他们上山在山沟里逛了三个小时没见着一只哈拉,这说明密度系数甚至已经低于0.1了。为什么反而今年鼠疫会传播给人?陶维国想了想,“是个偶然”。 生存是一连串事件 11月3日,从西宁到乌兰的中巴车上坐了不到10个人,一辆车冷冷清清地从下午开到凌晨,花了11个小时。下了西宁到茶卡的西茶一级公路,“茶德公路”还只是个名称,硕大的土堆堆在路面上,汽车只能在石砾小路中间缓慢地穿行。后来我听当地人讲,冬天修路是个麻烦事,得先把路线刮出来,看见路,然后用铁锹把还未冻死的浮土铲起来往坑里填,柴油还经常会被冻住,让机器发动不了,因此,这条路要到开春才能动工。晚上永不停息的草原风,你看不见车窗外,只能听见电线和灌木在瑟瑟发声。司机重重地抡着方向盘,对面不时有运货的大卡车晃着大灯经过,车就要停下来,卡车扬起的灰尘混着零下20摄氏度的空气从窗口的缝隙中钻进车厢,呛得厉害。车顺着这条路一直驶下去,就是柴达木盆地的边界了。 在我去乌兰的途中,乌兰的牧民也就是在这样的路上开始他们的秋季转场。对他们来说,“逐水草而居”既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习惯。牧场按季节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乌兰牧民以牧草生长周期每年进行3到4次循环轮牧,一般是从高处往低处走,春天把羊群赶到山顶,夏天转到山腰,秋天到山坡或山脚下,每次迁移距离在30公里以内。他们告诉我,这几年,政府帮助他们修建了很多带院子和牲畜棚的房子,却很少有牧民适应砖瓦结构的房屋,他们还是拉着蒙古包迁移。“从10月份开始,高海拔的地方开始下雪,为了避免牲畜在转场途中被暴风雪袭击,10月底我们就开始转场,到山脚下守‘冬窝子’,说是冬季草场,其实也就是少得可怜的枯草,有些还给雪埋住了,要我们去挖,所以过冬主要还得靠秋天打的草保留下来”,一个汉名叫席宁峰的蒙古族牧民对我说。 他们说,10月的某个早晨乌兰牧民的一个家庭吃完了以烤馍和羊奶为主食的早餐,收拾完毡房,由拖拉机和卡车车队拉着日用品、蒙古包,他们赶着羊群朝远方一个水面的方向前进,开始转场之路。 而这两年来的变化是,“队伍不断变得庞大,牧民的牛羊群越来越多了,每户牧民的羊从200只增加到400只、600只。因为草场承包给个人了,草场的面积也不断扩大,1994到1996年承包冬春草场是481万多亩,到夏秋草场已经多了100万亩了。在按存栏数定税而非按出栏数交税的情况下,使牧民事实上也被鼓励通过更多蓄养、超载来弥补亏损”。“羊越来越多,草场越来越饱和,这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是脆弱的”,草原监管站站长洪晓说这是个很无奈的生存局面,牧民的投入一再加大,成本一再提高,一旦哪个环节出现小问题——比如欧洲的某个国家这个冬天突然更流行新型纤维的服装了——你就会损失惨重,投入的成本再也没办法追回。 乌兰所有的关系都是紧张的。洪晓说,由于绵羊不赚钱,牧民纷纷去养绒山羊,乌兰的山羊绒质地上乘,它的价格是绵羊毛的二三百倍,而且国际行情一直看涨,但山羊开春踏青,更是灾难性的损毁草皮,破坏草场。 我在县林业局碰到了乌兰森林公安分局局长马沛,这个原本干劲十足的年轻警司却有着一言难尽的失落。他们有限的人力要看着那些盗猎者,还要制止挖“梭梭”、“盐爪爪”这些珍贵灌木烧柴火的农牧民,而防不胜防的天灾更让他们无可奈何。今年年初乌兰碰上了雪灾,山里的岩羊出现“雪盲”,常常群体性地跌下山崖,“我们一次巡山在一个山脚下发现200多只岩羊尸体”,马沛痛心疾首,“这可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啊”。对于岩羊的大面积死亡,许多牧民却都说至少不算是件坏事,因为这些“讨厌”的动物,常常越过他们的围栏,跑到他们的草场“偷草吃”。席宁峰说,以前他们用枪来赶跑他们,去年,枪都被森林公安局的人收走了。 席宁峰对这些在他们看来侵入牧民领地的岩羊、沙狐、狼实在没什么好感。他抱怨说,就是不久前,在格尔木,一个牧民为了抓住偷羊的狼,在草场外围下了夹子,结果夹死了两只雪豹,兄弟俩因此被法院判了十年,“你说有没有道理?”他反问我。 “说到底是草不够啊”,洪晓说,这上面乌兰还不算太坏,草场相对紧张但目前顶多算饱和,邻近都兰县的草场就更少了。他说,每个县每个村的牧民转场都有专门的牧道,必须按道行走,都兰县夏哈镇查查村因为人多羊多,他们自己的草场退化沙化得几乎快没了,“每年春夏转场的时候,都要绕到我们这边,呆上十天半个月,让他们的羊群吃我们的草,草场都承包了,我们这边的人当然不干了”。马沛也说,这样的“草场纠纷”每年都要发生,每年都打得很厉害。 牧民生活一艰难,乌兰农民的日子更不好过。11月5日,西关村的一个农民何满收告诉我,乌兰只适合种麦子和油菜两种作物,都是一季性的,他们一年有半年时间处于农闲状态。大部分农民选择到山上去给牧民打工,牧民每一次搬迁要修羊圈、盖房子,他们就去干活,盖个房子半个月时间,七八个人加起来挣七八百块钱,修羊圈按1米20块钱算。“他们收入少了,我们打工的机会都没了”,何满收快50了,年轻时候就跟老婆离了婚,现在和弟弟何满伍住在一块。我问这个冬天你干什么?他憨憨地一笑,“呆在家呗,就这么坐着,外面也冷”。可能是坐在家里的时间太长了,他行动迟缓,电话铃响了,接电话的几步路,他慢吞吞地挪了老半天。他的弟弟何满伍据说和一些人种树苗去了,他们家的10亩田属于劣质田,被政府选作“退耕还林”,去年就不种麦子、油菜了,改栽树苗。因为土质不好和缺水,110棵白杨树苗长了不到一年死光了,今年重新栽。“苗活了,我们才能分到政府补贴的粮食”,何满收说。 一些像何满收这样的农民终于还是偷偷上山去打哈拉了。毕竟打到的话,皮子可以卖个好价钱,肉能攒着吃上一个冬天。 马沛对我说,最近乌兰发生了好几起棕熊吃羊的事情,弄得牧民人心惶惶,纷纷向森林公安局汇报。他们亲眼看见被吃得只剩张皮的绵羊就不下百只。一名受惊的牧区妇女报案说,一天她听到羊圈有动静想走出去瞧瞧,转身发现,一头棕熊直直地趴在帐篷口,肚皮冲着她。棕熊是二级保护动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猎杀,乌兰县森林公安局拿到了省里“同意捕杀两只棕熊”的批文后在那个妇女报告的地点,枪杀了两头棕熊。解剖后却发现熊的胃里空空如也,马沛说,“我就说,它为什么下山来,肯定是山上没东西吃了”,“你知道,棕熊是吃哈拉的”。 相关专题:三联生活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三联生活周刊专题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