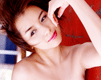宿迁“禁桌令”的政策硬伤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5日18:21 《决策》杂志 | ||||||||||||
|
本刊记者 杨 敏 “没什么稀罕的,前两年沭阳就搞过,老百姓办酒席,乡镇来人说铺张浪费,罚款收钱呗,以前还可以讨价还价呢, 如果乡政府有人还可以收得更少。”6月3日,江苏省沭阳县官墩乡所房村村民祝良健跟《决策》记者抱怨。他说的“没什么 稀罕的”就是指最近引起轩然大波的宿迁“禁桌令”。
又是宿迁,又是仇和 5月1日,是宿迁市纪委、监察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的日子,规 定里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办婚丧酒席不准超过5桌,普通老百姓办酒席不准超过8桌,当地人称之为“禁桌令”。 “禁桌令”甫一实施,媒体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又一铁腕之作”,于是沉寂了一年的仇和再次成 为焦点。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今年1月25日,宿迁市城调队拿出了一份城市居民人情消费统计,指出宿迁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占到总支出的近一成 。当这份调查报告摆到仇和案头,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于是建议市统计局就全市人情消费作一项深入调查。3月8日,统计 局正式向市里提交了4500字的专项报告。 沭阳一位退休乡镇干部告诉《决策》,宿迁的人情吃喝风一直非常严重,在仇和主政沭阳的时候他就着手严刹这种“ 劣俗”。宿迁市统计局专项报告统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报告显示:2004年宿迁平均每个城镇家庭人情消费25.4次 ,消费金额为3107元,占当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7.1%。69.5%的人认为,人情消费负担很重或较重;57%的 人承认,人情消费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压力。 据当地媒体报道,仇和为此专门做过三次批示,第一次是3月12日,仇和批示要求出台一份法规性文件,并给出了 实施步骤的时间表,即4月上旬向全社会公示征求意见,中旬颁布,5月实施。第二次批示是对法规性文件内容的要求,仇和 提出要出台刚性的、有约束力的、具体易操作的、对公务员、党员、百姓有区别的法规性文件。第三次是4月4日,《规定》 征求意见稿在宿迁日报上见报后,仇和批示“要从紧、从严、从高提要求,硬化规定,特别是党员干部要严上加严。” 有了这三次批示,宿迁“禁桌令”有条不紊地按照仇和的要求进行。 据媒体报道,最早碰到“禁桌令”这条高压线的是泗阳县城管大队副大队长胡刚。4月5日,是《规定》征求意见的 前一天,胡刚举办了“39岁生日宴”,十几天后遭举报被免职。 当日,胡刚宴请同事朋友,办了酒席10桌,收受礼金10150元。而《规定》上称,党员、干部“职务变动、新 房落成、乔迁、满月、生日、升学、参军、祭日及其他任何事宜,除直系亲属外,一律不得宴请”。 胡刚事件作为典型被当地媒体多次曝光。据当地纪委发布的消息,1个多月来,宿迁有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行政 和经济处罚,至少13起普通群众“违规”事件被制止。 江苏省纪委书记王寿亭近日对于宿迁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他说,“宿迁市《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若干规 定》很好,对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都有促进作用”,而安徽蒙城也赴宿迁取经,学习其做法。 尽管带有明显反腐动机,“禁桌令”飓风依然无法回避来自社会各界的诘难。深圳市委办李彬博士在接受《决策》采 访时对“禁桌令”的评论简短而有深意,他说:“又是宿迁,又是仇和”。他认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禁桌令”有着 多处硬伤。 “禁桌令”的四处硬伤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汪大海认为,宿迁“禁桌令”的政策制订主体与政策调整对象存在严重错位,这是最明显 的一处硬伤。 在汪大海看来,《规定》由宿迁市纪委、监察局颁布实施,规范对象应该只包括党员干部和公务人员,但是《规定》 却作出了普通百姓办酒席不准超过8桌的要求。 按照沭阳农民祝良健的说法,“我老百姓自己讨钱办酒席,又不是花公家钱,你凭什么管我?”由于沭阳几年前就有 关于所谓大操大办的禁令,加上乡镇在执行过程中处罚行为极不规范,因此,沭阳农民对这项政策的明晰化保持高度警觉,他 们甚至认为这是变着法子从老百姓头上收钱。 中国科技大学的张增田副教授分析说,如果将“禁桌令”理解为一项公共政策,它就违背了基本的行政伦理,因为公 权力在这里无限扩大以至没有边界;但是如果将其理解为一项组织纪律规定,它的规范对象又出现了问题。 政策主体与对象的错位只是“禁桌令”的硬伤之一。人们对“禁桌令”更多的诘问集中在公权力是否应该过多地干预 公民的私人领域。在宿迁《规定》刚刚出台时,就有媒体提出质疑:“政府介入私人消费领域,明显越权”。李彬曾经在中纪 委供职,他告诉《决策》,政府行为只能在“法有明文规定”的领域,而公民行为却是“法无明令禁止”都可以做,这是政府 行为和公民行为的分水岭。以此逻辑推理,宿迁“禁桌令”对私人消费领域的干预,没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作为依据,所以即 使合乎情理也不合法理;另一方面,无论对公职人员还是普通百姓,国家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吃请行为作出禁止。 “禁桌令”被指政府将手直接伸到老百姓餐桌,侵权之虞让宿迁官方百口莫辩。尽管该市纪委一位负责同志申辩,纪 委监察部门并没有直接管过老百姓的餐桌,但是宿迁在酒店办喜事的新人对纪委工作人员的防范心理说明了一切。 “公权力无边界”被李彬称为需要引起人们高度警惕的现象。他认为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蚕食,是公民社会的最大悲哀 ,此为“禁桌令”第二处硬伤。 而“禁桌令”在政策设计上存在明显漏洞则是其第三处硬伤。 “猫鼠大战”是对宿迁“禁桌令”实施过程中,政策主体与客体进行博弈的形象比喻。“现在,县城里的人喜丧宴席 都是分开办的,今天办几桌,明天办几桌,很麻烦,但没有办法,怕给上面查到了。”祝良健告诉《决策》。在宿迁市区,人 们也都是用这种化整为零的办法对付检查,由于《规定》只对宴席桌数有限制,所以人们应对的办法很多,一桌可以多坐些人 ,也可以分在不同酒店同时进行。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对“禁桌令”的政策设计在操作性与可行性方面提出了质疑,他认为, 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一定要考虑到政策调整对象博弈策略的选择,如果操作性不强,政策的影响力就会被化解,甚至还会走向 政策初衷的反面,“这跟以前对公务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没有什么差别。” 很多受访对象认为,宿迁的做法在技术上还存在很多漏洞。以宿豫区蔡集镇朱李村村民薛凯为例,他因为给儿子办婚 宴超过规定桌数被罚款,为此镇纪委还给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薛凯的罚款单是一张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据,盖的公章则 是“中共宿迁市宿豫区蔡集镇纪律检查委员会”,乡镇纪委是执法主体吗?仅从这一点看,“禁桌令”的确禁不起推敲。 不独宿迁,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拍脑袋行为,经常会导致政策制定过程缺乏缜密思考,由于缺乏可操作性 ,轰轰烈烈一段时间之后销声匿迹。 人们对“禁桌令”另一个诘问也是宿迁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人情吃请行为”作为中国一种民间风俗,用行政权力 加以干预,其效果到底如何?“禁桌令”的第四处硬伤体现于此。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朱士群教授对《决策》说,尽管他承认仇和出台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禁桌令”采取一刀切的做 法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弹性,人情太多不行,不尽人情也不行,对于人情吃喝的风气只能引导而不能强制。 的确,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人情吃请行为哪怕是一种劣俗,它也有自身更替的规律,对这一问题的引导和矫正,应该 更多地考虑纳入社会管理范畴,而不是行政权力的强制。 仇和的变与不变 安徽省政府研究室陈干全博士对宿迁的“禁桌令”关注了一段时间,在他看来,仇和在这一次的政策制定程序上几乎 无可挑剔。这跟以前仇和的一惯作风相比是不是反映出一种变化呢? 重视结果,轻视程序,一直是人们对仇和“强人政治”最精要的概括。从1997年主政沭阳,仇和的几项政策在当 地饱受争议都与程序上存在瑕疵有关系。从要求全县干部、教师,甚至农民集资修路,到变卖医院、学校、幼儿园,再到通过 电视台曝光整顿民风问题,没有哪项政策出台是程序完备的。 祝良健至今对仇和集资修路心怀不满,他告诉《决策》,仇和主政沭阳那几年是农民负担最重的几年,他家五口人按 规定一年要负担近3000元的集资任务。而乡镇农经站上门收钱都是打白条,就是今天,所房村村民手中还有那几年的白条 。“修路可不是给农民修的,县城是大了,漂亮了,农村有什么变化呢?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社会治安好一些。” 但也有受访对象认为,从这一次的“禁桌令”,的确可以看到仇和施政中的一些变化。 据报载,在起草《决定》意见稿之前,仇和要求有关部门进行调研,该市纪委宣教研究室的3名成员开了6场座谈会 ,共与六七十人进行了座谈。其中分别在沭阳县和泗阳县与农民座谈两次,规模均为10人左右,村支部书记、村民小组长和 农民代表加在一起,占了三成多。 宿迁当地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普通群众婚丧宴席的规模是通过座谈确定的,“在座谈中有人提出6桌,有人提 出8桌,也有人提出10桌,最终我们参考大多数群众的红白喜事规模,定出了8桌的标准。至于党员干部,为避免其借摆宴 敛财,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我们认为如果只请直系亲属的话,5桌够了。” 经过一周的调查后,《规定》征求意见稿出笼,在4月4日的《宿迁日报》上全文刊载。当地干部称,在《规定》征 求意见稿为期一周的社会公示中,群众通过电话、来信来访参与讨论,并对一些具体条文提出意见。 汪大海教授认为,对仇和开始注重程序的转变应该给予认可,他告诉《决策》,相比仇和以前的作风,还有另一点变 化值得关注,就是宿迁在“禁桌令”实施过程中开始尝试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规定》要求:“各乡(镇、街道)、村(居 )委会均要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理事长可由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负责人兼任,副理事长和理事由威望较高、原则 性强、善理事的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复员军人、老劳模、老教师、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担任。” 据宿迁官方统计,截至5月中旬,全市115个乡镇中100个左右成立了乡镇移风易俗理事会(设在乡镇民政办) ,1441个村(居)委会中有1306个成立了移风易俗理事会。 “仇和尝试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这样的说法却遭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高战的强烈反对。曾经是南京某高校 教师的高战抱着要“为农民做点什么”的理想来到沭阳县官墩乡所房村,他一直致力于新乡村建设,并在当地轰轰烈烈地建设 农民的自组织———农民维权协会。“一开始我们的工作是得到仇和重视的”,高战甚至与仇和就协会的建设问题交换过好几 次意见。但是,所房村的农民维权组织最终还是流产,高战也被逼无奈来到北京工作。“仇和的人治作风是容不得民间组织成 长的。”高战甚至认为仇和在民主问题上一直有“叶公好龙”的嫌疑。 《中国改革》杂志社执行主编焦新望在接受《决策》采访时也不掩饰他对仇和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宿迁的“禁桌令” 尽管在某些细节上谋求政策的合法化,但是“一把手”的绝对权力依然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疑,这跟中国法治社会的基本走向 相悖离。 从这一点上看,仇和还是以前的那个仇和,“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仇和的逻辑一如往昔。 倔强的仇和就像那个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他一次次从山脚推动一块巨石上山,巨石每次滚落,他又将重新开始, 因为他不明白,人治的力量终究无法将这块社会巨石推向民主的山顶。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