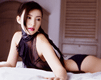三联生活周刊:从国营到混合的电影生产(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3日12:22 三联生活周刊 | ||||||||||||
|
谢铁骊:《暴风骤雨》、《早春二月》的一波三折 1960年进入西影的吴天明感受到的却是一波波运动的影响,“当时都是有计划的,文化部电影局下达影片生产任务,陕西省文化局下达每年的‘工业生产计划’,自然也不用愁片子的出路。不论是‘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上头有命令毫无例外地传达到职工。文化部每年都召开各种会议,这对电影厂有直接的影响”。西影在革命斗争和新社会建
在同样的体制下,北影导演谢铁骊拍片也一波三折。《暴风骤雨》是谢铁骊执导的第二部影片,之前谢铁骊自己仅独立执导过《无名岛》,在凌子风导演的《林家铺子》、《红旗谱》中任副导演。 北影厂原本是想把《暴风骤雨》的本子给李恩杰导演拍,那时周立波的小说获得了苏联的斯大林文学奖,由他在北影厂当编辑的夫人林蓝改编成了剧本。李恩杰觉得他没有体验过土改生活,对东北也不熟,比较为难。15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的谢铁骊在部队呆过10年,在一些革命根据地参加过土改,调入北京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任教时,也曾带着学生到汉阳县体验生活。“这时土改的阶段已经划分得很明显,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诉苦、批判地主、分田地等等。”谢铁骊回忆道,“那时演员完全没有‘大腕’的概念,只是在待遇上有区别不大的文艺几级的薪水。我为《暴风骤雨》选演员时,对女演员没有完全以漂亮来要求。基本上是从北影厂的电影演员剧团挑人。” 当时北影厂受北京市领导,主管副书记陈克寒对制片厂抓得比较紧。陈看到谢铁骊从东北外景拍回来的样片后比较满意,让北影厂将它作为重点影片来抓。“这一下厂领导紧张了,毕竟我是新人”,于是就把北影“四大帅”中的崔嵬、陈怀恺加入进来,准备重拍其中的一些场景。一番讨论后,厂里干脆准备将之改为彩色片。谢铁骊说他当时觉得不对,给陈克寒写了一封信,陈于是批示,“这样搞不对,作为重点抓并不是要换领导”,厂里于是又让谢铁骊单独拍摄了。 1961年6月,周恩来主持文艺界召开了著名的“新侨会议”,鼓励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刚刚拍完的《暴风骤雨》在会议上放映获好评。在新侨会议上,周恩来强调反对“五子登科”——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谢铁骊即使今天回忆起当时会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所以当时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激动,创作热情高涨,我一生参加过的会议,这次最让人激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会上发言也提出,反对影片“直、露、多、粗”,夏衍指责当时的工农兵电影有“直奔主题、毫不含蓄、对白过多、粗制滥造”的毛病。 谢铁骊回忆他当年拍《早春二月》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受新侨会议的鼓舞”。《暴风骤雨》得到肯定后,获得更多信任的谢铁骊开始想拍柔石的《二月》,“我当时的判断是,作者是革命烈士,作品肯定没有问题;调子虽然有些低沉,但是结尾可以改动一下”。 “北影厂的演员适合演工农兵的戏,并不太适合演知识分子的戏。”谢铁骊于是从上海找来孙道临、上官云珠,又从武汉找来刚拍完《青春之歌》的谢芳,谢铁骊对剧中萧涧秋的原型也有体验。他的长兄是1930入党的老党员,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过,国共第二次合作时获释,又投入到宣传抗日的斗争中,“当时与他来往的人都穿着萧涧秋那样的长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早春二月》在苏州取景拍摄,到了后期,谢铁骊收到老伴的来信:“现在中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你的片子里没有阶级斗争,很难拍下去啊。”谢铁骊说他还是不顾一切的把片子拍了出来,在工农兵电影打天下的年代,讲述知识分子的《早春二月》让北影厂感到很新鲜。谢铁骊说,结果,文化部领导来审查时,茅盾、夏衍都非常认同,周扬不赞同,他说:“这是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我完善的翻版,宣扬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之后,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批判文章,接着毛主席要求“把这批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不仅大城市要上演,中小城市也要上演。作为导演的谢铁骊后来听说,“当时很多学校和单位,都把这部片子看了好几次。很多人看了第一次后,觉得很好,看不出政治问题,但是又必须批判,于是再组织观看”。被大肆批判的谢铁骊说他“一到星期天就心慌,《人民日报》整版都是批斗这部片子的文章。”周扬一次开会提到,全国省一级报纸批判这部片子的文章就有300多篇。 《李双双》:60年代的农村类型片 《李双双》的拍摄几乎是一场偶然,在1962年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这部不以阶级斗争为主,却以塑造新的农村妇女形象为目的的影片才可能问世。上影厂导演鲁韧三年前去世了,他在导演手记中写道:“全剧的主线,从头到尾贯穿在李双双这一充满了不妥协的、有强烈生命力的中心人物的成长过程的斗争中。” 影片中的李双双尽管一直在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中斗争,所斗争的对象也不少,但基本却是集中在与丈夫喜旺的斗争中,“是对生活、对劳动、对听党的话、对社会主义集体的两种观点、态度的冲突。”不管怎么说,老百姓看的却是夫妻打架的家庭伦理戏,饱含着中国传统戏剧的精髓。 扮演李双双的张瑞芳当时是很陌生于这个爱吵架的农村妇女形象的,“当时我就是整天练习吵架。”她说。在河南林县的一所蚕桑学校里面住着,无事可做,那就练习吵架吧——她开始把那些阶级斗争的台词念得一本正经,导演说,吵架有这么慢的吗?于是快念,显得双双没那么理智和凶狠了。“导演还教我,学苏州人吵架,热闹但是打不起来。”她学会了边吵边得意地笑,边吵架边人来疯似的笑弯了腰。 丈夫喜旺也不是个简单的落后分子,他憨厚,喜欢乡村吹打,有情趣而聪明。仲星火当时不像张瑞芳,还不算明星,仲星火说导演看上他是因为他“傻大黑粗”。仲星火是部队文工团出身,长期跑龙套,但是政治上很过硬,跑龙套的同时也是各个剧组的团支书、工会组长。1959年,他因拍摄反映大龄民警为群众服务而耽误相亲的电影《今天我休息》而走红,“导演也是鲁韧,他说就是因为我傻大个才找我”。当时还去电影厂附近的派出所体验生活,所长说,演小片警把皮带系紧一点就行了。1949年前的上海众多明星吴茵、上官云珠此时在电影中都积极充当配角。“当时电影成本真低,我们一共就花了17.8元的服装费,民警和邮递员的服装都是借的,我们就花了点干洗费和修改的费用。”《今天我休息》因为“贴近现实生活”而在1960年的北京新片中受到表扬。《李双双》作为河南作家李准的小说也有着“贴近生活”的特质。 当然,也有完全背离生活的地方,拍摄电影的1961年,是中国的灾害年代,在河南林县的演员们根本吃不饱,“我们天天吃南瓜面条。”仲星火回忆,“好不容易吃一次米饭,当地领导专门调配的大米是红色的陈米,和石头一样。”后来怕演员们浮肿,又调来黄豆粉,睡在林县蚕桑学校的地板上,蚊子可以用蚊帐挡住,跳蚤却不能驱赶,也不敢打药,怕毁了蚕种。“每人起床时身上都是红红的包。”而这一切在一部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影片中当然不会有丝毫透露。记者 吴琪 王恺 龙灿 孟静 实习记者 葛维樱 声明:本稿件为《三联生活周刊》独家提供新浪网,如需转载请与《三联生活周刊》或新浪网联系。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