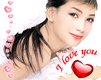中国儒家文化开始复兴 可否成为济世良方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0日09:22 南方日报 | |||||||||
|
特约记者 乌力斯 编者按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新近开张,读经、儒学、国学在中国越来越热了。
3个月前,为了人大国学院的建立,人大校长纪宝成与著名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还展开了一场关于“重振国学”的大讨论。 重新发掘儒学,是否能从中找出应对社会问题的良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提倡传统价值观,是否能消除不断突出的社会矛盾?韩国这样一个重视“儒学”的国家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 在此背景下,本版特约记者独家采访了新儒学的代表人之一杜维明。杜维明正在与浙江大学校方商讨出任人文学院院长的事宜。他的前任是金庸。在浙江大学的眼睛里,身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足以胜任人文学院院长这个角色。 背景 儒学越来越热 上周五,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2005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上,作了一篇名为《弘扬儒学建立和谐社会的伦理思考》的演讲。在谈话里他表示,相比以前,现在能够在一个公开的讲坛上公开地谈论儒家文化复兴的问题,这是非常进步的。 8月12日,美国合众社驻中国记者凯思琳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正在复兴儒学》的文章。8月17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编译转发了这篇文章,将文章改为《儒学复兴影响中国内政外交》发表。 这篇报道认为,中国的学者和官员正在重新发掘儒学,以便从中寻找应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 在更早些时候,200多名海内外的华人学者齐聚北京,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儒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希望从儒学中寻找避免社会冲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处方。 在7月份召开世界汉语大会上,我国政府对外宣布,将在海外成立100所传播中国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学院,这些学院有个统一的名称:孔子学院。在外国人眼里,这一行为被认为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增强,民族文化意识抬头的象征。 从目前来看,当今社会的儒学“热”,似乎仅限于一些形式的铺垫以及某些学者的学理研究,还并没有达到规范道德这一层面,甚至有些时候被简单化为纯粹的文化作秀,或被利用来以传统文化之名而行“政绩工程”。 国际上有些学者看好儒学,使“儒学与21世纪”成为国际文化界的热门话题。澳大利亚两位学者写了一本《儒学的复兴》,认为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正在复兴,“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 专家论儒学 任继愈(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学者): 儒学之所以能持续2000多年,主要是因为它不断地吸取新的内容。儒学的核心精神在历史上已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两极化的发展,现在到了中国文化第三次复兴的时候了。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发扬和传播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徐友渔(学者): 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主张,即“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孔子“复礼倡仁”,不仅是对“礼崩乐坏”社会情状的批判,对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品性下滑的担忧,同时也饱含着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和提升民众品质的强烈渴望。所以,孔子儒学的展开,实际上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对百姓生活、生命的深情关爱。也就是说,孔子儒学是富有批判性的。 儒家学者对儒学应具有真挚的情感。在历史上,确实有某些儒家学者对儒学是缺乏信念的,儒学对他们而言只是通向仕途的敲门砖。章太炎先生所批评的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就是指那些打着儒学的旗号招摇撞骗的小儒、腐儒。 孔子告诉学生,获得儒学之道是最为神圣的,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重新发掘儒学,是否能从中找出应对社会问题的良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提倡传统价值观,是否能消除不断突出的社会矛盾?韩国这样一个重视“儒学”的国家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 65岁的杜维明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看上去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杜维明教授不顾高温炎热,来到中国上海,为的是给由14位复旦大学学生发起的“两岸大学生论坛”作一个讲座。 这些年里,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在中国呆的岁月远比他在美国呆的时间要多得多。时间匆匆,岁月无情,随着年岁渐高,他行走在全球的步伐却越来越加快了。 在他的行程表里,下一年的时间都密密麻麻排满了。 记者一走进房间,杜先生就忙着给记者找喝的,“你是喝冰水还是热茶、咖啡?” 杜维明还在与浙江大学校方商讨自己出任人文学院院长的事宜。他的前任是金庸。在浙江大学的眼睛里,身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足以胜任人文学院院长这个角色。 面对记者的要求,65岁的杜维明详细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成长过程、学术生涯和儒学教育问题。 儒学影响了我的人生 1940年,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就读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父亲,读的是英国文学与经济。母亲是江西书香门第欧阳修家的后人,是当时典型的新女性,很早就离开家庭,前往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就读艺术专业。 我父母给予我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香门第,相反,我是在一个比较西化的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氛围与胡适等人那样的传统文化成长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仔细想起来,我对儒学的最初印象是从母亲和带我的奶妈那里来的。奶妈是江西吉安人,是从农村出来的,基本上不认识字,但是她对我言传身教,给我讲很多故事,或者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对我来说,从小学开始甚至更早一些,这些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对我产生影响了。 传统的儒学为什么能够影响到不认识字的人呢?多年以后,我到中国的乡村实地考察以后,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儒学的一些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经过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官方的传播,再经过民间的文学艺术创作演绎以后,已经融入到最底层的普通中国人的认知观念里了。 传统书院式的学习 我的童年一直跟随着父母迁移。我出生以后,父母从昆明到了上海。在上海的9年时间里,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母带着9岁的我去了台湾。 在台北的中学读书时,我遇到了影响一生的人——周文杰老师,周老师是新儒学第二代代表牟宗三的弟子。 当时的学习的方式也类似于孔子与弟子间的那种辩难、讨论,大家一起读经、释意,气氛活跃而融洽。这样的讨论式的授课对我启发很大,它有点像传统的书院,也许受到佛教的影响,像语录、问答、讨论和辩难等。 我记得当时共有五位同学参加,其他四位现在都在理工方面很有成就,其中一位现在是新加坡工学院院长,一位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位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直到现在我们五个人还会经常聚聚,在一起时更会谈起那段生活,感觉很好。 师从牟宗三 在周老师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他的老师牟宗三,当时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国哲学讲座,在空余时间里,我经常去听他的课,并报考了牟先生所在的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哲学专业。 当时东海大学中文系每一届只有七个学生,而教授却有十几位。有不少刚刚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学生来给我们教英文课。 很多时候我们上课都是在教授的家里。基本上都是一对一,比如说史记这门课程,我就经常晚上到教授家里,标点史记,一句一句地进行,有问题就问,还会闲聊其他一些话题,感觉很轻松、活跃。 事隔多年,我还记得当时在鲁实先家中标点《史记》、向戴君仁学《论语》、从孙克宽读历代诗选、杨容若指导中国文学史。当时的乐趣太大了,太大了。 我纯粹是出于兴趣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的。大学毕业以后,我获得了“哈佛——燕京奖学金”,因此得以有机会去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 我的哈佛学术生涯 在当时的哈佛大学,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偏重当代的政治研究,属于显学,比如以费正清研究中心为代表;另外一派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比如燕京学社。费正清先生曾希望我作他的弟子,但是我对传统的文化研究更感兴趣。 我发现哈佛在教育方式上和东海大学很像,经常会举行研讨会,教授基本上是导引大家讨论问题,而不是将已经消化的知识传授给大家。师生之间的对话是互动的。比如,有一个学者是研究希伯来文化的,他是一个资深教授,我是个研究生,我是去向他请教,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身边摆着一叠小卡片,我谈了以后他就去记,谈完了以后,我发现他记的比我记的还要多。他是想从我这边多了解关于亚洲传统、亚洲文明的知识,他很虚心好学。以后我还通过很多渠道,跟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接触,感受是相同的。 大陆的儒学研究有明显的断裂 当时在哈佛还有一个要求,只要你学习和中国有关的东西一定要学习日文。这种要求很合理。因为日本汉学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有很多优秀的论文,比如东京和京都都有长期的汉学积累。反而中国的学术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后就断裂的非常明显,儒学研究以北大为例,可分为五四时候的北大、国民党时候的北大、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北大,文革以前的北大,文革中的北大,文革后的北大和现在改革开放的北大,不仅观念、教学理念,人物和传统改变了,而且研究的课题和意识形态都改变了,变化很大。至于日本,相当一段时间由于没有断裂,汉学传统积累比较深厚,台湾在1949年以后学术改变不大,因此也有一定的学术积累。 儒家的传统是多元多样,非常复杂的。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文化,你对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还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对儒家传统有个全面的认识。很多第一流的中国儒学家,基本上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儒学是鄙视的,认为他们都是拿了我们的来模仿。可以说,中国儒学学者对日本、韩国的儒学的认识并不多。 儒学有美好的未来 对儒学在未来的发展我很乐观。从1978年开始,我就开始回中国内地做访问和交流,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课,之后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现在,我已经在内地的几十所大学做过有关儒学的演讲,我还在内地几所大学当老师,带了一些博士研究生。 在这些年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儒学在大陆发生的变化。1978年,我最初接触的多是老三届的大学生,当时他们只是把儒家当做严肃的课题来研究,人数不多,而且他们并不认同儒家的价值观,不把儒学当做立身存世、人格修养的学说,不把它当作生命哲学,而且往往还持批判立场。 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视野的开放,传统文化的复苏,中国人要求重新认识、理解传统,甚至继续创造、发展传统,这个意愿非常强烈,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从黄色的土地进入蓝色的海洋”,想把脏水和孩子完全抛弃掉的态度完全不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 有很多人误会我杜维明,认为我从事儒学研究,总是想儒学一枝独秀,想独尊儒术。 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觉得,儒学在中国最近这一两百年里的命运太悲惨了。因为命运太悲惨,如果能够为它陈词,让它有再生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责任。看世界几大精神文明:基督教、印度教、佛教、中东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希腊哲学,再有中国的儒家哲学等…… 为什么其他的传统一直在健康的发展,为什么儒家的传统受到那么大的批判?为什么影响遍及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儒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或幻想过要把儒学变成一枝独秀,即使是能够一枝独秀,我认为也是不健康的。 儒学的未来在中国内地 曾经有人认为,儒学研究的希望在韩国、日本,其实,在我看来,儒学将来的发展在中国内地,不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是中国人才济济,30至40岁左右的一批学者正在集中亮相,如给这批年轻的学者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以他们的视野和基础,儒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 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机构做了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我想如果现在再进行调查的话,答案可能有变化。 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素质问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能在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这个时候,它的文化资源慢慢累积要厚。华人社会里,从事理科研究的都是聪明才智之士,真正从事文化传播尤其是文史哲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这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虽然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很少,但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访谈 我是儒家文化的守望者 记者:9·11以后,儒学、亚洲价值受到了更多人的质疑,你怎么看待儒学的负作用? 杜维明: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儒学也有负作用,比如韩国是一个儒学非常深入的国家,在韩币1000元的钞票上,印着韩国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李退溪的头像和它的书院,这说明了儒学在韩国的重要性。 前几年韩国发生了金融风暴,这场经济危机是它的大财阀大企业引起来的,比如大宇、现代,这些企业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出现这样的经济问题,一个国家都遇到了麻烦,这里面有没有儒家因素?当然有儒家的因素。 但是,当韩国要自救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种共赴国难的精神,比如为了不让政府破产,韩国的家庭主妇甚至都把自己的耳环、戒指都捐给了政府,和政府一起努力,度过难关。在政府和人民的一同努力下,韩国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而且它现在把文化也搞成了一个强大的产业,现在开始对外输出文化了,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经济不能发展、社会变得不稳定、贫富不均的问题出现,有很多是儒家因素。但同时它也能够发展国家和社会,推动经济发展,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仔细地分析、研究,去弊取利呢?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反对新加坡提出的国家、社会和社群高于个人之说,我认为这不是儒家思想。 国家社会只有在可为个人创造适宜发展的条件时,才会高于个人;若国家腐化社会庸俗,个人可以说不。虽然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如果它想要长期、稳定的发展,它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者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激进主义者,但是到老的时候,成为了保守主义者,比如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这样。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杜维明:我现在对文化保守主义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在美国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朋友,他是我的忘年交,叫丹尼·贝尔。他说,“在经济的领域,我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特别突出分配的重要性,在政治领域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我对人权、法治、自由、平等观念特别强调,在文化上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我要承继我的犹太教文化。” 这个说法非常好,大家总是把保守跟激进、和自由分开来,这其实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区分方法。但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一些研究基督教神学的杰出人物,事实上他们在美国自由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不能因为他们认同基督教就说他们是保守。我们可以把保守的观念理解为一种保存、继承,就像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这种继承的本身又有创造,又有重新的诠释,就是重视文化。 我保存,我保护,我发扬,我关心,我关怀。所以我们对文化保守,应该有自己的定义。 我愿意改革,不平等的事情我愿意改变。但是我对文化的继承,对传统观念,非常重视。我认为文化保守不仅是上层结构的内容,文化保守对人的整个日常生活起到很大作用。 人物简介 杜维明: 祖籍云南,1962年台湾东海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胸襟。 目前在中国大陆8所大学做兼职教授。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