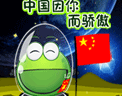巴金为家族和大哥创作了《家》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11:47 生活报 | |||||||||
|
巴金的小说《家》中的主人公高觉新原型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李尧枚的儿子李致撰写了文章,回忆他的父亲(李尧枚)和四爸(李尧棠,即巴金)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手足之情。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母亲卧室里就挂着一张颇大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眉清目秀,身着西服。母亲说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名叫李尧枚,字卜贤。母亲和长辈众口同声,说他是好人;在学校功课好,在家学过武术,喜欢阅读“五四”以来的新书报,热心为亲友帮忙,会办事,还懂医,能为亲友看些小玻他死后,连邻居、小贩都感到惋惜……但所有的人都说他不该自杀。 上中学的时候,读了四爸李尧棠(即作家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我才对父亲有所了解。《家》中的高觉新以我父亲做原型。父亲自小就很聪慧。他对化学很有兴趣,希望将来能去上海或北京上大学,以后再到德国留学,脑子里充满美丽的幻想。可是高中毕业后,祖父给他娶了妻子,结婚不久又为他找了工作。父亲顺从着,毫不反抗。但回到自己屋子却伤心地哭了一常祖父逝世后,父亲又担负起我们这一房的生活重担。 五四运动发生了,父亲和三爸、四爸都受到新思潮的洗礼。父亲的见解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正如四爸所说,我父亲“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这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这是以后所发生的悲剧的根源。 曾祖父和祖父死后,父亲做了承重孙,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用处。四爸说,他和三爸“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我父亲招来更多的麻烦。我的哥哥李国嘉在他四岁多时突患脑膜炎逝世,对父亲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精神抑郁,偶尔还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后来,父亲帮助三爸和四爸到南京读书,又支持四爸去法国留学,希望他们学成后回来兴家立业。由于大家庭分家,田产收入减少,父亲曾另想办法增加收入。他开过书店,但因经办人选择不当关门。继而把田产抵押出去,希望用贴现的办法取得较高的利息,不料他生了一场大病,等他病好才知道好几个银行倒闭,全家的“养命根源已化成水”。他感到愧对全家,终于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父亲离开人世,把母亲和五个子女留在人间,让母亲独自承担莫大的痛苦和灾难。 四爸后来曾对我说,你父亲如果放下绅士的面子,过一般人的简单生活,完全可以不自杀。他懂医,可以好好学医,成为一个好医生,解放后说不定还可能当一个政协委员。 为我父亲,我和四爸有过辩论。一九六四年九月我第一次去上海,我向四爸提出要去给三爸扫墓。我没见过三爸,但我非常尊重他。主要原因是父亲去世后,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主动用教员的薪水供给我们全家生活费用,努力工作,省吃俭用,直至抗战开始后联系中断。当抗战胜利时,三爸贫病交加,逝于上海。 在去墓地的三轮车上我们谈到父亲。我说父亲丢下母亲和子女去自杀,太不负责任。我当时年轻气盛,用语相当激烈。只记得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对父亲的“谴责”,在我心中保留了几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四爸交给我父亲给他的四封信。这四封信增进了我对父亲的理解。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父亲谈到“对人类的爱”。由于四爸在小说《灭亡》的《序》中谈到过他和我父亲的差异,父亲在信中表示了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说:“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在谈到他俩的差异时,父亲说四爸“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而他对“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他俩“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接着父亲又强调“我俩对人类的爱是很坚的”,“我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 我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四爸写小说《家》。他在信上说:“《春梦》(即以后的小说《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他还鼓励四爸不要怕,说:“《块肉余生》(即狄更斯的《大卫·高柏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我通过这四封信,接触到父亲的心灵。此后我不再谴责父亲对母亲和子女不负责任。尽管我仍不赞成他自杀。对四爸在小说《秋》里,没有让觉新自杀,我也有了新的理解。四爸本想通过《家》鼓励父亲,勇敢地面对生活。但小说的《序》刚在上海时报连载,父亲就在成都自杀了。四爸为此感到“终生遗憾”。写到《秋》的结尾,四爸既想给读者希望,更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一九八六年春,我就父亲的四封信,与四爸有一次较长的谈话。最令四爸痛苦的事,是两个哥哥都是因没有钱而死去。四爸痛哭失声地说,我现在有钱,但钱有什么用,我又不想过好生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四爸。四爸对我说,“一个人做点好事,总不会被人忘记。我时常想起你父亲,他对我有很多帮助。你三爸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知道,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但我希望他两人也被人记祝”几十年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终于理解了父亲。 (摘自《解放日报》) (生活报)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