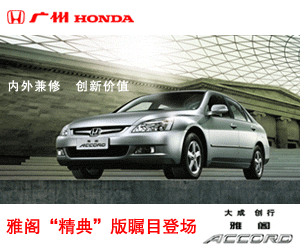|
|
|
|
|
曹禺之女推出自己首部话剧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5日11:42 环球人物
本刊记者 路琰 北京人艺的小剧场里,演员们正在排练话剧《有一种毒药》。“我的话剧第一次能在这里上演,总觉得是天意。父亲 在天有灵给我加油!”在戏剧大师曹禺逝世10周年之际,他的女儿万方推出了自己的首部话剧,是为纪念。 此前,万方已是著名作家。她的名气并非因为父亲,而是源自她的“魔镜”——2002年创作编写的电视剧《空镜 子》跻身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风靡一时,获多项大奖。直到现在,还有电视台在一次次地重播、回味。 曹禺写《雷雨》时才23岁,而万方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与话剧擦肩而过了这么久,无论是宿命还是使命,她终于 完成了。拉开大幕,她的遗传因子、苦乐人生让我们有怎样的期待? 距离2006年12月19日首演只剩下两天,采访只能安排在排练的间隙。小剧场名副其实,观众席只有百十个座 位,为了不打扰排练,万方挑了离舞台最远的角落坐下,提醒记者:“咱们小点声。” “毒药”是什么 “父亲的戏摆在那儿,话剧对我来说是很高的,必须有能力接近那样一个标准,我才敢写。”像《雷雨》一样,《有 一种毒药》是家庭剧,情节矛盾在一家四口人之间展开。 万方轻声背诵了一首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 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一下子被这首诗点燃了!”她下意识地转过头,回望自己过去的几十年,大多数时候 为了生存劳碌,忽略了内心真正的渴望。万方相信,人们对自身生活的不满意,也缘自这种相同的渴望,这是激发她写《有一 种毒药》的情感所在。 在《有一种毒药》里,剧中人都生活在矛盾、问题和痛苦之中,但却不明白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公公年轻的时候爱唱 歌剧却被迫放弃,患病的儿媳和嗜钱如命的婆婆时常“战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内心追求,却又相互冲突。话剧直到最后 20分钟才揭示真正的主题——人应该怎样活着。就像一个人,衣衫锦绣,层层绫罗,然后站在你面前一件一件往下脱,直脱 到什么都没有了,突然把心掏了出来。万方忍不住一再重复:“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特别喜欢。” “为什么叫毒药?”整个剧本写完了,万方才突然决定用这句戏里的台词作剧名。她说:“我无法告诉人们什么是毒 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怀着渴望。无论它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是痛苦还是快乐,是迸发而出的创造还是可 怕的破坏,我们都无法遏制,别无选择。幸福是一种毒药,爱情是一种毒药,渴望也是一种毒药,这毒便是对心灵的侵害。” 这是《有一种毒药》的首演,万方很上心。演员一开始走台,她的眼睛就黏过去看着,不时地在台下提词。对台词的 时候,有一个字甚至一个语气觉得不太妥当,也忙不迭地过去跟导演和演员商量:“话剧尤其需要人物语言的精确与精彩。” 在万方的眼中,话剧有着无法比拟的魅力。“在黑漆漆的剧场里,面对面的表演给观众带来的冲击和碰撞,是电视和 电影无法替代的。这就像是你在电影中看到的死亡和亲身经历的死亡场面,不可同日而语。”一次偶然经历,让万方体会尤切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另一个人三两步就跨上车后座,我正好也推着车跟在后面。突然,前座的小伙子倒在地 上,脸色唰地变了,原来他心脏上被扎了一刀。那种亲见死亡的感受,像人一下子被扼住了咽喉。”她停顿了一下:“舞台剧 对观众的冲击就是类似的力量。” 虽然话剧的魅力如此独特,但万方承认,在当下这只可能是小众的欣赏。人们已经活得太匆忙,鲜有人肯坐下来跟自 己、跟生活说说话。“如果有人看了这部戏,能给生活一个停顿的时间,问问自己这样匆忙究竟为了什么,我也就成功了。” 那些人,那些事 或许因为经常跟着父亲看戏,万方最初的梦想是当演员,从没想过要当作家。说到这,她自嘲似地笑笑:“可我这小 个头,最多也只能当儿童剧演员。”曹禺那时也更希望女儿们学习自然科学,万方的大姐学了医,二姐学音乐,还没有轮到万 方选择,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曹禺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万方的生活一下子翻了个底朝天。 “现在很少有人能体会到,忽然间生存的颠倒,比一切人都低贱的感受,甚至产生了对自身存在的恐惧。”从著名剧 作家的女儿变成了黑五类的孩子,还在上初中的女孩儿,既敏感又要面子,各种压力让她抬不起头来。到了学校,万方的神经 会绷得更紧:“有些孩子挺能捉弄人,在地上画个圈‘你进去,单腿站着!’这不是闹着玩,是真的惩罚。”那段日子,正常 的生活丧失了,但万方获得了从前想象不到的东西,她开始拥有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不同的人生体验和积累。 16岁那年万方到东北农村插队,“一帮十几岁的孩子胡乱活着,没饭吃,甚至偷鸡摸狗。”农村的日子很苦,却比 城里快乐,不用看谁的脸色,压在心里的石头没有了。可是,更大的苦痛埋伏在后面。1974年,万方的母亲突然病危。“ 我永远都记得,怎么样挤上火车,站了一夜,但还没到家,妈妈已经去世了。”万方吸了口气,伤痛这么多年还没缓过来:“ 到现在,晚上我都常做一个梦,在找我妈,夜里老会哭醒。” 这些经历,像烙印似地改变了万方的内心,也渗入到她的创作中。万方早期写的小说,她自己形容“非常狠,全都涉 及到了死亡,有非常极端的东西在里面”。拿过去给父亲看,“他不多说,淡淡的,我已经明白,他不满意。后来,他对我说 ,希望我站得更高一点,不要陷在个人的情感中。” 万方选择写作,是因为“没得选择”。文革中断了她的学习,从部队退伍回到北京后,她当了编辑,这是她当时唯一 有信心的工作。也从那时起,万方开始尝试创作,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当,她常常怀疑自己究竟能不能当作家。小说《杀人》是 她的第一个转折,这篇小说发表在《收获》的头篇。“那时我父亲住院了,他一看到我来非常高兴,说你真行,你真的能写。 ”如果说这时万方开始从自身情感的局限中脱离出来,写电视剧《空镜子》时,她已经可以走进胡同里的百姓生活,从容散淡 地讲述家长里短。她的笔触日渐成熟,人情练达,珠圆玉润,只是现在没有父亲在身边夸一句:“小方子,你真能写。” 从未想超越父亲 人们总会拿万方的第一部话剧和她父亲的相比,《雷雨》也是曹禺的处女作。有人认为《有一种毒药》继承了父亲剧 作中的经典气质;也有人说,相比《雷雨》中紧凑的生活化人物对白,《有一种毒药》中莎士比亚式的抒情独白让观众感到了 距离。面对着这些评价,万方说自己没有太大压力,因为“从未想超越父亲”。 “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人有兴趣,在生活中怀着一种极深的情感去观察人。别人没有看到的,我看到了。”父亲 甚至有目的地训练万方去积累生活素材:“他让我记下每天看到的人、有趣的话、有趣的事;我渐渐养成习惯,在街上走路, 在餐厅吃饭,甚至聚会聊天,我都会把别人没留意的东西收入眼里。” 对于父亲一生挚爱的话剧舞台,万方太熟悉了。还没懂事,她就被父亲带着看排练。“一直跟舞台接触,话剧在我心 里早就有了根。”这种情结,在万方心里若隐若现了半个世纪,现在终于通过《有一种毒药》开枝展叶。万方原计划用一年的 时间来写,没想到居然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巧的是,年底北京人艺正准备公演曹禺的几部名剧,作为大师10周年的祭奠, 也趁此机会把万方的《有一种毒药》搬上舞台。首都剧场是曹禺担任北京人艺院长期间建造的,“从剧场设计到筹集资金、建 设,我父亲从头盯到尾。小时候他带我来看戏,他老了我扶他来。我的话剧第一次能在这里上演,总觉得是天意。” 人生最大的炼狱 万方曾经用《空镜子》平凡质朴的百姓生活打动人们,而她自己的生活也一样有平凡的苦涩。万方说,失去亲人是人 生最大的炼狱。她曾经是一个男人的女儿,一个男人的妻子,另一个男人的母亲;现在,她的前两个身份都丢掉了。但这个明 慧通达的女子,懂得如何对待不能掌控的别离:“这是生命的一部分,无法逾越,人活着就是要体验这些,感受这些。生命是 什么?不是任何的物质,而是一段段的经历和从中感受到的东西,组成了你的生命。” 纵然想得透看得穿,她的整个生活状态仍然被改变了。她怕热闹,怕被人盯着看,怕惹人注意。更多的时候,她只愿 意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不过这样一个人,却喜欢探险的故事:“我虽然不去探险,但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精神, 因为他们更接近内心的需求。我现在登山是不可能了,我只能追求心灵的自由,让自己的心灵更平静、更安宁、更宽阔。” 万方的儿子现在做导演,经常在外面跟着剧组奔忙。母子俩没有太多时间见面,陪伴万方最多的,是家里的小狗。晚 上她几乎不参加任何应酬,怕小狗在家里孤单。 记者忽然想起,和万方约采访时,本来说好到排练的小剧场里见面,她却一直站在剧场大院的门口等候,很可能就源 于电话里记者不经意问的一句:“小剧场在哪?” 或许,对每一个人来说,孤独都是人生最大的无奈;难得的是,在孤独中,仍然对他人怀有一颗温柔体谅的心。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