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农民需要途径表达利益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8日09:26 南方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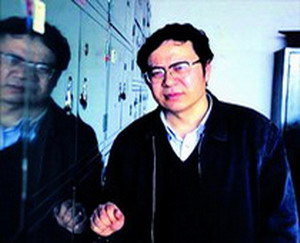 于建嵘为农民代言,被称为“行走在乡间”、“用脚写作”。资料图片 “人大代表他可以不是农民,但一定要是农民的代表,起码要增加农民选举的权力。 我们要找到一个社会平衡机制。多元化的社会一定要有多元化的表达。” 对话人物 于建嵘 1962年生于湖南衡阳,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斗争》、《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风险》、《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等。 于建嵘是信访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从农民税费抗争到土地维权,再到信访改革,他展现了一位学者关注现实最尖锐问题的勇气和敏锐,他所发出的声音也屡受高层重视。 他是重建农会的积极倡导者,多年来,他奋笔疾书,为农民代言,希望农民早日有一个表达自己合法利益的途径。 所有的问题都与利益表达相关联 记者:人们都说,这些年来,变化最大的是城市,农村在改革中惠及的层面大吗? 于建嵘:其实,经济改革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不但城市发生了变化,农村的变化也很大,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充分发展,有目共睹的是,农民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记者:回顾十年的变化,邓小平曾提到的有关农村和农民的一件事还没有做? 于建嵘:是的,那就是关于农会,我到处讲,我也多次提到过,邓小平曾经在很早之前就讲到农会的事。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经给邓小平建议过要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当时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我的理解是,邓小平可能要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不是需要这个体制性安排。 我认为,邓小平的意思可能是对于农民成立农会的要求,应该保持战略性模糊。政治需要有战略性的模糊,需要有一定的灰色地带。改革中的政体尤其必须保持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不能把不成熟不完善的体制僵硬化。农民组织的存在是个既成的事实,无法否认,也不能消灭。 记者: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后,需要有一个新的体制安排? 于建嵘:我们肯定这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农民来讲,这十年来最大的实惠就是取消了农业税,把几千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座大山搬掉了。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 为什么城市化的进程比较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农民因户籍制度无法转移到城市,二是农民的土地权益无法得到保证,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不仅制约了农民的生存权利,也制约了他们往城市转移。由于他的土地在农村,他的根就制约了他往城市转移。第三个问题就是环境污染,土地受到的污染危害已经很严重,这也是我这两年研究的一个方向。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于建嵘:我认为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与另外的问题相关联,那就是与农民的利益表达相关联。农民没有办法进行利益表达,在几个层面的社会表达中,农民都是弱势。全国人大代表中很少有能够体现农民利益的人,代表农民的都是些官员,在最高的权力机构中间,没有人表达农民的利益。另外一个就是农民组织问题。现在我国安排的体制是村民自治,我认为十年来,村民自治的成果正在流失。我曾经和吴思做过一个对话,谈到乡镇改革的问题,比如村财乡管,乡里的干部下派,村干部由乡镇发工资。拿工资必须听上面的话啊,这导致了农民的利益表达出现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无全国性的农民自治组织,就是农会。村民自治和农会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概念,两种形式,而区域性的行业协会、经济合作组织都无法表达农民利益。 记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改革是不是到了有一个农会的体制性安排的时候? 于建嵘:经济发展到了目前这个地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农民组织农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感觉到目前,一定要培养农民的组织意识,农业经济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也需要一个新的机制安排,所以,中央做了一些决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去年就出台了《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法》,想解决农民的经济合作问题,但还没真正涉及解决农民利益表达的问题。我认为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制约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所有的问题都与利益表达相关联。 我建议有关方面应该对农民自发成立农会一事予以高度重视,在农民自己要求重建农会的地区,可以在一个县范围内进行试点,并加强引导和规范。 记者: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是组织不起来的? 于建嵘:不是能不能组织起来的问题,是体系的问题,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应有一个制度保证,不是农民有无组织能力的问题。我的书中有详细的调查,你看看农民在下面搞什么,是怎么组织起来? 记者:如果有法律真正出台,让农民可以组织起来,会不会一下子乱起来的? 于建嵘:不会乱的,所有的组织性的社会可能带来冲突加剧,但都是有秩序的,是可控的。台湾的农会也不是随便开放的,也是政府规定的农会,台湾的农会闹一阵儿,但很快就可以停。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乡村是稳定的,下层是温和的。 有组织的社会产生的动乱、冲突是可控的,没有组织的社会发生的冲突是骚乱,是不可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黑人运动,走向了组织化,但没有走向社会骚乱。今年4月10日,法国政府将邀请我去考察他们那里的社会骚乱,法国少数族群的骚乱就是因为没有组织化导致的。 土地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记者:有人说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于建嵘几个人闹的,如果不是你们闹,是不是不会改? 于建嵘:怎么会是我们这些人闹出来的?有人说我写农民闹事,李昌平为农民呐喊。并不是我讲话有人怕,是我告诉他,现在有农民在闹,我告诉他一个事实。温家宝总理不是说,农民的钱,我们不要不就行了吗? 千万不要高估学者的作用,农民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是自己为自己做主。 记者: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最直接的实惠是什么? 于建嵘:税费改革是一件大好事,肯定是对的,但配套一定要跟上啊,没有配套就不能做下去。 记者:但好像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于建嵘:税费改革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把从农民那里拿走的还给了农民。但是由于产权不明晰,从农民手里拿钱变成了从农民手里拿地。 记者:农村税费改革后,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于建嵘:农村取消税费,农民为农业税闹的事情减少了,但是土地问题加剧,现在土地就是利益,以前土地是负担,现在种地有国家补贴,土地就变成了有价值的资源,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也增加了。 还有,计划生育问题出现了。原来计划生育在政府收税时还不是问题,而现在政府卖指标,计划生育变成了生财的路子。我调查过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一个计划生育指标几千元,分下去,每个人去搞点钱回来。限制生育变成了动员生育了,本来要控制的,结果变成了多生,我的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记者:在税费改革的同时,又进行了乡镇合并、精简机构的改革。 于建嵘:我以前就提到过,中国农村的综合改革还没有真正起步。把税费取消了,撤乡建镇、精简人员,但是,大家把原来的财产卖了,挪到另一个地方办公,还是那么多人,撤乡并镇有什么用? 记者:农民没有了土地之后,可以转移到城市去,有很多地方已经放开了户籍管理。 于建嵘:是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去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有配套的措施,户籍改革不能只是给一个空头的城市户口啊,一些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了还要回农村争那块地?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记者:税费改革之后,土地是不是就成了农村最大的问题? 于建嵘:中国目前的农村问题差不多80%是土地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土地是最大的利益,是农民的低保。我们原来的调查是60%-70%,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预测,能够看到前面一步。 早几年我写农民土地问题,很多人攻击我说,农民不存在土地问题,很多人不想种地了,现在看是怎样呢?农民有一块地,心里是安定的。为什么现在的事件多发生在沿海和水库移民地区?什么原因?因为把农民最根基的东西夺走了。
【发表评论】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