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民周刊:王朔“人来疯”-我就一京油子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04日12:55 新民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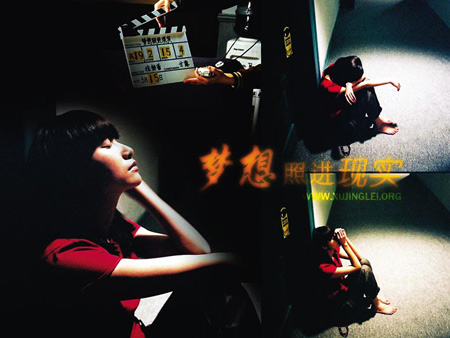 从《渴望》到《梦想照进现实》,王朔在影视圈风生水起  面对众多媒体,王朔“舌战群儒”  王朔觉得用佛和药物把世界打通了,有时候很自信,有时候又很不自信 窦文涛说,王朔说话有口腔快感。说得有道理。每隔一分钟,王朔就爆发出得意洋洋的笑。他有疾风骤雨般的口才,没有咯噔,决不忘词,决不车轱辘讲话。后一句紧赶着前一句,把他的口腔快感一直延伸到听者的耳朵里。说话显然让他兴奋:没有寒暄、客套、敷衍和渐入佳境这一套程序,劈头就是迭起的高潮。不管站着、坐着、斜躺着,都是一言堂。 这连绵不断话语的高潮让人兴奋,也容易让人疲劳,一如他2007年高调登场至今的全过程。在这个兴奋又速朽的王朔的高潮中,最后出场的是一本27万字的书,提醒世人这滔滔不绝的中年人的身份,原来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作家。是的,一个作家。他的新作甚至一改从前的语言风格,显示出突破的努力,可惜,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在盛大的发布会上,媒体将滔滔不绝的他包围在中间,几乎无人提及这本白色的书。写作的得与失,成与败,都不再重要,也无人评价。这个高度兴奋的“人来疯”,这个文学上曾经的重要人物,他的影响还在方方面面发挥余热,本人却乘着娱乐的狂潮,在口语的自我复制中,一阵阵爆发出微醺般的高亢大笑,越行越远,渐渐难辨来路与去向。(汪 伟) “我没病,严重正常” “我先前是想和知识分子认同,后来发现反了,人家还不和我认同呢。你说我跟谁认同去,我跟痞子认同去?后来我认同这个了,问题是这还是一个社会身份,还不是我自己啊……” 撰稿/钱亦蕉 汪 伟 3月31日,王朔飞赴上海,准备参加第二天召开的新书发布会,当晚,他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个半小时的对话,王朔的语速飞快、语音高亢,连绵不断的话语高潮让人兴奋,也容易让人疲劳,一如他2007年高调登场至今的全过程。 刚走上社会的看韩寒去吧 以前读过你的不少小说,这次的书跟以前的写法有些不一样,用北京土话写历史、写经? 完全不同。我本来想换个名字出,他们还以为一新人呢。法国有一小说家,出完名以后就没了这人,好多年以后又冒出一个小说家,特别火,大家一看原来是这哥们。我原来也想来这一套,但谁叫我太虚荣,我他妈拦不住要吹牛逼,这不就吹现了。可是现在我要假装出一个吧,这些(人)还要你改,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各出版集团就拿大钱砸了,其实我本来不想这时候出的,后来路金波也跟了好久了,出吧。加上大家不是都说我只会聊天,不会出书嘛。我哪受得了这个呀,那就出一个给他们瞧瞧呗,就这被人激了将了。 本来说要挂在网上供下载的,可现在为什么还是出了纸质的书了? 本来我想等“鲜花村”(网站)开了,挂在那上面的,所以这都是没写完的,《金刚经》也是没写完的,你要是看不惯北方话你就看《金刚经》。家里死过人吗?要是一生出来(到现在)都很满意那就没办法看了,得是家里死过人的,岁数太小不能看,太赶时髦的人不能看。北京话,其实不太多。北京话我也是掌握在即使不能全解,看大意也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譬如他们给我改了一个字,我就说我住在那广东,广东下的每场雨我都沦着了。北京话说沦着雨,是三点水那“沦”,他给我改成轮换的“轮”,我一看,这你不能给我瞎改呀。我原来就说,我就是把那写作痕迹都搁那上面了,我别装完人啊,当完人我多不主动啊,留点破绽在上头。 出得挺好,但是这样的装帧是给年轻人看的,字号也有点太小了,其实我觉得这书适合年龄更大一点的人看,所以我说如果能再印的话,出大三十二开,至少要小三号字,我眼没花我能看,但我周围好多人眼都花了,里面那注释就太小了。 你觉得这书是更应该给经历过生老病死的人看的? 至少预感到这个,至少有过悲欢离合的,刚走上社会,刚开始斗情的,看韩寒去吧。我们可以孙刘斗仲,太年轻看不懂,看不到心里,当时髦赶,对不起,你还赶不上这时髦。 成功人士建议不要看,跟他们没关系。 这次的书还是保留了很多口语? 我觉得语言是从口语来的,你得与时俱进嘛,因为我是口语写作,所以我不能受它拘束,要不我说突破就是说这里突破,现在我们快变成文言文了,党八股一进来,政府公文用语接近于文言文了,他是一套官话,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你不了解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这个你念一遍,琅琅上口,当然写的时候没存心,写写押韵了,成唐诗了,我原来不会写诗,中间写写押韵了,什么“闪电暴露前朝事,雷鸣都是旧消息”,“游鱼无非前儿女,飞鸟尽是旧情人”…… 以前你的语言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直到《看上去很美》都不是。 以前从来没有。实际上,《看上去很美》的语言是失败的。那个时候我是从书面语来,书面语走得完全失败,那个东西写得太绕了,你看现在写的都是短句子,那时那个句子太长了,看起来很累。我今天要写,不会那么写,我那时候想事无巨细往里头搁,那太累了。关键是心里面没东西,所以要拼命堆砌细节,这回心里有东西,当然就挂一漏万地写了。 《千岁寒》的语言比较节省。 过去我心中无物,所以堆砌感受,过去我写景特别不自信,写景要堆砌很多东西,让人觉得绕了,是一滑头,现在我心里有数,要写的东西就在眼前,我只要把重要的东西写出来就完了。 以前没写景,都是对话。 我避实就虚呢。我见过什么呀,就在那瞎说,我就游山玩水转过几圈,其实我什么植物都不认识,我去植物园转过几次,记不住,就知道树草花,什么树﹖不知道。 这次怎么就写得出来呢? 这次我眼前有。写的时候是…… 觉悟了? 也不是,写的时候是,说句虚的吧,上帝握着我的手写的。说句实在的,我这也是吹牛掰了。我写的时候是有现场感的,看见了,画面迎面而来。 怎么会呢? 这就是……练的。这个没办法。我作了点弊,你们是公共媒体,我就不在这聊了。当然里面有方法,你让我自己现在写也能写,当然写不了这么好,凭着印象,照葫芦画瓢,也能写个差不多。这个我也没有写到百分之百,写到了百分之六七十,现在我能写到百分之三四十。就是个别段落突然有了,接着,因为我们汉语太习惯叙事,其实你不在现场,你人的差别心就上来了,你的价值观这种利害得失利害心就上来了。我可以这么讲,是在“定”中写的。和他们在饭桌上写的,在被窝里写的就不一样。站在自然立场和站在人文立场上写的不一样,站在民族立场站在国家立场上写的跟站在胡同口写的不一样…… 其实我真正状态好,也就1991年一年,还有去年。 物理和宗教是一回事 你说这次是在写“经”? 您觉得呢?《千岁寒》出来有些人说你未证菩提,我说,哥哥我不是佛教徒。我不认为就你们一家有觉悟啊。释法平等行吗。我假装是金刚了,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觉得就要提高觉悟,“鲜花村”开播以后我继续写,《金刚经》我现在还是用文学语言写的,其实还是语焉不详,因为中国这个文学语言非常不准确,它在能指上太宽了。我和史铁生聊,我聊所指,他聊能指,完全聊不了了。我准备拿中学物理来聊,能量守恒原则,质量守恒原则,所有机械都不省功,我觉得所谓功德就是这个功,还有阿基米德定律,那个上升的浮力和排出的重力是相等的,这个世界一切物质都是守恒的,但那是量子水平以上的,听得懂吗?听不懂我就不多聊了。拿中学物理那些弄完《金刚经》,你们可能不懂,但中学生刚上完,我跟一个小孩聊,他马上弄懂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佛教说这是出离物质观。 我们现在教的中学物理都太讲功能性、太微观了,物理和哲学其实是相通的。 是。我一个朋友做生意的,他是一个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是一个绝对的异端分子,他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史铁生说这世界是物质的,这是一废话,其实不是,这是一切的前提。那哥们就说,那精神现象是不是物质的?精神现象不全是物质的,回头一想,果然不对,除了物质还有能量存在呢。物质和能量的关系在相对论讲,能量等于质量乘速度的平方,能量和质量的转换关系是正转换,但是我这哥们说了,其实温度也决定能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我的意思是除了物质还有能量,因为我自己见过,人死了魂不散,能量守恒原则是什么呢,能量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消失,它只会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人死后,这个物质形式消除了,这能量在。所以,只有跟他亲的人或者跟他有仇的人能够感受到,因为能量没有消失嘛。打架的时候,你丫打死我,我能量不消失,它哪去了,一个翻转上你身上去了,拧不死你。打死那么多人,这些能量哪去了,都给胜利者背回来了,所以你不纪念亡灵是不行的。当然能量不见得受速度影响,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能量是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说的那个产生物质的速度,最大的粒子回旋加速器也达不到。 这就是普通的中学物理,只是我们的教育把它当工具理性了。我重新把中学物理看了一遍,俩礼拜就看完了,哪能学六年哪,我靠,那班笨老师。……能量,我这么讲生动多了,我们是物质造物,我们不可能摆脱这东西。他们把它工具化了,他接着说发电去了,太小了,又不当电工,聊这个干嘛,全变成特别实用的东西了。你比如说,任何机械都不省功,这完全是个人间道理,谁都占不到便宜,但是他就把它当成纯粹机械的啦,省了什么功啊,省了点人力,省了点额外功,有效功是不会省的。其实这是一个哲学,可是我们不当成哲学教。物理也是追求宇宙本质,它就和宗教干的事是一回事。 好战言论是要不得的 你怎么对慧能感兴趣? 惠能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说的有些话也不是实话,比如他说他父亲武德三年发配岭南,武德三年李世民家还在和王世充打仗呢,岭南地区是被汉阳太守隔断的,唐朝刚建国,还没有打进洛阳,他正用人之际。当时卢姓是北方大族,惠能怕人瞧不起,就假托是卢氏后人。当时允许吹牛逼。来历不清是正常的。 现在流行说汉唐,说那时是盛世。 于丹啊,我百分之八十喜欢,百分之二十不喜欢。我觉得于丹有个最大的问题,她犯了一个中国文人集体的坏毛病,就是把历史审美化。历史不是不能审美,可你拿古典诗词来聊历史,不带这么聊的。唐朝人民生活非常痛苦,老实说,在盛世,在汉唐都是这样。于丹你要是在唐朝你要守活寡,看过那时候的怨妇诗、边塞诗吗?李白那个“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汉乐府那个“七十从军行”,你要当一辈子兵,在外面打仗。在那里打仗,拿一棍,拿一木头枪就去了,搁今天谁去啊! 《千岁寒》里写到了唐朝打仗…… 李世民还是不错的,他们打仗的时候,当然也屠过赵县,李靖也讲啊,士兵都没有军饷啊,就是为了破城了以后,掳掠妇女和财帛,你不这样,士兵为什么来啊?李世民说,各位别这样,我拿我们家里的钱给你,饶了这一城百姓行吗?他当然是要买人心了,但是他确实有这一套。李世民特牛逼,我挺佩服,那时候中国当帝王真是亲冒矢石。李世民把一千人俘虏了,这一千人说我投降你们得了,李世民说你还千万别投降,你们太太和子女都在城里,你们投降我们把你们太太和子女都杀了,给吃完饭,回去吧你们。逮一间谍,一看说你怎么那么瘦啊,说我抄小路来的,李世民说了解我军情况你用得着抄小路吗,你来,我堂堂正正告诉你,放他回去,然后给新疆那帮人带话,你们来打我呀,谁都不敢。他有一个少数民族将军,打仗的时候被人拿槊把腰给捅伤了,李世民把这人逮着了,说将军你把他杀了,这将军也特别牛,说这哥们跟我没私仇,他是为他的主人打仗,我干嘛要杀他呢,放了。还剩两个城没有打下来,李世民说,牛逼,打得好,赐他一百匹布帛,那城主在城里面也拱手说,秦王你也牛逼,你也打得好。那时候人打仗,那叫军人,不滥杀无辜。 古代历史就是战争史,你看那农民起义,哪有兵器啊,拿着菜刀,那时候冶炼技术很落后,你要想打一把好钢刀你没有火,你没有煤,你没有焦炭,你那火力就不够,你连瓷都烧不成,烧出来是陶,你还别说淬一钢,那时候最好的钢是大马士革钢,就我那书里面写了。那农民几百万人就怎么叫两百人就冲了哪?那李世民打下唐朝只一千兵马,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各领一队,就是这一千人打仗不退,站在那里死扛。他们打窦建德的时候,他那马没吃饱,他不打。李世民经常亲自探阵,被射得跟刺猬似的回来,那箭都是树枝的,他里面穿了一件黄金甲,没有受过一次伤,他那马倒是经常射瘸了。等马吃饱了,他往前一冲,窦建德的部队只有第一排是大高个,骑在马上,后面全是老百姓,李世民把窦建德逮到了,说关你什么事啊,干犯我军兵锋。窦建德说你去逮我不是麻烦吗,我送上门来了。所以李世民得天下没打过什么硬仗,他那一千匹重装的马一冲,身上带护甲,老百姓就全散了。兵败如山倒,前兵踏后兵。 所以盛唐百姓还是很苦的。 隋炀帝的时候,全国有800万户,(经过战乱)到武则天的时候只有350万户。武则天是个女的,心眼小点,搞得还行,但是告密也是她那时候搞起来的,安史之乱的时候,又大概有800多万户,中国人过亿的时候,也就是康乾的时候,狂升不止啊。唐朝那150年全靠天吃饭。唐高宗的时候,库里拴钱的绳子都烂掉了,第二年就饥荒,他也没有存粮,国家不管这套,你们有粮就吃,没粮就活该,现在国家还存点粮,那时候谁管这个,赶上丰年还好,灾荒一起……唐朝是有几年好的,安史之乱搞成什么样,最后长安都给黄巢吃了,他进长安城老百姓都欢迎他,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我花开后百花杀”,第二年没有粮食,他把老百姓都抓来吃了。那唐朝人太拧巴了,头一年还太平盛世,第二年给人吃了。所以你讲话要一分为二,你不能好处全要了,我们那还经常聊赫赫武功,你聊什么呢,是你打仗吗?那战士多苦啊。所以我认为今天好多民族极端分子那些排外情绪是要不得的。 我就是一起哄的 书的序言叫《我是谁》,是不是对自己有一个身份质疑? 这个很正常。因为你有时候会怀疑,当然,其实,怎么说呢,碰到好多事,有时候会感到人生虚幻,我觉得一切特别无聊,我晃了十多年了,我觉得人生实现的那点东西,我太早实现了,没有意思,人生没有意义。一开始我并不怀疑自己,但是随着你怀疑人生跟着也怀疑自己。 写小说,搞电视剧,挣了钱,也不快乐吗? 没什么快乐,因为中国人有些我觉得很可笑,我先前是想和知识分子认同,后来发现反了,人家还不和我认同呢。你说我跟谁认同去,我跟痞子认同去?后来我认同这个了,问题是这还是一个社会身份,还不是我自己啊,我自己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知识分子该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痞子该是什么样,我觉得自己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我没觉得我比别人活得更加不道德,当然,我很不道德了,当然这是按照绝对标准说。但是我没犯法呀至少。我最多摧残一下自个呗,捎带地,伤害一下别人。但是,社会评价对我来说,我是不屑的,你说我好,说我坏,我觉得跟我都没关系,你说我好,我也不那么好,你说我坏,我也不那么坏,那我自己对自己又没有参照系来评价,当然我不是说我今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今天也没有解决这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觉得我就是一起哄的。 很多人期待你出来兴风作浪吧。 站在我的立场上,我没有什么出不出来的,只不过过去我玩得太忙,没空来料理这事。最后玩颓了,不是我要出来讲话的,是他们把我逼出来的,全是他们来找我呀,我也是闲着。这段时间写点东西,照我的原计划,没打算这时候出来,本来打算贴在“鲜花村”的网站上,现在全便宜你们了。等我开了“鲜花村”,我也是媒体了,到时你们要我聊,就要付我10万块钱,当然我不是自己要,我捐了。 刚开始有人说,时代变了,对我的宣传力产生了怀疑,我哪受得了这个,结果就被撺掇起来了,原来不打算出来混的,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本来也活得挺好,可是国际总公司先把那小孩给告了,那小孩又不在北京,我得去应诉去。赶上搜狐做娱乐节目,我哪知道啊,有人说现在都娱乐了,他们来一帮人在那瞎问,那我可不是问什么就答什么嘛,瞎问我瞎聊,站了一堆人在那问,感觉也挺新鲜的,说这么多年你哪去了,最后就聊炸了。 有没有觉得现在媒体与以前不同了?全体娱乐了。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就是觉得人民更庸俗一点。我就是从娱乐打起来的,边打边看,不会出事吧,我一看没出事,接着聊……越聊越热闹,当然后来我觉得聊得有点多,把我给聊恶心了。我不能天天跟你们聊,天天聊我又不是一主持人。我得写东西啊,老这么聊我没法写东西,我整天处在兴奋状态,最后弄得我嗓子都哑了,差点得一肺炎。 自己也控制不住了。 那你想啊,我是一“人来疯”啊,当然后来那些人也会逗我,当然也有好多社会丑恶现象,我觉得恶心他们两句也是我的社会责任,是吧。 我没病 你在《锵锵三人行》做节目时,说到吴征。后来杨澜回应说,你复出的动静太大了。 杨澜的事就别聊了,杨澜是我偶像,我是她的粉丝。你是骗子我也支持你,但是吴征不许是骗子。我还以为他们分手了呢。……我就说有的人,有了钱了,为什么就不收手呢?你看我有点钱就收手了。挣多少钱拣多少骂你至于吗,干嘛呢,岁数也不小了,你说我们穷人,咱不顾脸面地往上混,这是有道理的,你现在不有了吗?你不光有了房,汽车也有了,何必呢,处处授人以柄。 10年以前你是这样想的吗? 10年以前我已然这样想了。10年前我就基本上退了,1991年以后我就不怎么干这些事了。说实在的,写电视剧我没拿多少钱,我全是帮他们忙,也就是冯小刚还给我点钱,别人没给我钱,你说人家请你去聊聊,你怎么开口问人要钱?那时他们也都是没起来呢,也没钱,等起来了,有钱了,我也找不到这人了,也不会说挣完钱回头给我送一份的,很少,那我就留人情在了。所以我现在好办事,就是都还给我面子,因为都是别人得我好处,我可没得过别人好处,没占过别人的便宜,就落一个人缘好。我在北京真的是人缘好,谁也不能说我坑过人,我就没干过这事,我是帮过人确实帮过无数。 你骂过的人也不少。 我真是对事不对人,我恶毒攻击过谁啊,除了我说过余秋雨两句,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吗?李敖确实有点讨厌,你别冒充文人,你作为一个文化人你在某个领域里有点成就,你别在那里吹牛逼,包括我也不吹牛逼。凭什么我给你喊好啊,你冒充宗师就不可以。儒家,百分之一可以,百分之二都不可以。历史给过你们机会,君臣共治,北宋,明朝,全有,全都搞砸了吧,还能再给你机会吗? 你是不是对文学批评家有意见?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经过80年代的,80年代我这叫批评与自我批评,哪叫骂人。那时候批评厉害极了,我到上海来,李劼当着我的面,那叫批评,没有什么,我们后来也是好朋友。我不是人身攻击,你看我说金庸,说鲁迅,我是不是谈作品啊?我只不过用语讥讽,都谈不上刻薄。你们冲我骂街,我是不爱理你,我要是骂起来有你受的,这些人太讨厌了,这帮人,他们不许别人讲话。 他们是文绉绉的骂,你是比较有杀伤力。 我当然用词犀利了。你们人多势众,我当然犀利点了,我要不是犀利点,好好说,你们就更得意了。有人说我是痞子,说痞子写,痞子看,××,我们说胡同里那个叫痞子,当然让我严重地不高兴了……你管我叫痞子,痞子是有特定含义的,当然后来我认为相对于你们,我就是痞子,我认了,我认了这个。 其实那不算什么事儿。 是不算什么事,我那时候不是心眼小嘛,我心眼小,而且我有旧的优越感,我认为痞子是一种侮辱,当然我现在认为是一种赞美了,当时,我也是从年轻过来的呀,他们说我轻狂,我哪受得了。你说我纨绔子弟我都愿意听,你说是痞子,太挤兑人,那仇结大了,我什么时候想起来我什么时候得骂。现在我不骂了。 我演知识分子太累了,演痞子挺好,我就是文坛“钉子户”。 那你是不是有攻击性性格? 心理医生可说我没病啊,严重正常。央视12套,心理访谈嘛,我去了,李子勋老是说,我没病,当然播出来就不知道谁有病了。看来全社会准备关心我,准备给我治一下,结果我没病。说实话我是带我妈去治病,结果我妈这病没法治了,就算了。……我那么着急攻击人家,也不是很正常,还是有点病态。当然李子勋老师是正面肯定我,基本正常。方式有点粗暴,就是这个。这个可以改,没问题,所以这次来上海就是准备和大伙和解的。 女儿严重比我好 你现在跟你妈妈生活在一起? 我们没住一起,我妈是一个无比坚强的老太太。自己跟一帮八十多岁的人混得挺好,还有人追她呢。她跟我住干嘛,多闷啊,他们是一帮子老头老太,他们有一些比较庸俗的活动,跳舞什么的,人得跟同龄人在一块,所以你们干嘛呀,都在那里演孝顺…… 你女儿怎么样? 我女儿是一个严重比我好的人,她比我自信,她和我的命盘是一个镜像,就是我的黑灯是她的红灯。你明白赌钱那个吗,我在这儿下注,她要到一个相反的对面下。所以她今年考上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了,我理科不行。我是一个特逞强好胜的人,我的弱点是唯恐别人把我当傻逼,我一定要向聪明人证明我特别聪明。我女儿是装傻充愣,为什么你考试不考第一啊,她说,我怕人自卑啊,我干嘛刺激别人啊,太自信了这哥们。……给伯克利录取了,去伯克利不用搬家,就在旧金山。伯克利学费还便宜,公立大学的NO.1,又是嬉皮士的发源地。……所以我就彻底放心了,经济学毕业想挣钱太容易了。当然,我今天碰到一个上海人在联合国工作,我就建议她以后也去联合国工作。她要去一个单位什么也不干,就剩聊天,那就只能联合国了。而且联合国免税,同样挣10万,你不交税,开车被罚了可以不交,出去外交护照,比美国护照好使。那上海女的说,她在联合国当同声传译,她说联合国跟中国的单位特别像,也得拍上司马屁。我说我女儿在中国那学校里被管惯了,拍上司马屁也不算什么难事。你说你在那混那么多年,你就当一老好人,完了干不成事也不怪你,跟你聊天的全是国家元首,这不挺好吗? 你女儿也喜欢聊天吗? 她喜欢。但是她不跟我聊。我观察过她,她在幼儿园,睡午觉起来,叉一手在腰上,跟人家聊,回家去她装小孩。她肯定是以聊天为乐,但她不跟我聊,她跟社会大众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我惹事,说你跟他们瞎吵什么呀,碍得着你吗?我就爱管闲事,争夺话语权呀,你哪懂这个呀。 当主流太辛苦了 你那个大院的优越感现在还保持着吗? 我宁可把它化为一种自信,我不认为这有多牛逼,没必要,今天很可笑了,坚持这个。今天玩的是众生平等,你没看我在这演社会边缘人士吗?我可不演主流,但我很容易当主流。 你要是当主流不怕很辛苦? 当主流太辛苦了。我还是功利地看这事的,觉得当主流能落着好处,就是太累了,跟一帮××一天到晚混在一起,太多的应酬,应酬一旦开始,你就没法弄了。所以那时候我有点逗药,建议年轻人不要玩这个,因为有假药,加了冰毒,还有玻璃渣什么的。我特别喜欢你们上海一个自强委员会,他们把这个统称为药物滥用者,不叫吸毒者,吸毒你明显是歧视嘛,我没逗过白粉,你们叫抽大烟,我没用过那个,我就是用一点精神类药物,我用这个就是为了断绝我的社会关系。因为,那时候我多少饭局啊,我本来是一个瘦子,忒瘦的一个人,1993年天天出去吃饭,那时候一下子就变成160多斤,完全是一胖子,现在是150斤左右吧。后来我觉得太烦了,吃饭这个,说实话,你吃到300顿以上吧,就没劲了,有什么可吃的,就这点动物尸体,你还怎么吃啊。然后喝滥酒,喝得他妈的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喝得第二天恶心好几天。那你没法拒绝,很多人是好意啊,而且不是有人天天请你,问题是他好几年没见到你,请你一顿,每人一顿你就排不过来了。我就愣不去,愣爽约,为什么,就只能说这哥们吸毒了,所有的人都不来了。 那你不做主流的风险也太大了。 这没什么大的。人一听起来都有点害怕,那是因为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一开始碰所谓的(毒品)其实就是精神类药物,我都是在合法的药店买的,是因为你们精神偏见嘛,像王安忆以为我把身体搞坏了,那时候很多人传我身体不行了,我到南京朱苏进专门来看我,是来看我身体如何……当然没事了,苏童就知道这一点,就吃点麻黄素嘛,开玩笑嘛。我妈是医生,她那么保守都知道没事。 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体制内的生活? 你喜欢吗?昨天我们碰到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还说,中国没有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统统公务员化了,体制内,用我的话说是官僚化了,所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别聊了,你们统统是公务员而已。你们只不过是另一口的,教育部口的公务员,你们假装什么独立知识分子呢?我才是独立知识分子呢,当之无愧吧! 讲真话是最有效率的活法 这次复出,你曾几次谈到余华,是不是因为余华去年的书很畅销啊? 畅销榜这不是胡扯吗,他印了多少册,总不会比韩寒还多吧? 你这本书印了多少册? 我不知道。印得多我为他高兴,但印得多不代表他好。我的也有印得多的,我不觉得好。咱们都得拿绝对标准比,咱别拿咱们自己这不行的互相比,我觉得余华在这事上是明白人。 余华的《兄弟》你看过吗? 我现在不看小说。 写小说,不看小说是吗? 我现在也不是写小说,我是跨媒体写作,跨文体写作。我是觉得现在再特别强调哪种形式没意思,因为今天的生活比戏牛逼,比小说牛逼,牛掰。我在小说的写作中写写可能是诗,写写可能是散文,可能是纪实,可能是历史,我发现我就写真的,咱们上海的老先生巴金倡导过的,讲真话嘛,讲真话可怕吗?我不觉得可怕,谁还怕谁有脏心眼。我从今天起到处讲真话,爱吓唬谁吓唬谁。说真话怎么了?它能让你少块肉吗?不会,它顶多让你晚上睡觉不太踏实。……配着讲真话能随时道歉。 人家看到你觉得可怕,是因为你讲真话? 唉,我想说的是,说真话你付不出多大代价。很多人把自个吓着了,哎呀,讲真话不行啊,要付出代价的。阮玲玉同志就死了啊。我觉得讲真话得了好处。谁能怎么着我呀?你们一亿人骂我,怎么了?有本事你当面骂我呀,别背后骂我,我还骂你呢。所以讲真话付不出什么代价,而且讲真话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活法,在生活中和人接触,你愿意交一讲假话的朋友吗?坏人都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他一天到晚都讲假话,很累的,讲真话省事嘛,你不用去猜啊。有的人听惯了假话,你一说话他跟你说,你说的是真话吗,很多人认为你说话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我对这个社会一无所求,我挣点钱我全捐了,你看着。 难道你这次闹腾不是为了卖书?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目的来假装讲真话,所以我说要把钱捐了。我日子过好了,我不需要再靠这些钱维持生活了,我不是说捐钱把自己搞砸了去捐钱。我也不会对别人施加道德压力,咱们这点道德感还是有的。我不能逼着大家捐钱,大家日子都过不成了,那就招人恨了。 现在内心特别柔软 《千岁寒》要拍成电影吗? 目前还没有,以后有可能。叶京说这只能我拍了。张元我觉得他未必能拍,这东西文学性太强了,文学性太强了的东西未必能拍。《千岁寒》本来也是剧本,想写了到慧能的老家抓点钱去,弄点广东的善男信女的钱,现在我完全不想这事了,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不管谁干总要差不多吧,不能瞎弄一个吧,我写得这么好。 张元的《看上去很美》怎么样? 怎么说呢,后来我没看,他拍的线索太多了。他用的那意大利人来剪,剪得太政治化,应该是说商业意图太明显了,都被人家外国人看出来了,这就玩得不好了。当时我看了两遍,当时那意大利人怎么都剪不下去了,据说是给贝特鲁奇当过剪接的一个人,也快崩溃了。中国的事儿他不能理解,他怎么剪啊?我特别不同意他把一场戏剪开用,你不能把观众当傻子,我一看就知道,完全是同一场戏剪了用。包括《孔雀》也有这个问题,为了剪得节奏平均。一场戏用光都一样,明眼人一眼就知道这是一场戏剪开的,一看这活就是糙的。 姜文特牛逼,他这个新片子(指《太阳再次升起》)如果没有《罗生门》这样50年不遇的片子,应该能在戛纳拿奖,他的水准在那儿。姜文还是对得起他自个的,七年一部戏,化了5000万,那跟一年一部戏不一样,太不一样。它讲的是诗意的梦幻美,票房我不知道会好还是坏,也许会好,因为姜文宣传是很有力度的,很会来这套的,他也很下决心的。至少他的口碑是好的。 你这个《千岁寒》要拍的话,难了点吧,你通篇讲觉悟。 其实也不难拍,里面故事线索很多。 从广东到湖北这一路风景描写得太超现实了吧? 不超现实啊,姜文这个戏就是这样的戏,很美。不过现在从广东到湖北不是这个劲了,但是罗霄山脉应该没有什么变化的,人类没有那么广泛地把环境搞坏的,秦岭山脉就保持得很好,那里人还烧黄檀呢,森林人都没进去过。……张家界山里还是可以拍的,拍电影就跟军队似的,进去保障就全上去了,只要有钱就行,它都是原始状态的,你破坏一点,它又修复了,不是说你破坏了它不长了,你别在那搞什么不可降解的东西,别彻底地把人家河改了道了。 你那里面写到的水果林,哪找去啊? 很多小孩看了都觉得像卡通片。其实不行我就仿照宫崎骏拍一卡通,卡通又省事。宫崎骏的《龙猫》、《天使之城》我特别喜欢,一个小女孩从天上掉下来,掉在一个小男孩手上,太可爱了。他是一小女孩的观念,那种想象力怎么拍啊,拍不了。你看过《骇客帝国》的动画版吗?那个比电影好。那时候我迷过一阵动画,觉得特好看,美国动画那种三维,没必要,它太男性了。二维真是美极了,那个《听海涛声》就是一言情小说嘛,特别好看。以前我看《情书》特别感动,发现日本有这一路,过去有一段爱情,发生的时候不知道,特别可爱这东西。哎呀,我现在内心真的是特别柔软。 要拍电影还是讲北京土话吗? 我写的是广东话嘛。广东白话。其实这是我编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当然有那么一种传说,广东白话是唐话,客家话是北宋的,潮汕话是秦朝的——秦始皇一口潮州话。至少白话有很多宋朝的语言,你看话本小说就知道了。-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