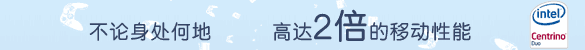|
|
|
|
沉沉浮浮香港地 历尽沧桑一学人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5日09:51 南方日报
国学大师饶宗颐回归十年前夕借“三舍”言心志 沉沉浮浮香港地 历尽沧桑一学人 慈、悲、喜、舍。 这四个字,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的招牌大字。 走入馆内,饶老私人特别珍藏的小玻璃柜内又见这四字,这回却是指尖大小的玲珑小字。 一大一小,皆居显赫处。 饶老感慨地说,这浓缩了我的人生体验,最高境界就落脚在这“舍”字上。 他扳出三个手指说,“舍”有三种境界:一是“财舍”,二是“法舍”,三是“无畏舍”。我是历尽沧桑一学人,60余年来,与港岛沉沉浮浮,直到今天。 □ 人物传奇 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1917年6月生于广东潮州大富之家,字固庵,号选堂。 饶宗颐笔耕七十年,著作约70余种,著述3000多万言,治学之领域,遍及10大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金石学、史学、目录学、词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诸多学科。仅其中《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即浩浩12卷,洋洋1000多万字;专著60多种,各种论文400余篇。先生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其中古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等被形容为异国“天书”,他也精通。 去年饶老九十寿辰,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学者以及香港九所高校首次联手行动,共同为这位大师所涉及的九大学术领域,召集海内外学者展开学术探讨和交流,盛况空前。 □ 饶老印象 大师“有趣” 白发白眉、颜容清癯的91岁国学大师,最爱用的词却是“有趣”。 在学术馆里参观,每走一步,每见一个作品,饶公都要给我们讲上一大段“古”。 说到“打坐”,他索性把双脚盘在大腿上,连皮鞋都没脱,看到我们一脸佩服和惊异,干脆直接笑着问:“我很有趣吧?” 我们发现,大凡采访饶老的人,都心有忐忑,因为饶老在敦煌学、甲骨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填补海外汉学界的扛鼎之作,他本人更被誉为“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且琴棋书画俱佳,被钱钟书称为“旷世奇才”。 但连串“有趣”却把我们的忐忑打消了。 “他涉猎广泛,研究深入,常身处高处难免寂寞。”港大教授们告诉我们,饶老要常用“有趣”化解学生对艰深课题的畏惧。 也许是怕我们看出他太“寂寞”了。饶公打趣说,“我是不是一个‘怪物’?!” □ 饶公四论 奇正 蜡烛 守株 旁移 听说我们是广东来的记者,饶老更厚爱三分。访谈中,饶老的精彩四论令记者拍案叫绝。 一是“奇正论”。他说,别人说他是奇人,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老子讲“正以治国,奇以用兵”,他则是“正以立身,奇以治学”。立身做人要正,但做学问要出奇制胜,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 二是“蜡烛论”。先生自14岁起,学“因是子静坐法”,几十年从不间断,每日早起静坐,然后散步,晚间9时必宽衣就寝。国内学者曾将他与清末两位大学者龚自珍、王国维并论。饶公说:与上述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80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三是“守株论。”别人一辈子在不停追逐机会,他笑说自己则比较“偷懒”,坐在树下做好准备、耐心待兔,一见到兔子就以最快的速度扑上去,这样一辈子总能抓到几只兔子的。这其实就是讲究治学“一以贯之”的重要性。他研究佛教,一直想学梵文,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碰到印度专家,就以甲骨文与他交换传授,学会了人称“天书”的梵文。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学会了中东的楔形文字。这些机缘看似偶然,背后是他的“一以贯之”。 四是“旁移论”。他说,别人总结我学问有八大门类、十大门类,看似涉猎繁杂,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其实每次我只是往旁边移了一小步。像一开始继承父志编撰《潮州艺文志》,是搞方志学,就得懂一点碑记,进而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接着机缘凑合就到了敦煌学,一步步都很紧凑,很扎实。 财舍 4个银庄和治学之间的选择 当时我家有银庄四个,还印钞票。李嘉诚的父亲也常来银号办业务。我是长子,既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两者挑一。我选择了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 广东人喜欢把饶宗颐与另一位潮州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李嘉诚富可敌国、饶宗颐学富五车,分别代表了当今香港人经济、文化领域的最高成就。 但不为外人知的是,90多年前,饶宗颐出生时的饶家就是潮州首富。 饶老说,潮州人喜欢管富家少爷叫“阿舍”,就是家里有很多房产。 “不过,我要修正这个财富观”。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一生,与香港的缘分不浅。 饶宗颐(以下简称“饶”):我今年91岁了,我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香港。 我16岁第一次来到香港,当时家里有生意在香港,我来视察。 1939年,我23岁的时候,中山大学聘请我当研究员,但当年日军南侵,中山大学迁赴云南,我绕道到香港。没想到,我当时生了一场大病,滞留在香港。战乱的洪波把我甩到这里,从此命运大转折。 记:所以,香港成就了您? 饶:我在港大教中文,一教就16年。在香港,我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每年都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开会,参加美、法等国的汉学研究机构工作,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能到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这是我的幸运。 记:大家说,您研究学问广泛。 饶:不能这样说。我主要是研究文史哲、艺术等几个方面,研究世界:伊拉克、波斯、希腊等古文化。 把根扎在香港,我既可以了解祖国内地考古新发现,又可以接触世界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化思潮,文化的血脉并没有割断。 更重要的是,站在这里,我学会了从世界的立场看中国、看香港、看我的家乡广东。 记:香港遍地是黄金,制造了无数财富神话。但您这位国学大师,却把巨大家财从手里慢慢散去了。 饶:(笑)当时我家非常富有。有银庄4个,还印钞票。李嘉诚的父亲也常来银号办业务,十分熟悉。 父亲去世时我仅16岁,是长子,既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两者挑一。我选择了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放弃了“管生意”。 记:不可惜? 饶:潮州人管富家少爷叫“阿舍”,就是家里有很多房产。但是我要修正对“财富”的定义。我认为,不仅财产是财富,文化也是财富,而且超越了地域,是世界共通的财富。 这一点“舍”,不仅是对香港说,也是对中国说的。 法舍 《文心雕龙》当教科书 我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就把古典的重要书籍带到了课堂。比如把《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作为教科书,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去上课。 这样做缩短了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能有条件扎进去。 今天,在港大的饶宗颐学术馆内藏书超过3万册,当中不乏遗世孤本,饶老的字画佳作、篆刻陶瓷更是琳琅满目,价值不菲。 这些均由饶公豁达捐出,无私地把毕生心血与港人分享。 港大学生每日来来往往。这个古色古香的国学天地,扎根于色彩斑斓的香港文化中,生机勃发。 在他的眼里,这就是“法舍”。 记:为什么把毕生心血捐出,这蕴含您对香港怎样的感情? 饶:我和香港有某种相似,都经受了沧桑沉浮。 我有一篇《宋王台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去参观宋王台时候写的。当时感慨万千,“台空名在”,物是人非,香港已沦受殖民统治。有感而发,奋笔疾书,文章一挥而就。 记:香港文化多元,在这里传播“国学”,有挑战吗? 饶:无论在哪里,国学的基础都是汉字。每个人首先要把“文字”学透。 现在的一些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但其实是误解。 还有一个就是要背诵。我小时候,没有怎么正式上学,就躲在家里的天啸楼中背了很多书,从中获益良多。不背书,就写不好文章。这是我80多年的学习经验。 记:您也这样教育香港学生? 饶:我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就把古典的重要书籍带到了课堂。比如把《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作为教科书,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去上课。 这样做缩短了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能有条件扎进去。所以,我所教的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里,就已经能做出研究性论文。 之前是没有人这样做的,这是我对港大一个贡献。 记:现在很多大学生不太重视基础,资料找得快,论文做不深。 饶:大学生们一到写论文的时候,就在电脑里找大量的资料。但由于基础不好,往往找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乱拉关系,结果错漏百出。 无畏舍 做学问要点无畏的精神 我对学问是“溯源不止,缘流而下”,对问题穷追不舍,逐一弄清,哪怕把生命都耗上都不惜。 “无畏舍”,在饶老身上折射的是对学术的坚韧。 先生家道中落,始终处之泰然,旁若无他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我的心不受羁绊,胸中并无挂凝,本是沧桑一学人”。 饶公说,当年革命,别人捐出金银财宝支持,反问孙中山“带了什么回来?” “孙大炮”说:“我带了‘大无畏’”。 “我也一样!”饶老说。 记:您第一个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第一个研究敦煌白画及写卷书法,第一个将殷礼与甲骨文联系研究,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这么多“第一”很吓人,怎么才能做到? 饶:治学、修为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 我对学问是“溯源不止,缘流而下”,对问题穷追不舍,逐一弄清,哪怕把生命都耗上都不惜。做学问还真需要这点无畏的精神。 记:有人评价香港是“文化沙漠”,您怎么看? 饶:“沙漠”这个词不公道,香港始终是商业社会,对文化的兴趣较淡。 香港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尽沧桑,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景象。 记:但又有人说,香港有了您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饶:不能夸大某个的作用。早在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许地山、叶恭绰先生在学术上对我影响就很大,当时商务印书馆就在北角,我在那儿编了辞典。 至今,商务印书馆仍是香港学术、文化的重镇。 记:十年来,您也为香港文化发展做了那么多事情,有什么最满意? 饶:在大屿山,我写了“心经简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佛经群,38根8至10米的古朴原木上,是我书写的260个尺大佛教《心经》原文。 记:这已经成了为港人开启智慧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了。 饶:香港回归前夕,我还为回归专门创作了一幅一丈六尺的国画《百福是荷》,121朵的荷花,占满香港大学展览馆椭圆形大厅整整一面墙壁,表达我对香港回归的祝福。 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记:十年了,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饶:看到香港基本保持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我很开心。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香港成为“不慕物欲、甘于孤独、潜心学术”治学者的宝地。我更加要争取自我精神,排除外来干扰。减少交际、应酬,留下时间,多些潜心做学问。 专题撰文:本报特派记者 胡键 谢苗枫 陈枫 图: 率性饶老盘腿打坐接受记者采访。胡键 摄 2000年,董建华为饶宗颐颁发大紫荆勋章。 饶宗颐在展览庆典中给曾荫权赠送画册。 饶老为本报题“报导翔实”四字。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