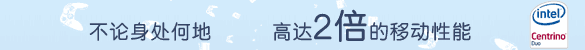|
|
|
|
饶宗颐:中山大学影响我一生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9日02:29 金羊网-新快报
推荐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倡导,国学热渐成燎原之势,各类学者筑坛,经典心得出书,甚至三岁小儿也着儒装,俨然一副旧式子弟模样,正襟危坐读起了《三字经》、《弟子规》。 在这喧嚣背后,有一位白发白眉、清矍智慧的耄耋长者,他少年早慧,以清净无为、专志于学,心无旁骛而思维活跃的气质,以数十年如一日求“阙”穷追,甘以有限探无涯的治学精神,尽享文气“熏蒸”,深入书海翻波寻知,在文、史、哲、艺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他著作等身,他荣衔无数。他开潮学之先气,立足于香港,游学于世界,以深厚的学养和独绝的治学方法,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焕发生机。 我们不得不沉静下来,认真思索这位“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劝学中的一句话: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谁能设想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一个曾家财万贯的富家公子会甘心钻进一个世人认为无趣的胡同里,毕其一生之功苦寻生命的皈依,独守对中国文化的血浓于水的痴情。 家学很重要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没有家学,就没有您今天这样渊博的学问? 饶宗颐(以下简称“饶”):是的,我15岁以前已经培养了这个基础,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 我的学术发展是因为我有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家学。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第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 记:您本人是不是私塾教育的成功例子? 饶:其实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代数和英文对我以后治学都很有好处,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要做到像王国维那一代人那样的学贯中西,旧学底子很重要,现代学校教育也不可缺少。 学问在于积微之功 记:您从5岁开始接触学问,到现在80多年,这过程中会觉得枯燥吗? 饶: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我觉得搞学问是一种乐趣。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 敢于否定自己 记:要说您学术之“奇“,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在许多陌生的领域开荒播种,例如率先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等;治楚帛书之第一人;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之第一人……据说您身上这样的“第一”有百项之多! 饶:现在是一个制作模型的社会,但我制作了自己的模型,我不想跟着别人走过的路走下去。 记:好些人说您是奇才,写的东西多,出手快。迄今为止您已发表专著六十多部,内容字数以千万计! 饶:其实我写文章也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长期的积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前几年发表的《郭子奇年谱》,那是我20岁时写的,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好像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这种修正跟前边所说的谨慎发表文章并不矛盾,因为有些领域是没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勇气首先去探讨,不足了再改正,再补订。 要去功利心 记:您的一生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经商,为什么终生痴迷学问矢志不改呢? 饶:佛教讲求一个“定”字,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和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记:如今这个年代或许不太适合搞学术研究,商业化的侵袭,功利心态对人的诱惑太大了。您的字在拍卖行一字敌万金,画值数十万、上百万,可您一直深居简出,淡泊名利,非常难得。 饶:商业对文化的确是一个挑战。现在书画家很少知道“墨谑”的情趣,他们扳着面孔作画,只看着钱,书画家要回归到“艺术本源”上去。 与世界汉学结缘 记:我们认真研究了先生的学术年表,又去作了一些对比,感觉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不像国内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受过政治运动的干扰,可以一心做学问。所以想请先生谈一谈看法,就是学术环境对于一个学人的重要性。 饶: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上世纪50年代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每年都被派到外国去开会,与欧洲结缘,法国人也授予我儒莲汉学奖;后来我又去印度,在整个国家旅行,学了点印度的东西,明白印度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东南亚也差不多跑遍;后来我又在新加坡大学教书;有机会去了美国……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我都参加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每一个地方与那里的汉学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做学问的方法,这是我的幸运。 中国隐文化最好 记:您认为国际上的汉学研究,哪个国家水平比较高? 饶:这个我不批评,我不得罪任何国家。我有一个基本条件,看你能不能写中文。我们在英国,用中文写的汉学论文,他不发表,要求用英文。为什么要求我们的汉学一定要用英文写?这不公道嘛,没有道理嘛。 记:您觉得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饶:我觉得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 与中大的渊源 记:能说说您同顾颉刚先生,同中山大学的交情吗? 饶:顾颉刚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早的知己,到今天我还感谢顾先生。顾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好处是提拔人才。我也是他提拔的,那时我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中大在石牌,而这个机构在文德路。我在那里看书,修志,撰写稿子。 记:当年您好像只有十几岁。饶:我18岁。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感激中山大学。我年轻时邹海滨(邹鲁,前中山大学校长)请我。那时地方志研究方面,北京是第一位的,它是首都所在;中山大学是第二位的。 记:这么说中大是您起步做学问的地方? 饶:这个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所以我很感谢中山大学,感谢那些方志。顾先生是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他也不知道我是多大年龄,其实当时我十几岁。这时我同顾先生都还没有见过面。 著书盼回归 记:现在国家经济条件好起来后,很多地方在修典。 饶:这个我知道,我在里面做顾问。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摆在里头。一个经,一个藏,要整理。我们国家现在提出和谐的观念,这个很好,这些工作都要慢慢做,不要太急。 记:您是如何保持自己自由、独立的精神世界,又是如何去开阔自己的思维及眼界,以便跟上时代的发展、社会进步? 饶:争取自我精神,排除外来干扰。减少交际、应酬,留下时间,多些潜心做学问。 我一直期盼着香港能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一篇文章《宋王台赋》能体现我当年的心情。 记(笑问):香港还会出现像您这样的国学大师吗? 饶:肯定会的,肯定会的!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