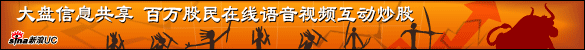|
|
|
|
|
专家谈重庆土地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滞后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8日04:38 新京报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中方专家组长  王小映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前述课题组成员 - 访谈动机 近日,刚刚被确定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出台政策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办合作社和公司。与此同时,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清理整顿“小产权房”事件。两种现象都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无疑,探索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是各方共识。这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怎样让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本报就此展开访谈。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严重滞后 背景:本月初,重庆市工商局发布通知,允许农民以土地直接入股创立合作社或办公司。该市还鼓励农民自愿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换取城市社保。与此几乎同时,在北京发生了广受关注的郊区小产权房事件,已成气候的小产权房禁而不止。 新京报:一个是地方政府主动实施“土地新政”,一个是郊区农民和城市开发商的自发交易导致小产权房乱象,两者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关联或相似动力? 刘守英:两种看似性质很不同的现象,反映了同一个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问题:土地市场化走什么路径。是继续沿用征地制度,国家取得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推向市场,还是让农民以土地要素参与城市化,分享增值收益。两地的事实说明,后一种路径的现实要求已很迫切。 王小映:土地制度改革的长期状况是城市改城市,农村改农村。前者以企业用地为中心,已有较完备市场体系;后者则主要是确立农民对农用地更稳定的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滞后。这样出现了城乡割裂,在利益诱导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各种形式隐形流转。 新京报:小产权房一个关键情节在于,城市开发商直接与农村集体或农民进行交易,农地避开了国家征用环节转为城市建设用地。重庆的新政,虽然提出土地用途不变,其实质是否也是农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供开发? 王小映:随着人口迁徙和劳动力转移,农村建设用地有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城市建设用地控制趋严,成本高。一些企业和居民把目光投向集体建设用地,两者合拍之下出现了诸多乱象。过去一些地方的土地股份合作制,通过合法规避国家征地,在农地转用审批后或者干脆不经过审批,将一部分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后直接供应市场。这种制度安排保证农民分享了土地增值收益,但是,也对耕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带来了一些冲击。 新京报:成渝的土地新政有没有越出现行的法律框架? 刘守英:在广东等沿海地带,农地通过出租或转让进入市场的先例已经存在。农民以集体土地参与工业化和获取收益,是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繁荣的秘密。相比之下,重庆的改革处在一个土地管理制度更严格、用地矛盾更突出的背景下。所谓土地入股新政,还没有越出现行的法律框架,《土地承包法》第42条有允许农民入股的规定。土地换社保也没有触及建设用地的核心问题。需要有更实质的制度创新。 王小映: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可以土地入股;为扶持乡镇企业,《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可以联营、入股举办企业。现实中,一些地方利用这些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集中集体土地,统一划定农业区、工业园区和商品房开发区,在取得农地转用审批后或在直接违法转用后,将部分土地以出租、转让等方式供应给市场。 土地入股只是一个过渡性制度安排 背景:《土地承包法》确认了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又为其加上了限制。如何在维护农民对土地的自主权益的同时,又防范农民失地?在转让、出租、抵押或入股的多种流转形式之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实践。 新京报:允许农地直接进入市场,一个前提是农民对于承包地除生产经营权之外,还拥有更完备、稳定的权利。而现在这种权利还受到各种限制。 刘守英:用地制度改革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如何实现价值,这包括资产处置、转让和收益分配。《土地承包法》确认了农民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权利,但更多是在集体单元内部。重庆采用“土地入股”提法即是受制于这一现状。如果农民拥有更完备的流转权利,他们就会有更多方式的选择,比如出租。 王小映:在农民对土地的物权中,现行土地承包法中有一个关键不足,就是承包期30年的限制。为什么不是更长,或者永远呢?这个期限还赶不上开发商取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年限。30年的承包期限,给土地流转带来很大不确定因素。重庆土地入股也规定是在剩余的承包期内,那承包期过了又如何? 新京报:在充分实现农民物权的前提下,农地进入市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更合理的,既能让农民分享增值又能避免失地风险?后一个问题受到普遍关心。 王小映: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方式如出租、入股、转让或抵押,入股跟出让比,避免了一次性收益或失地的问题,可能获得长期的稳定收益;跟土地出租比,企业的用地契约更为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土地入股对企业来说,用地的稳定性比不上出让,对农民来说收益的稳定性却比不上出租,一旦企业效益不好或者破产,农民能否分红和能否拿回土地都是问题,因为土地的物权已经变为对企业的债权。 刘守英:农民入股经营企业,虽然可能有稳定收益,但也有多种风险,除企业本身的风险外,农民不清楚企业财务状况,难以维护股东权益。单纯就入股和出租的比较说,农民可能会更倾向于出租土地。 新京报:从入股到出租,是否仍会有走到对外来者出让使用权的趋势?农地入股本身,只是一个过渡性尝试? 王小映:从广东等地的经验看,出租给企业的土地已经走到了转让的地步,通过补缴土地出让金进入市场。重庆的土地承包权入股和股份合作制,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在大城市近郊区尝试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具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可能还要面临第二次改革。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存量相当大 背景:限制农地转用一个最主要的考虑是耕地保护。为此,重庆土地新政有不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集约经营的承诺。但是经验证明,集约农业的收益并非一如预期。 新京报:重庆此次的土地新政中,设定的方向之一是发展集约农业。在我国目前农业规模小,生产力面临瓶颈的背景下,通过土地流转使农地集中,扩大生产规模,是否是提高农业效益的有效方式? 王小映:小规模的适度经营,相比于大规模农业并非就没有效益。农业生产受制于收益边际效应,比如不可能对一片土地施用无限量的化肥和使用无限量的拖拉机。集约农业的效益主要来自劳动力节约,只有在劳动力发生大量转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一般农区,没有农地转用发展二三产业的支持,单纯依靠集约农业,土地股份合作制很难自行维持。 新京报:那么用地制度的改革是否会冲击耕地保护? 刘守英:内地一些面临本轮工业化的地区多是粮食主产区,怎样以土地支持工业化又保证粮食安全,我们的主张是对一些重要块状工业带地区,建设用地指标适度放宽,给地方政府一定的依法行政的空间。实际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存量是相当大的,土地整理的空间也很大,给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很大空间。 王小映:这些存量用地既有乡镇企业以前获批的土地,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公用设施用地,也有合村撤乡并镇过程中出现的闲置土地,还有村庄总人口减少留下的宅基地。用好这些土地,一要通过改革集体建设用地制度,使其流转起来;二要靠整理,从已有的经验看,通过土地整理可以拿出相当比例的建设用地推向市场。改革可以首先着眼于解决这些存量的问题,然后应对增量的要求。 政府应退出赢利性用地的征用 背景:有论者认为,要打破目前的用地困局,必须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同地同权同价。而无疑,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至关重要。 新京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呼声,一直很高,你认为眼下应从什么方面入手? 刘守英:眼下应该着手解决两件事情:一是允许农村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眼下工业用地是由政府征用之后协议出让给企业,政府并无利益反而付出征地成本。企业低价获取土地后,可能浪费土地甚至囤积土地。因此对于工业用地可不再采取征用,而让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使农民通过土地租金等方式获取收益。这个占到土地市场的30%以上。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农民宅基地商品化,对于小产权房与其一棍子打死,不如研究政策使其与城市房地产市场接轨,可以设想存在两个价格有落差但产权也有区别的市场,比如小产权房可自住不可出卖,让市民自由选择。 新京报: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它的构成形态如何?能实现城乡自由交易吗? 王小映:应该由政府提供一个有形的交易市场,实现税制统一、交易费用统一,建立完备的产权登记制度和提供其他保证交易安全的服务。这个市场可以实现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建设用地和房地产交易,但要符合国家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 刘守英:一套完备的土地财产税制度以及各种配套改革,是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前提,现在只能逐步扩大农地市场化的范围。最终来讲,要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场交易,同地同权同价,农民通过土地增值参与城市化获取收益,政府通过土地财产税制获取增值用于公共利益。 新京报: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角色会发生什么变化?它通过什么行为来维护用地秩序? 刘守英:政府征用的范围必须大为缩小,保留公益性建设用地通过征用来取得,赢利性用地则退出征用。同时,政府必须通过规划管制和用途管制规范土地市场。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