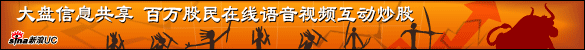|
|
|
|
分洪区百姓承受洪水之重:春种可能看不到秋收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4日00:08 红网(来源:财经时报)
他们在承受洪水之重 本报实习记者 胡佳恒 春种可能看不到秋收,本有投资欲望的外地商人也不敢前来——分洪区这样的硬伤使得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始终悬空。而在洪水肆意的时候,分洪与否的不确定性也使分洪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时刻处于不稳定的焦虑当中 涡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它从安徽蚌埠市怀远县的一个村落前流过。 这个背倚大堤、紧邻河水的小村现在只剩下何京一家。 由于几乎年年涨水,村里的其他人从去年起就陆续搬到了堤内的移民小区,凭着政府补助一点,自己支出一点,住进了商品房的村民们告别了农耕生活,以外出打工或做小本买卖作为营生手段。但何京一家仍然靠着河边的草滩放牛养鸡,这是村里最后的住户。 “我们已经习惯了涨水。”何京说。四天前外出回家时,她趟过了十公分深的浑水,但仅过了两天,水就涨到了一米多。现在,何京忙着把家里值钱的物件搬到二楼,每天出门买东西,她都划着自家的小木船。 “其实我们也想搬,但住进了商品房,我们养不成牛了,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在何的眼里,今年河里的水涨得还不算快。但她家的两层楼已颇让人担忧——因为几乎每年都有半个月浸泡在洪水中,墙壁红砖裸露,上面的石灰也已经开始剥落。 何家的生计靠河滩来维持,但河水的暴涨又时不时带来麻烦。不过何京最近还是决定年底搬进移民小区,至于搬过去后做什么他们还没有计划。无论怎样,当何家的两层小楼倒掉以后,这个河边小村将最终消失。 淮河分洪 淮河岸边越来越多的房屋已经在最近几天的洪水当中消失。七十二小时淹没数十万亩的汹涌洪水,让淮河抗洪形势变得愈发紧迫。 继7月10日安徽淮河干流王家坝开闸泄洪之后,安徽省上六坊堤、下六坊堤、南润段、邱家湖、姜唐湖五大行洪区又在一天之内接连启用。7月12日晚7点,安徽淮南市的石姚湾行洪区也开始扒堤行洪。至此,淮河防总下令开启的9处行洪设施中安徽就占了7处。 “现在天气已经不正常了。”安徽阜阳市的刘力说,上周末他粒米未进,因为从周六凌晨开始,阜阳下了20多个小时的雨,出门就是没过小腿的积水。雨停之后又是暴晒,他说气温恐怕有37度。而来自当地气象部门的消息称,周末还会有暴雨来临。 离阜阳县城30公里的王家坝在经过了两天的开闸蓄洪后也于7月12日关闸,它在静待更大洪峰的造访。“安徽不应该再分洪了,别人嘲笑安徽人穷,但他们从不说安徽为分洪作了多大的牺牲。”刘力调侃道。 也有市民不同意刘力的观点。“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自己会不会被淹,还顾不上关心分洪区的农民。”出身农村的阜阳市民王力强说。王直言他曾经泡过水,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安徽省颍上县赛涧乡清真村村民刘守黄五天前上堤参加防汛巡逻,现已日夜坚守了一个星期。“如果不开闸,我们一定能保住大堤。”但刘守黄说这句话时,他所在的姜唐湖行洪区已经开始行洪。 荆江煎熬 现在,同样经受分洪煎熬的还有荆江分洪区,尽管这个921平方公里的分洪区现已半个世纪没有趟过洪水。6月的一次长江流域强降雨,让沙市水位在6月8日到22日之间日最高涨幅达到2.33米,但就在5月,沙市航道水位还处于历史同期罕见的负值。 80多岁的沈美安经历过第一次荆江分洪。1954年的夏天,当长江对岸传来两声枪响,警告将要开闸放水时,沈正在家里整理行李准备逃难。他后来随着人潮走上了汽渡码头,远远的看见汹涌的江水从太平口闸流进,向对岸的南婺州奔去。“当时水离堤面只有一尺多了。”在人潮涌动的汽渡码头一侧,静静端坐着一尊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铸造的镇江铁牛,此时它的身子已被江水淹掉大半,上有铭文“翳千秋万世兮,福我下民。” 44年之后,在1998年8月6日晚接到准备分洪的通知时,家住公安县(在荆江分洪区内)埠河镇的李海青刚刚初中毕业。当晚他和三个兄妹坐在小货车的车厢里被转移,汽车在堤上举步维艰,“满眼望去黑压压的都是人,还有人赶着猪,很多猪都半路上热死了。”这段7公里的转移之路从晚上十点一直走到凌晨四点。而这一夜,公安县孟溪决口,地点就在荆江分洪区边上。也正是这一次鲜为人知的决口,加之此前有计划的扒堤行洪,荆江大堤顶过了历史最高水位,埋在分洪闸口的炸药终于没有引燃,荆江分洪区免遭洪水的侵蚀。 尽管当时并未被水淹,公安县仍然损失惨重,正处于成熟期的棉花因无人治虫造成大面积绝收。此后的几年其经济也一蹶不振: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97年就达到了2175元,1998年的洪水使人均纯收入骤降至1580元。大灾之后水旱灾情交替出现,1999年长江特大洪水、2000年和2001年特大干旱、2002年持续低温阴雨、2003年外洪内涝,使公安县农业经济在与频发的自然灾害抗争中艰难前行。 公安县这种“看天种地”的无奈与淮河流域“水灾年闹水灾,旱灾年闹旱灾”的处境有些相似。而现在,随着洪水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分洪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煎熬。最重要的是,这些分洪区都背负着相同的硬伤——春种可能看不到秋收,分洪区的招牌也足够吓跑本有投资欲望的外地商人。 迷失的分洪区 但毫无疑问,建立分洪区在经济账上是经得起盘算的。 湖北荆江分蓄洪区工程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果对湖北省1500公里的长江干堤加高1米,不仅需要国家投入资金60多亿元,而且还要挖压农田1.3万方。而加高1米的堤防,在洪水期只能增加荆江行洪量4000—5000立方米每秒,况且堤防不宜加得太高。 根据水利部上报国务院《关于加强长江近期防洪建设若干意见的报告》显示,如果单纯靠加高堤防来防御百年一遇的洪水,测算总投资达2400亿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洪水水位越高,险情越多的防洪风险。 相较而言,荆江分洪区则实惠许多:完成建设任务只需投入29亿元,进洪量为7700立方米每秒,紧急情况下能达到17000立方米每秒。 但“分洪区”三个字的阴影还是笼罩在当地居民心中,分洪与否的不确定性也使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始终悬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分洪区时刻处于不稳定的焦虑当中,加之分洪区几乎都为农村地域,这就使这一特殊区域的自救产生了一种套路:快速城市化,以及减少农业人口。因为在设置分洪地点时,秉持的依然是效率优先,然后才是兼顾公平,而城市与农村的效率却一目了然。一些分洪区正在扶植的“打工经济”即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实际上就是在用效率追赶公平,以期缩短城乡差距。 在荆江分洪区与对面的城市之间,四年前就架起了一座长江大桥,不过四年来这座大桥并不是很忙碌。分洪区内的农民,清早贩一担蔬菜或葡萄坐班车走大桥到城里,晚上卖完再折返。虽然每天都进城,但他们都知道自己还不是城里人:因为在洪水凶猛时,他们还要放弃自己的家园。(来源:财经时报)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