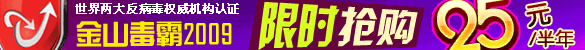|
|
2003:孙志刚案开启的公民权利道路
2003年,孙志刚的受难给了“收容遣送制度”以最后的一击。
从2003年开始,以孙志刚案为标志,媒体、法律学者和公众发起了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古往今来维护权利的行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人们把2003年称为新起点,这是因为孙志刚之死成为震撼国家的标志性事件,而且经由这一事件,一个以捍卫公民权利为特点的法律职业群体开始崛起。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公民的维权行动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人类政治文明进程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受难者
2007年11月7日,我到海淀区六郎庄调研打工子弟受教育问题,回来路上搭乘的黑车司机是一个安徽来的做服装生意的中年人,他说,这几年他们的生存环境好多了,至少不用经常提心吊胆查暂住证了。我问他,记得孙志刚吗?他说,怎么会不记得呢?那个被打死的大学生,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收容遣送了。
孙志刚,27岁。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03年2月,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
孙志刚死了,因为他刚来广州,还没办理暂住证。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后来他被送到收容遣送站的救治站,在那里被殴打致死。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记者陈峰写的一篇题为《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详细讲述了孙志刚之死的经过以及他的家人告状无门的遭遇。这篇报道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孙志刚的死震撼了整个国家。
孙志刚受难的背后是一个广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收容遣送就已经开始了。1958年初,户口管理条例出台,城乡分割制度正式确立。1961年11月11日,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负责将那些没有开介绍信的流入城市的人口收容起来遣送回原籍。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正式开始,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维护户籍制度。1982年,中国出台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1985年,开始实施暂住证制度。1991年,国务院发出通知,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
回首二十世纪,从五十年代初清理城市的运动到1958年户籍制度确立,从三年大饥荒到六十年代的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通知,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到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从1991年扩大收容遣送对象到孙志刚悲惨地死去,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执著地反城市化,同时把这种计划经济实验所带来的后果几乎全都压在了农民身上。
也许,在各个地方的收容遣送站里,很多人成了默默的牺牲者,而孙志刚生命的代价是有结果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公民权利高涨的年代。
法律人的行动
2003年4月25日,我从北大的“一塌糊涂BBS”上知道了孙志刚的不幸。一个青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被打死了,而他的亲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奔走于各个“有关部门”之间,备尝哀痛与艰辛。本来,要不是非典,我原计划“五一”期间到北京南郊一个村做两个星期的调研,主要是了解暂住证和收容遣送状况——我对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关注很久了。可是,又一个极端的悲剧发生了,我长久地呆坐在电脑前,心里非常难过。
我的朋友俞江和滕彪也看到了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很多网友也在北大的 “一塌糊涂”BBS的三角地和公民生活版上连续讨论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呼吁严惩凶手,也有的学者提出了收容遣送制度违宪等问题。我们商量,除了呼吁之外还能做什么。5月初的一个早上,远在武汉的俞江突然打电话来,提醒我《立法法》第九十条规定公民有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法律法规建议的权利,这里规定的公民的建议不是传统的公民给国家机关提意见,而是带有一定程序的建议:公民的建议经初步审查,“必要时”可以进入正式的法律审查程序,这就相当于公民也可以就某个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诉讼”。我和滕彪都非常赞同这个想法。我们仔细研究了《立法法》之后,决定利用这一权利以普通公民身份提出建议。我们想,这或许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改变以及启动宪法审查程序能有所帮助。很快,我写了初稿。通过电子邮件用十天时间反复商讨,终于完成了1000字的《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我们关注的问题已超越了孙志刚个人的不幸。我们相信,孙志刚案既然已经有了这样广泛的影响,个案的正义应该可以实现。我们想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个违宪的制度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我们期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启动审查程序,修改或废止这一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政法规。同时,我们还期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通过对该行政法规的审查,建立一套完善的审查程序,逐个审查违背宪法和法律却至今仍然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促进我国法制统一。
考虑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提出的只是一个纯粹程序性的建议,丝毫没有谈及孙志刚案,其基本内容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作为行政法规,其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宪法和相关法律相抵触,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议。
考虑到行为的专业性,我们以公民的名义提起。不是作为旁观者的呼吁,而是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的主体,就像一份诉状中的原告一样。我们列上了我们的身份证号码——这是最有效的公民的标志。
建议书没有影响力就可能很难有结果,这时,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如果没有一家媒体关注此事,该怎么办?幸运的是舆论始终在关注,《中国青年报》很快作出了反应。虽然俞江和滕彪倾向于安静的学术生活,不想被打扰,但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毕竟,有了传媒关注,即使没有法律上的结果,也会有社会意义。
5月11日,我们开始考虑递交的问题,这时新华社公布了孙志刚案件刑事审判的结果,打人凶手以及渎职官员都受到法律制裁。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立即递交了,如果再延迟一段时间,这个案件也许就永远成为过去。5月14日那天北京下起了大雨,我冒雨在西直门附近转了很长时间居然没找到一家打字的地方。后来只好把建议书发给滕彪,让他从昌平发过去。下午,滕彪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去传真,电话确认对方已经收到,然后到邮局又寄了一份。
公民建议提出以后,媒体广泛报道。但我们丝毫没有放松,一方面准备建立网站专门论证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另一方面对救助站制度深入调研,准备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理性和建设性,这是我们一贯的做事风格。我们当时准备用两年时间击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