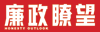寻找民意的底线
寻找民意的底线
——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
民意事件的实质是什么
《廉政瞭望》:2000年到2009年是民意蓬勃发展的十年,您觉得已发生的这些民意事件有什么共性?
于建嵘:我觉得,从类型和性质方面分析,因维权引发的事件占80%以上。就事件的特征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网络化和官民冲突。
首先,这些事件都具备了网络时代的某些特征。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传受一体化、快捷性等传播特性,使事件的信息来源多样、传递迅速。某一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传播,能够迅速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进而引起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现实中的民意行动,最终形成较大的民意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上海钓鱼事件等都是网上和网下互动,在社会现实中不仅有众多的参与者,众多的网民则在网络上参与评论甚至声援。
其二,这些事件均与官民冲突有关。无论是由拆迁、征地引起的维权行为,还是由环保问题引起的集体行动等等,都与公权机关的行为有关。大部分的民意事件,实质上还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
《廉政瞭望》:也就是说,网上的民意事件是一种表现形式?
于建嵘:对。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不但漠视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且自恃垄断的政治社会资源与民争利,成了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公司型”政府。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工农等弱势群体由于掌握的资源很少且缺乏表达的机制,经常容易受到权力和资本拥有者的侵害,这是造成官民矛盾的制度性根源。再加上一些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无视民众的利益诉求,使得官民的冲突加剧。这才是这些民意事件频发的直接诱因。当前的公权力代表组织和机构的权限过大,缺乏一种制衡其被滥用的力量是深层次原因。
民意事件的未来发展
《廉政瞭望》:您觉得今后的民意事件会越来越多吗?
于建嵘:我觉得,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稳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但民意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事件。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发生社会动荡。
《廉政瞭望》:政府越来越开明和包容,可能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另一个因素?
于建嵘:是的,这十年来政府的进步也很大。但如果仅以“刚性稳定”为目标,即以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或掺杂官员个人的目的,对各种民意的表达都要进行压制或打击,那么我认为这种稳定状况是有政治风险的。比如之前发生的“因言获罪”千里追捕的王帅案、更早以前的彭水诗案,等等。
改写规则与重建信任
《廉政瞭望》:您刚说民意事件的实质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如何缓解这种冲突?
于建嵘:我觉得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着手: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以及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学家裴宜理教授提出,中国民众的抗争活动与西方社会运动最根本的一点区别就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一般的情况下,民众会将对现行不合理规则的不满隐藏在心里,不会显化为具体的抗争口号或行动,我称之为“抽象愤怒”。比如对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的不满,对官员贪污腐化的不满,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一般都会隐藏起来,或者只在私下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留言、歌谣等形式传播。这种表面遵循规则,内心却愤怒的状态更为可怕,因为这些愤怒就像无法准确预测的地震一样,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如果愤怒在短期内得到了转移或者发生了多次较小规模的“余震”,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愤怒长期积聚,而且又不能得到有效的疏导和化解就会带来令我们无法预料的大爆发。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一些本来可以通过现行法律规则解决的刑事或民事纠纷出人意料地演变成有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危害比较严重的社会泄愤或社会骚乱事件。比如典型的瓮安事件。起因很小,事态的发展却来了次大爆发。因此,缓解官民矛盾,平复民众心中隐藏的“抽象愤怒”,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
《廉政瞭望》:怎样改写规则?
于建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规则的改写应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博弈过程,一方面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另一方面民众权利的觉醒和力量的壮大也需要时间。“砸碎旧体制不易,重建新体制更难”的基本共识已经初步达成。因此,通过渐进的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寻找改写规则的突破口成了现实的理性选择。
我刚说的第二个办法是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
信任不仅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普遍信任的缺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瓦解。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这些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消解民众对公正理念和制度规则的信任,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重要问题。因此,在我看来,社会不公平的普遍蔓延和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滥用是造成目前社会信任缺失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官员的怨恨和不满情绪就是这种社会信任缺失的重要表现。
一些官员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化,这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民众对公共权力的社会信任感急剧下降。比如罗彩霞、邓玉娇等事件,对公权力信任感的缺失会引起民众的共鸣,这是最终形成民意事件的重要诱因。
由此可见,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应该首先考虑如何完善社会规范从而减少社会不公和约束公权力滥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重建社会信任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改善社会不公、约束公权力滥用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廉政瞭望》:除了规范官员和公权力,民众这方面应当做怎样的努力?
于建嵘:公民参与网络是重建社会信任的另一个方面。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下,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等尚处于刚刚起步的不完备阶段,因此,培养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积极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充分发育公民社会应该成为重建社会信任的重要方式。
《廉政瞭望》:您上面说的改写规则和重建社会信任这两个办法比较宏观,有没有具体的建议来实现?
于建嵘:无论是改写规则还是重建社会信任,都需要选择合适的突破口。我建议以启动县级人民代表专职化的综合县级政治改革为契机,使县级政权有足够的地方社会和经济管理权限,同时使县级政权及其主官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通过建立既对中央负责又对地方民众负责的县级政府,并容许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可以这样说,如果现在执政者还不能从改写不合理、不公平社会规则的高度来审视民意的表达,来反省官民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所谓的“意识形态式”的旧思维和旧方法来解决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