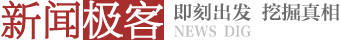开篇语
 韩国MERS患者金某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负压ICU接受隔离治疗
韩国MERS患者金某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负压ICU接受隔离治疗苏灿(化名)想起诉她老公的公司和韩国同事。
这位常年生活在深圳的年轻女士认为,是他们让她和老公被迫卷入中国大陆第一例MERS风波。
这是一种被拿来和SARS(非典)比较的病毒。12年前的春季,后者曾在中国大陆爆发,确诊病例5327人,致死348人。
6月8日,是MERS登陆中国大陆的第14天,正好是这个病毒的最长潜伏期。
韩国人金鹏国(音),中国第一例确诊的MERS患者,躺在广东惠州中心医院的负压病房里,他不知道自己何时可以离开。
MERS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缩写。
中国公众对它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金鹏国。这位44岁的韩国人,当父亲和妹妹在韩国已确诊MERS后,发着烧坐上飞机抵达香港,转乘大巴至深圳口岸,入境惠州。
发着烧的密切接触者
 共有43名医护人员轮流护理金某
共有43名医护人员轮流护理金某“接到去惠州出差的通知,那一秒,心里‘咯噔’一下。”
6月1日,北京飞往惠州的航班上,一名到此间谈生意的旅客安慰自己:“应该没事吧,不会那么巧让我赶上。”
飞机降落后不久,原本艳阳高照的惠州,忽然下起了雷阵雨。
巧合的是,6天前,惠州也下了一场雷阵雨,还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5月26日12时50分,金鹏国乘飞机抵达香港,下午3点乘坐机场大巴从深圳沙头角口岸入境抵达惠州。
从这时起,苏灿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与MERS发生了联系。
金鹏国是她丈夫李先生的上司。当日,李先生从深圳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惠州,和金鹏国汇合。
他们都是一家韩国公司的员工,这家公司是LG的供货商,次日要参加LG的技术交流会。
“26日晚上,他们在酒店住同一个房间,一起吃过几顿饭。27日开完会,换到另一个酒店。晚上我老公就回来了。”苏灿说,要说“密切接触者”,没有人比她老公“更密切”。
5月27日晚10时,世界卫生组织发布“MERS密切接触者入境中国”的消息。
4个小时后,金鹏国被转送至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这一夜,李先生一直在阳台打电话。
“见面时,他一直发烧,我老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我老公还去给他买了感冒药。”苏灿在电话中告诉《新闻极客》。
苏灿回忆说:“后来电话一直没人接,我老公就给酒店打电话,请酒店去房间看一下金先生的情况。”半个小时后,酒店回电话,金先生被卫生部门带走了。
随即,李先生被隔离。
戴四层手套的护士
 护士穿上防护服需要10分钟
护士穿上防护服需要10分钟金鹏国被隔离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重症ICU病房。
这不是一间普通的ICU病房。
病房里的气压低于病房外,外面的空气可以流入病房,里面的空气无法流出。病房内被污染的空气经由专门通道,进行处理后,再排放出去。
“打开门(空气)都出不去。”该医院一位接近管理层的员工冯明(化名)说,这叫负压病房。
这种病房,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抢救非典病人时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条件。非典和禽流感后,中国发达地区的一些大医院纷纷建有负压病房。
惠州市中心医院的负压病房,去年才投入使用。
护士卓斯第一次给金鹏国抽血。
卓斯是90后,去年7月刚毕业。
“她戴了四层手套,一般抽血都是戴一层。头上还戴了一个护罩,只有眼睛部位是透明的玻璃,其他全部都是封闭的。她一呼吸,里面就会有蒸汽。外面是空调,里面是热气,呼吸越快,蒸汽越多。抽完血以后,玻璃全模糊了,看不清,都不知道从哪里出去。”
该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负压病房护士的危险很大,要寸步不离地照顾患者,经常会接触到患者的唾液、分泌物等物,“卓斯当时心里很紧张,都想哭。”
传染科护理经验丰富的李春梅同样“害怕”。她是第一班护理MERS病人的护士。
她回忆说,走过缓冲间,站在隔离门前的一刹那,“头皮一阵发麻。”
从这天开始,她再没回过家。家里有她5岁半的女儿。
“这毕竟是全国首例。”冯明说,非典会不会重来,谁都说不准。
被隔离的韩国病人
 深夜医护人员还在开会
深夜医护人员还在开会韩国的MERS还在扩散。
截止当地时间6月8日,韩国MERS确诊病例总数已达87人,隔离2361人,已有6人死亡。
在异乡的ICU里,金鹏国躺了12天。
6月5日官方通报中,他“病情仍重,情绪波动明显,专家组已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金鹏国“情绪波动”不是第一次出现。
根据公开报道,金鹏国1971年出生,他的父亲是韩国第三例MERS病例,妹妹是第四例。他曾于5月23至24日在医院陪护父亲,属MERS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来中国出差时,他已感到不适,且发烧。
这使他遭到声讨。除了中国网友的不愤,也有韩国网友称其做法是“耻辱”。钟南山也曾公开告诉媒体,“他是不应该离开韩国的。”
他的妻子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为丈夫辩解,说他平时工作特别忙,不得不出差。
在隔离病房中的金鹏国,可以通过网络看到这些消息。
他接受了韩国媒体的电话采访。
他对韩国记者说,吃不惯中餐,已经饿了几天了。
网络碎片拼凑出一个韩国MERS患者的形象:40多岁、暴躁、自私。
但,这至少不是卓斯眼中的形象。
“他情绪不平稳时,我会做一些相对亲密的接触,摸摸他的额头,给他加油。”卓斯面对《新闻极客》,用韩语说了一遍“加油”。
卓斯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正睁着眼躺在床上。双目无神、表情有点抑郁又有点愤怒,两眼直直地盯着卓斯。
“亲故(音,韩语‘朋友’的意思)”,卓斯叫了一声,用蹩脚的韩语接着说:“我们做朋友吧,我叫卓斯。”
病人的表情有了一些变化,愣了几秒钟,回应了一句:“我叫金鹏国(音)。”
卓斯说,这个韩国人“很讲礼貌。”“有时发了脾气会道歉,吃退烧药出了很多汗,我们帮他更换床单,他会谢谢我们。”
依靠翻译软件,金鹏国知道了自己的病情距离死亡有多远。“我在屏幕上写了一个:不要担忧,一起战胜困难。”卓斯说。
后来,医院安排了韩语翻译,“还请了一个做韩餐的师傅,每顿都吃韩餐,韩国泡饭、泡菜这些。他吃不惯中餐怎么办?不好好吃饭没有抵抗力,也影响治疗。”
被恐惧包围的接触者
 重症ICU门外
重症ICU门外在金鹏国的隔壁,隔离着一位密切接触者。
苏灿认识这个人,“他是酒店的,和我先生也是工作认识的。他被隔离后,我们还通过电话,他有时候要给那个韩国人当翻译。他也很无奈。”
“有媒体说我老公是他的翻译,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同事!”哪怕是最小的细节,苏灿也抓住不放,希望能够再准确一些。
她受够了。
“很生气,懊恼!现在我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苏灿和丈夫李先生是朝鲜族。
李先生回到深圳后,在家住了一晚。5月28日一早,原计划两人一起搬家至另一个小区。
次日白天,李先生被带走隔离。
“当时我丈夫没有任何不适,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病的迹象,几次检测都为阴性。”苏灿说,她自己没有被要求隔离,而是“医学观察”,每天向社区健康中心汇报两次体温。
“我特意问过自己的危险性,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即使我老公被传染上了,我是在他还没有发病时跟他接触的,没有关系的。”
对苏灿来说,最恐惧的不是MERS,而是周围人对她的恐惧。
就算是在病毒潜伏期即将平稳度过的时候,人们对她的恐惧也远胜于病毒。
从5月28日起,她只出过两次门。
官方通报中,详细发布了深圳密切接触者的行踪,包括他们搬家的小区和时间,“周围的人马上知道是我。”
“我去了一趟公司。同事看见我,嘴上说你怎么来了?眼神里都是‘你不应该来。’”
“我出门去买菜,小区里的人看见我都躲得远远的。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罪犯,以为我是从隔离区逃跑出来的。”
“我真的没有被隔离!”苏灿说。
最新的官方通报称,MERS的隔离时间是14天,部分人的隔离最后期限是本月8日,最晚的是11日。
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何剑峰告诉媒体,风险确实已降到最低,但没有绝对,“和患者打个了照面的人,严格来说不是密切接触,但万一中招了呢?”
苏灿难以忍受周围人恐惧的眼神。
“我准备请律师,起诉我老公的同事和公司,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新闻极客 刘洋 报道)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标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或个人不得全部和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