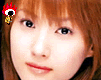| 乾隆年间已是东方大埠--讲述上海曾经的繁华(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11/02 10:14 东方网-文汇报 | |||||||||||||
|
作者:李天纲 ●乾隆年间的上海十六铺,已经是中国和东亚的最大码头。也就是说,在上海向西方国家开埠前,这里已经是东方大埠。 ●徐家汇陆续建造了教堂、修道院、藏书楼、博物馆、天文台、大中小学……到处弥漫着欧洲文化的氛围。这在中国和亚洲还找不到第二处……  静安寺路上建立的跑马厅 十六铺:开埠前的大埠 西方人说,是他们把上海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一个大都市。这话不是事实。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乾隆年间的上海十六铺,已经是中国和东亚的最大码头。也就是说,十六铺在上海向西方国家开埠前,已经是东方大埠。 中国传统的城市,沿街设铺。旧上海县把城厢内外的街市商业地带规划为“念七铺”,一共27个市铺。看同治《上海县志》,清朝初年东城最繁华的姚家弄一带为“头铺”。向东隔壁,靠大东门里一带是“十五铺”。出东门,至黄浦,北起小东门大街,南到董家渡大街就是“十六铺”。十六铺的面积范围比头铺大出十几倍,可见划定之时,城外十六铺地旷人稀,商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三百年前,这里称“城厢外”,在城墙的外面,是上海的东郊。清初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沿海运输和贸易的中心。四方来货,那时所谓的“洋货”是来自东西南北四洋,非特指“西洋货”。 “以港兴市”,十六铺的码头和街市联为一体。据《嘉庆上海县志》上海县城街道图:东门外,沿黄浦,有“会馆码头”、“竹行码头”、“大码头”、“新码头”、“王家码头”、“董家渡码头”,从城北一直沿到城南。码头的西面,至城墙下,按行业分出了一条条细小的专业街市。大东门外南北向有“内篾竹街”、“外篾竹街”,曾经是竹木器专业街;“豆市街”专做米豆杂粮等北货;“花衣街”做棉布、棉花生意。此外还有“洋行街”做的是广货、南货生意。“咸瓜街”后来发展成桐油、药材等南北货生意。明清以前,上海城墙里的街道,是江南县级城市的传统工商业格局。当十六铺兴起以后,全国和东亚地区的货流经这里中转,城墙东门外面出现的商业区域承担了全国的商品大流通。冲出“围城”的上海商业,在十六铺地区形成繁华,这里听得到广东、福建、宁波、山东各地方言,甚至外国语。 当大量的宁波人、南京人、福建人、广东人,以及松江府各县的商人进入上海之后,十六铺的社会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尤其是开埠之后,各地区的商人各执一业之外,还有各色人等的百样营生。潮州人买卖鸦片,福建人引进花会赌博,苏州、扬州人搬来妓院。公开的烟、赌、娼之外,还有地下的清、洪帮会,帮会内部还有各个地区、行业的码头、山头。这里成了上海最复杂的地区。如果说“十里洋场”是外国人的“冒险家乐园”,十六铺就是中国人的“创业者天堂”。上海帮会中最显赫的人物杜月笙,就是在十六铺船上船下卖水果出身。 十六铺的各地商人有不同职业。山东人做杂粮、生茧;徽州人做竹、茶、墨、纸;江西人做瓷、布、药;无锡人做铁工、棉织、丝织;绍兴人做酒,开钱庄;杭州人做绸缎;宁波人做煤、钱、鱼、药等;福建人做米、糖、木、漆器和烟土:广东人做烟土、杂货,也做买办,等等。 帮会控制的是地下黑社会,而同乡、同业会馆则是维持社会一般秩序的权威。 徐家汇:上海的“拉丁区” 通黄浦江的肇家浜,通吴淞江的法华泾,在漕河泾附近交汇。漕河泾经过上海县的七宝镇、青浦县的朱家角镇,从淀山湖港叉进入京杭大运河。三条河道在此交汇,地势非常重要。交汇点原来无名,因为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别业,徐氏有家人在这里边种地,边看顾徐光启的坟墓,所以人称这里是“徐家汇”。 从鸦片战争后徐家汇地区开辟教堂开始,一百年里,此处陆续建造成一整套宗教文化设施。教堂、修道院、藏书楼、博物馆、天文台、大中小学,一应俱全。它们作为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总部,弥漫着欧洲文化的氛围。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和亚洲都没有第二处。 当徐家汇开始建设的时候,它还不是上海城市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和江湾、真如、川沙的农民一样,都把去上海市区说成是“到上海去”。直到20年后,才因为和“太平军”打仗的关系,从上海租界里开了两条“徐家汇路”(当时称“军路”,即后来的“华山路”和“徐家汇路”),把徐家汇和上海市区连接了起来。 上海原来农业发达,开埠后工商业、房地产急剧发展,天主教上海教区因为占据了成片的土地,靠租金成了远东和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裕的教区。上海天主教“老教友”有几百年的奉献传统。史料记载,建造徐家汇大教堂的时候,大户人家出资买材料,贫寒教徒就到工地上帮助磨砖。在徐家汇周围中国本地的田宅中,天主教建筑密布,兀自成为一座独立的城市。 同样是宗教建筑群,徐家汇的肃穆与龙华的悠久辉煌有着异样的气氛;同样是西方文化,徐家汇的宁静致远又与租界的车马喧嚣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徐家汇直属法国巴黎耶稣会领导,来这里传教的大多是法国神父。徐家汇周围,很多学生在学习法国的音乐、舞蹈、绘画、体操,很多人以讲法语为高雅,神父们还都懂拉丁文。这种情景使徐家汇很像是上海的“拉丁区”,如同巴黎塞纳河右岸的教会文化中心“拉丁区”一样。 徐家汇的居民结构是两个极端,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交通大学的教授,以及各个学校的学生,是当地的知识分子一端,他们占人口的少数;另一端则是许多江苏、浙江、安徽、山东逃难来上海的贫苦农民,低技能、低收入者在这里为数不少。在1950年的徐家汇区总人口中,有24376人处于“失业、无业和家务劳动”状态,失业率高达25%以上(当时棚户集中的普陀区是23%,杨树浦区是22%)。可见徐家汇也曾经是上海一个低收入的贫民生活区。 江湾:“大上海”的梦想 宝山民间流传这样的话:“金罗店,银南翔,铜大场,铁江湾。”开埠以后,江湾因为在宝山县的最南端,离租界最近,面对19世纪末上海租界的北上势头,首当其冲,很快被时代潮流带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江湾镇,弯弯的吴淞江在这里蜿蜒而过,因而得名。1872年,中国最早的铁路——淞沪铁路第一期工程的终点站设在这里,江湾镇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在中外报纸上频繁出现,遂为世人所知。那时候,黄浦江吃水浅,吴淞口有内外沙堵住江面,千吨以上的大轮船难以进入外滩。有些广东商人把鸦片和其他走私货物从吴淞驳下后,运到江湾储藏,伺机进入租界销售,江湾成了走私者的摆渡站。同时,也有租界的商人到江湾来养奶牛、种蔬菜、开仓库。就这样,连通虹口和吴淞的江湾镇,在上海附近的村镇中较早地发达起来。 有一个中国商人,看见上海人参加泥城桥头的跑马场的赛马会,举市若狂,西人大赚其钱。当时租界华人只能买票参赌,不能与西侨同等使用马场里面的运动场地。他不甘心让中国同胞的钱博洋人的彩,肥洋人的马,决定自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跑马总会,便在江湾镇附近建造了一个专门让华人赛马的跑马场,于是江湾在那一代好赌马的上海人中间家喻户晓。这个中国商人,就是上海滩早期宁波籍巨商叶澄衷。他可说是江湾开发功臣中的第一人。 然而,上海北部的开发屡屡受挫,江湾的繁荣也随之几兴几废。第一次挫折是在1880年左右。淞沪铁路开通后,江湾应该借此交通枢纽的地位迅速发展起来,然而,铁路在中央和地方的保守势力中引起非议,一定要加以拆除。拆除后,江湾万众瞩目的地位,一下子消失了。第二次的挫折是在20世纪初年。眼看江湾在19世纪末将接着虹口、闸北的北上势头繁荣起来,忽因为成立了“浚浦局”,黄浦江航道被欧洲各国来的挖泥船打通,租界失去了“北上吴淞口”的冲动。 三十年过后,江湾遇到了更好的机会。1927年,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想要抓住上海这条中国的命脉,开发江湾,建设“大上海”,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二首都”(经济首都)。“大上海”的“市中心区域”并不在江湾旧镇的中心,它的中心设在江湾区的东部,靠近黄浦江的7000亩规划区内,后来称此为“江湾五角场”。 选择江湾,还因为这里“北邻吴淞,南接租界,东近黄浦,交通便利”;在农田中新建楼舍,没有大量的旧城市棚户区的改造负担。上海充满游资,市政开发的资金相当充裕,不需中央拨款。经过贷款,发行公债,土地、住房出售,“大上海”筹集到不少资金,在20世纪30年代初,江湾五角场的庞大市政体系已初具轮廓。 江湾五角场的规划,是由美国规划专家和中国设计师一起制订的,比较科学和先进。如“五角场”,是五条马路形成的放射广场,它用三条马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和翔殷西路(今邯郸路)分别接通杨浦、虹口和闸北;用两条马路:翔殷路、淞沪路通向“大上海”腹地。在五条放射主道之间,各有横向的马路加以联结,如同蜘蛛网一样,结成密度平均的中心道路网络。它不像——般的城市道路垂直平行分布,成“棋盘状”。广场联结的“蛛网状”社区,其好处是马路的分割比较细致,更多的房子可以临街,容易销售。 无法预料和不可抗拒的事件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于1932年爆发。淞宝一带至虹口、闸北,沦为战场,从吴淞的工厂、学校、码头,到闸北的工厂、车站、戏园、图书馆等,市北几乎所有的新式事业都受到日军战火的严重破坏。建设中的“大上海”被殃及,江湾繁荣又一次受挫。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政府继续建设“大上海”。几大市政项目,如“上海市政府新厦”、“江湾体育场”、“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都在这一时期落成。正当《中央日报》大肆吹嘘一个新的世界级大都市将在五角场兴起的时候,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爆发,市北又成了主战场。 总是从吴淞口进入上海的日本人,一贯偏爱住在虹口、闸北、杨浦、江湾地区。八年中,他们一直企图把这一块日占区改造成“小东京”、“东洋乐园”。他们修复了“大上海”的南部地区五角场附近的旧建筑,还号召本土的民众来“大上海”享受洋场繁华。计划中要迁移56万日本人到江湾五角场。一时间,五角场到处是小灯笼、小酒铺,路上是脚着木屐、身穿和服的妇人。然而日本人根本没有建设“大上海”的雄心,他们只想霸占、掠夺。江湾的蓬勃青春,正是断送在日本军人的蹂躏之下。 摘自《人文上海》,李天纲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编辑:燕于)
|
|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