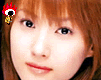| 历史解密:郭沫若的《武则天》是吹捧江青吗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11/03 11:31 中华读书报 | ||||||||||||||
|
《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2期连载了黄伟经先生整理的《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读后颇受教益。年届八旬的黄老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作家之一。他不仅散文写得好,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不过,在这长篇“录音访谈”中,黄老谈到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我觉得有失偏颇,现斗胆提出,以求赐教。 黄老说:“我看,无论在学术上、文学创作上,郭老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把郭沫若的《武则天》说成是“吹捧江青”的剧作,总要有事实根据,否则是无法使人信服的。 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初稿系五幕剧,完成于1960年1月10日,发表于同年5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后几经修改,于1962年6月20日定稿,改为四幕剧,于同年10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为什么要写历史剧《武则天》?他的创作动机是不是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的目的性,即“借颂扬武则天在吹捧江青”呢? 根据可查的史料,我们知道,郭沫若萌生创作《武则天》的念头,始于1959年6、7月间。1959年6月29日至7月11日,郭沫若离京赴安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太原等地考察访问,因在洛阳参观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有所感触而引发了创作激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去年(1959年)我曾到龙门去游览,我之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我怎样写<武则天>?》)。 郭沫若在游览龙门时,曾作过《访奉先寺石窟》一诗,其中云:“万躯残佛憎顽盗,一寺灵光号奉先。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这说明,作者游览之日就开始酝酿做翻案文章了。 在完成五幕历史剧《武则天》初稿以后,“为了更多地接触武后的业绩”以修改剧本,郭沫若于1960年3月下旬,特意在陕西乾县游览唐高宗与武后合葬墓的乾陵遗迹,并作七律五首以纪其事,其中《游乾陵》第一首云:“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这再次说明郭沫若是一心要为武则天做翻案文章的。 为了写《武则天》,郭沫若翻读了古史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还看了宋之的写于1937年的五幕历史剧《武则天》,以及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发表于1960年5月《上海戏剧》杂志)。他认为这两个剧本“都把武后写成为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我怎样写<武则天>?》)。他不满意于这些剧本,想把武则天写成一个“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并“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的女性统治者。郭沫若在盛赞武则天的业绩时,突出肯定了她的“民本思想”。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一千多年来,对于她毁誉不一,迄无定论。武则天这个案翻得翻不得,郭沫若翻得对不对、好不好,是属史学界争鸣的范围,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一,郭沫若于1959年6、7月间酝酿史剧创作时,是不是有可能预见到或觉察到江青想当中国当代女皇的野心,并自觉地去迎合、吹捧?二,根据当时中国的形势,有哪些社会的、政治的迹象表明江青已经露出了想当女皇的野心?三,在1960年5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武则天》初稿时,是不是中国广大读者“谁都看得出来”这是郭沫若在“吹捧江青”,还“捧得很肉麻”?这“谁”们那时果真的已经对江青看透了并且憎恶她了吗?四,郭沫若的史剧创作,是否都是为了灌溉现实的蟠桃,即是否都要同现实政治挂上钩,有无例外?如对他的四幕历史剧《孔雀胆》,该作何解? 倘若对上述问题不能作出肯定性的回答,那么,所谓“吹捧江青”,就不免有主观臆断之嫌了。 实际上,作为一位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主观诗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和史剧创作,都有着一种在时间上相对集中的爆发期的特点。就以史剧创作而论,大致是三个时期:20年代初期,创作《卓文君》、《王昭君》、《聂》“三个叛逆的女性”;40年代初期,即抗日战争的重庆时期,创作《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创作《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电影文学剧本)。据我们所知,郭沫若在看完话剧《蔡文姬》彩排和写完《五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后不久,就紧张地投入创作《武则天》的准备工作;而在《武则天》定稿后的1962年11月,他又匆匆地南下福建,酝酿写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了。这种现象, 说明《武则天》与江青并无瓜葛,倒是反映了郭沫若艺术创作特异的规律。 不错,郭沫若发表过一首吹捧江青的诗。他在诗中称颂“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载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不过,与1959年6、7月间《武则天》之“受胎”,相距已有八年之久。我们看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 郭沫若已经作古了,无法为自己辩诬。因此,我们活着的人,说话行文,特别是关涉到政治性质的评论时,应取负责的、审慎的态度,力求客观些、准确些;否则,诬枉故人,是很不应该的。(黄侯兴)
(责编:幽山) |
|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