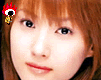作者:张芙鸣
关于陈寅恪,在我面前有两本书:一是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下简
称《二十年》),一是蒋天枢先生撰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以下简称《事辑》)。学界普遍以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陈寅恪热”是从《二十年》开始的。一位当代文学教授读过《二十年》后,心潮跌宕,说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一部字字有来历的严谨翔实的评传,读来让人心情沉重,不能不思索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又说:“这一类知识分子只能在社会生活中作‘宾语’, 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口号对这类知识分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不给他们以‘尊重’和‘爱护’,他们就一筹莫展、寸步难行。”〔1〕像这位教授一样,许多人是通过《二十年》来认识和了解陈寅恪并从中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沉重命运的。如果作者的目的是凭着一个文人的良知和同情心,激起世人了解陈寅恪的热情,强调其命运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力,那么,那位教授澎湃的心声和本书高达八万零五百册的印数已经肯定了作者的努力,并给了他一个惊喜作为报答。与陆著“洛阳纸贵”的热闹场景相比,陈门后学蒋天枢先生的《事辑》倒显得门前冷落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陈寅恪热”中极少被提到,这是个令人遗憾的现象。它一方面说明人物传记与年谱在当今文化氛围中的不同境遇,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像陈寅恪这样独具神韵的大学者,选择什么方式叙述其一生才能恰当地揭示其在历史中的位置,准确地找到其立足之“点”?
中国的传记作者善于通过气势磅礴的“论世”来“知人”。但每个人在历史流程中的坐标是不同的,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都能与伟大的历史事件联在一起。陈寅恪在其自撰年谱《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中有曰:“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若后人得以览阅年谱全貌,想必能从中读到一部家史重于国史的撰述。对陈寅恪来说,他首先是以旧学深厚的家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博学卓识,和治史之专之精令学界钦仰赞叹,然后才是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时事遭际时令人敬佩。换言之,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首先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界的贡献,然后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陈寅恪的生命自始至终与学术相融,其“不谈政治”以及生死力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韧力,都是实现学术价值的保证。这不同于胡适、梁启超等人,虽同为旷世学人,后两者是既“问学”又“问政”。写胡适,绕不开新文化运动,尽管他极不情愿将他的文学革命与这场政治运动相提并论,但也不得不承认,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政治化倡导和“五四”这一政治事件,使其学术思想得以深入民间。胡适每居一地,不仅喜闻当地政治社会新闻,更善于投身参与,研究利害是非;同样,写梁启超,也绕不开“复辟帝制”、“二十一条”、“巴黎和会”这些政治事件,没有它们,也就无法显示梁公审时度势、机敏善变的应对本领。 而这位“至死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的人物,晚年的学者生涯,其实是中年的政治生涯的直接继续〔2〕。胡、梁两位学者的一生,都对政治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其著书立说,不仅是学术史上的财富,也同时是政治史上无法省略的一笔。而陈寅恪是无法容忍学术具有这种斡旋本领的。学术于他,纯粹得近乎一种法律,几近冷漠,不识人之常情。这使我想起不平凡的“9·11”事件。事件爆发后,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停课,以示对死难者的哀悼。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却说:哥大是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天也不能停课。这种“惟学术”的精神,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它像政治上的某种主义最终必然诉诸实践一样,也会体现在授业、治学的细枝末节。一个不甘被环境所染、不屈从时世的人,环境和时世本身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任凭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正如冼玉清所说:“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3〕这种临风独立的精神也是对陈寅恪实质性的概括。因此,为这样一位学者立传时,过多渲染动荡时世,以及不惜笔墨于历史事件,似乎游离于传主的核心价值。在《二十年》中,作者虽然对陈氏授课、研学、著述有较为全面的描述,但与更多的枝节蔓延和厚重的背景资料相比,前者时隐时现,不能给人强烈的印象,也无法凸显“一老树枯涩、独立于天地间”的精神气质。另外,笔者以为,以“传奇”来概括陈氏一生似有不妥。从1890年到1969年,中国历史发生过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有过质的变化,这一切并没影响到陈寅恪的思想和行动。“持短笔、照孤灯”仍是其生命的全部内容。正是在这种缺乏传奇色彩、枯燥又单调的日常生活中,陈寅恪显示了神奇的人格魅力。同时与这个时代多数文人学者的命运相比,他又是幸运的。生活上,他享受到省级以上的待遇〔4〕,并一直有政界要人暗中给予理解和保护,所以,在罹难岁月,在失明的恶劣条件下,仍有著述依稀问世。而更多的人却去蹲牛棚、坐大狱,几乎丧失了生存的最低保障。体将不存,毛将焉附?这种集体性的知识丧失,想来不更令人含泪滴血吗!因此,以陈寅恪作为概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是否得当,笔者以为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 [2] [3] [下一页]
(编辑:独孤)
点击查看文化昨日超强人气排行榜,更多精彩尽在新浪文化!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