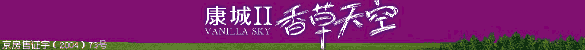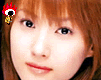与《二十年》相比,蒋天枢先生的《事辑》略去了国史背景,仅以时间为序,集中陈
述了陈寅恪的家史和治学经历。尽管他在本著《题识》中有云:“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云。”但其著述形式、内容及编排材料的方式,都说明此著可作为上乘年谱来阅读。胡适曾指出,年谱“不但要记载他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5〕。陈寅恪的学问是其精要,也是他最想留给后人的遗产,比某种精神的发扬光大更具体也更具紧迫性。陈于晚年曾对黄萱倾吐衷心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以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6〕黄萱过于谦逊,未敢应允,这的确令学界遗憾。而蒋先生的《事辑》不仅圆了同门学子之梦,也令后人在丰富的原始材料中领略到大师治学的原貌。本著有正文三卷及先生论著编年目录,附录有先生讲稿两篇、小传一部及师生们往事杂录。《事辑》记录家事变迁必有诗为证,记研学则有文为录。文则一来自寅师上课讲稿,二来自友朋交流心得之信札,三来自学子听课笔记及问学通信。在《事辑》所辑“晋至唐史”第一课要旨中,寅师要求学生读《资治通鉴》而非《通鉴纪事本末》,因为前者是原典,后者是别人读《通鉴》的体会,其时时人正喜读《本末》胜过《通鉴》;讲到治史,寅师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发现。”〔7〕
《事辑》在展示寅师治学的过程中,叙述平实、少有概括评论之语。比如,写寅师致力佛经研究,每读典籍,常以点、圈识其要旨,曰:“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劬。而行间、书间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皆枢所不识,不敢赞一辞也。”〔8〕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不仅承传了陈寅恪的治学风尚,同时也秉承了清华园先辈“出言有据,勿为空疏之学”的科学精神。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清华园国学研究所的宗旨,这里的“科学”从本质上对中西科学形式均有普适性的意义,它是企图从本质上把握世界(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统一〔9〕。具体到表述中,指无歧义的语言表述材料。清华教授们以科学为方法和途径达到使学术尽可能接近真理的目的,这与“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赛先生”(Science)不同:前者是在方法论的范畴内来理解和运用科学最本真的意义,后者则将科学作为反封建的工具,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像那个时代流行的各种主义一样,科学也成了“主义”,成了政治运动的符合物。中国的多数民众几乎是在对“科学”一无所知的蒙昧中,骤然醒来,一下子成为科学的传播者和倡导者,这种缺乏哲学层面的知识和意识积累的狂飙突进运动,势必使“赛先生”在被倡导和被传播时,同时被异化,从而走向科学自身的反面。这种被异化的科学思维今天在学术领域里仍混淆着人们对真正科学精神的理解。因此,有人提出:“对科学而言,应该守住自己的阵地,任何对之崇拜和奉承的做法都是力图使科学变成科学主义的企图,最终将毁掉科学应有的作用。”〔10〕陈寅恪一直强调自己从事的研究是探讨历史之“真”的科学研究,他说:“其实我每一分钟都在思考。”他思考的是科学问题而不是生存立足的方式。所以,当陈寅恪“被描写”时,如果强调的是其品质、个性的影响,而将科学研究的过程作为附带物,那描写本身就会成为文化上的泛意识形态产物,从而失掉科学性,走向科学的反面。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编辑:独孤)
点击查看文化昨日超强人气排行榜,更多精彩尽在新浪文化!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