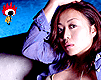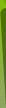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 两个犹太名女人:海明威妻子与邵洵美小妾(组图)(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1/27 19:03 中华读书报 | |
|
她的中国名字叫“项美丽” 艾米莉·哈恩较为中国人所知。她的中国名字是“项美丽”,那是她的“中国丈夫”邵洵美为她取的名字。项美丽于1935年和她的姊姊到达上海,本也只打算小居数月,没想到一待就待到了1943年。到中国之前,她曾只身前去比属刚果,在黑色大陆的中央住了二年。和葛尔红一样,她周游世界,阅历广博,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出版过52本书,且有数 我能找得到有关项美丽的中文资料,当然都是谈她如何成为邵洵美的妾的事迹。毛尖女士写的《邵洵美和项美丽》一文里,谈到东西方对这个爱情故事不同的着眼点,说得十分贴切。中国人写的传记里爱强调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并刻意强调这位白人女子只是一位中国男人的“妾”,好似其中有说不出的得意。 在项美丽的自传及英文的传记中,她绝不是一个“被养着”的女人,她不但一直在经济上供养着邵洵美及他的妻小,并对邵洵美反复向她索钱有过多次的描写,完全颠覆了中国男人“养妾”的怡然自得。 毛尖又说在白人男子 指项美丽传记的作者KenCuthbertson的笔下,邵洵美却成了被“西方女性所欲望的‘美人’”,毛尖引了传记中长段对邵洵美容貌的描写为证。这个观察自有其意义在,不过此处可能有点误引了。那描写邵洵美容貌的段落,并非Cuthbertson的文字,而是出自项美丽自己的一篇小说,所以大概并不能算是“白人男子”的观点。不过依循毛尖女士的取向,对照中英文的资料来看这一桩越国的爱情故事,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两者不但在事件的记载上有着极大的出入,在情绪上更突显了许多东西方各自的一厢情愿。这些有趣的对比,可能值得另写专文讨论。 项美丽在到中国以前已有不少文章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也写过几本小说,但她真正成功地建立起文名,却始自《宋氏姊妹》一书的出版。这本书的得以写成,完全靠了邵洵美的牵线。邵的一位亲戚是宋霭龄的闺中好友,经由那位亲戚的引介,项美丽得以和宋霭龄见面,并由宋霭龄劝服了另两位姊妹让项美丽写她们的传记。她花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在香港与重庆两地和宋美龄共处了长段的时间,三姊妹中除了宋庆龄外,另两位都和她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和葛尔红不同,项美丽对宋美龄非常有好感。她在自传中描述宋霭龄对她的情谊,读来也十分动人。因为对宋氏姊妹正面的描写,使项美丽在美国极受左翼分子的攻击。 《宋氏姊妹》于1940年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到底那时美国有关中国的书籍并不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知识也十分浅显,《宋氏姊妹》的出版样本寄到香港时,项美丽赫然发现封面那个大大的“宋”字居然印颠倒了,出版社急忙重新装订才没闹出一场大笑话。《宋氏姊妹》之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以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了另一本畅销的自传《我所知的中国》。 和葛尔红一样,项美丽拒受传统制约,两人又都是才貌双全,自然一生绯闻不断,但她一生真正浪漫且彻骨铭心的爱情,应是和英国少校鲍克瑟(CharlesBoxers)之间的恋情了。他们两人之间爱情的惊世骇俗,绝不输于她和邵洵美的关系。有多少人的一生可以缔结两桩如是可以入书入戏的爱情 鲍克瑟在战前即驻守香港,早在《天下》杂志中读到项美丽的文章,对她颇为仰慕,到上海时也特别前去探望她,当日却因其它杂务干扰,两人只匆匆相见无缘多谈。项美丽多年后在自传中写到送走鲍克瑟那一刻,自己没来由地觉得怅然。鲍克瑟回港不久就结婚了。 两人后在香港重逢时,鲍克瑟的婚姻虽已出现裂痕,但仍是已婚之身,所以他与项美丽不久之后即展开的恋情并不为舆论所容,等到项美丽怀孕的消息传开,那就真的成为丑闻一桩了。战事急转直下,香港沦陷,鲍克瑟伤重生命危急,后又成为战俘,数年生死不知,项美丽和女儿回到美国后痴痴等待,一场一幕,真可拍成一部高潮迭起如歌如泣的电影。这对恋人最终克服万难,缔结了长达50余年的婚姻。 作品之外不平凡的一生 葛尔红与项美丽两人的生命有太多的平行处,但除了在文坛互闻声名外,两人却可能并没有过什么真正的交集。在我找到的资料里,两人唯一见面是1941年,葛尔红与海明威在香港等着去重庆时。那时项美丽未婚怀孕的消息尚未完全公开,海明威曾自愿出来承担他是“孩子的爸爸”,好使鲍克瑟免受军法制裁。 除了在政治上左右不同的倾向之外,葛尔红与项美丽文风也很不同。葛尔红的文字犀利严苛,几近冷峻,但对境况大局时有一针见血的灼见,所以她的文字常被收入各种语录。项美丽的文字则舒展铺陈,有很大的亲和力。而且她又有几近暴露狂的自白倾向,周围人事一网写尽,不给作传者留下任何空间。这也和葛尔红对私事的洁癖形成强烈的对比。 两人对故乡圣路易也有迥然不同的态度。葛尔红对圣路易有着极大的反感。项美丽对圣路易却一直有一份难忘之情,晚年还曾回到故居凭吊一番,那是80年代的初期 正是我自己迁居到圣路易的时候 ,圣路易已是今非昔比,她那一度是圣路易最高级住宅区的故居所在,已沦为贫民窟,老房子被一划为四,供四家共住,但她仍写了一篇长文,怀想她在圣路易所度过的快乐童年。 现在读葛尔红与项美丽作品的人不多了,即便是在和她们有深厚关系的圣路易,她们的书也少有人借出图书馆。2003年CarolineMoorehead写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葛尔红传记,对葛尔红的一生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是一本极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也许这本书可在读者群中激起一些对葛尔红作品的兴趣。当然,这两位作家在本质上是和新闻挂钩的叙事体作家,她们作品的生命自然与时事同起同落,不过她们文字中所表现出的优异文采,即使是时过境迁,仍有很大的阅读价值。但不可讳言的是,多数人对她们的向往,仍是她们在作品之外所活出的不平凡的一生。从她们传记的题目里,如《勇者无事》(NothingEverHappenstotheBrave)、《美丽的放逐》(TheBeautifulExile)、《没人说别去》(NobodySaidNottoGo),我们就几乎可感到她们生命的质地——火热的生命力,不畏惧的精神,与拒绝不经思考地默守成规。她们在生活与作品中所表现的独立精神,也早已远远地超越了那女性主义尚未萌芽的年代。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