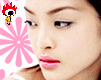| 编剧邹静之:我是愿意在大街上找乐子的人(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3/28 15:56 南方周末 | ||
|
□本报驻沪记者张英 实习生万国花
在如今的影视圈,编剧的名气很少大过导演,可邹静之却是一个例外。他几年前写的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在内地、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具有很高的收视率,在2005年春节的电视屏幕上依然可以看到它们的踪影。他的新作《五月槐花香》在北京首播时,更是创下了仅次于《新闻联播》的收视率。 一些为剧本头疼的电影导演也在找他,现在正在忙着拍摄的有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吴宇森的《赤壁之战》,更早些是应田壮壮要求根据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地》和为陈凯歌写的一个关于老北京的剧本《衣裳》。 因为喜欢音乐和戏剧,邹静之和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合作的歌剧《夜宴》已在香港、英国、比利时、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区和国家上演,为北京人艺写的话剧《我爱桃花》则参加了中日韩三国戏剧节的演出。近日,刚刚离开《诗刊》调到北京作家协会的邹静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抽烟喝酒的剧情 记者:为什么会认为《五月槐花香》是你当编剧以来写得最好的剧本? 邹静之:《五月槐花香》表现的是在地上行走的生活。为什么想写这个作品?当时看了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很有感触,写了篇文章叫《向张大民学习》,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写这样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是我到写的时候才发现,这样实实在在地写很有难度。普通人的生活,吃饭、抽烟、喝酒,还要出戏,不好写。开始写怎么都觉得不对,写出三集以后全部作废了,觉得人物不新鲜、故事过于戏剧性、不够生活。那时就跟自己较劲,经过反反复复的挣扎,后来终于把剧本写完了。我开始有点担心,再后来看过剧本的投资方和(张)国立、王刚、(张)铁林、邓婕都说是一部好戏。他们也是拍古装戏有点多了,这个戏从时代到风格都不一样,大家都有了情绪,我才有了信心。后来,《五月槐花香》就这么拍了。还有就是写戏时看了《钢琴师》,我为波兰斯基的从容所折服。 记者:有观众分析,你写的每一部戏都有一个老百姓感兴趣的主题,因此你的电视剧才那么成功。《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是“借古喻今、反腐倡廉”,《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人际关系、官场厚黑学”,《五月槐花香》是“普及文物知识、教生意经”。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解读? 邹静之: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不过,从我创作的角度简单说来,《康熙微服私访记》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写帝王微服私访,戏剧冲突和戏剧趣味很强,吊人胃口就是很自然的了。换言之,《康》剧是个筐,现实往里装。《铁齿铜牙纪晓岚》有所变化,它借鉴了民间流传的长篇相声的形式,把这种反讽、捧哏、逗哏、抖包袱的状态做到戏中来,这部戏观众说打开了就能看。说《五月槐花香》“普及文物知识、教生意经”,我也不反对,因为我写完了,观众怎么解读都行。但我还是在力求出人物,出味道。 记者:你的几部戏被人命名为“新派古装剧”,你怎么理解这个说法?你怎样看待历史剧里的“正说”与“戏说”? 邹静之:有的人把古装片看成历史,那是他的问题。我想中国最大的戏说可能是《西游记》,没有人看了会觉得唐僧取经时真就是那样吧。评论家说的什么“戏说”也不是新鲜的形式,中国相声中有一种形式叫“八大棍”,什么《君臣斗》啊,《硕二爷》啊,老祖宗早就这么做了,只不过现在电视剧化了。 关于“戏说”与“正说”的评论,有时脱离了戏的本质。你做了一个川菜,他用上海菜的要求来说你,这就没说到一起去。搞“正说”的人往往沾沾自喜,认为用正史的笔调写,就比其他的风格高明。任何一部戏,在风格上没有高下,只有你写得好还是写得坏之分,再就是你观念的高下之分。同样写二战时期的集中营,《辛德勒的名单》是正剧,而《美丽人生》有喜剧的风格。后者悲凉的程度不比前者低,这两部电影都获得了奥斯卡奖。它们对集中营的表现视角不同、风格不同,很难说哪部更伟大。文学不是只有现实主义一种写法,还有很多其他的风格。 提笼架鸟的生活 记者: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年轻、现代化的城市,你在《五月槐花香》、《琉璃厂传奇》里呈现了一个鲜活的老北京,你怎么触摸到老北京的生活方式? 邹静之:我是南方人,可是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大院里,是所谓的新北京人。老北京人的生活我不知道,但在这儿呆久了,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天会像老北京人那样思考问题,包括你的语言、礼节都受到它的影响。 记者:在一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您怎么看待老北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邹静之:我过去不觉得那些提笼架鸟的人生活有多好,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他们的生活比我有意思。他们即使是吃炸酱面、散步、买菜,都要很从容地去做。我看过一个老北京的纪录片,调芝麻酱都必须得调出油来,黄瓜丝之类的什么都不能少。做得这么精,就是为了吃这口炸酱面。这种生活态度不是心静的人做不到,让我吃鲍鱼,我可能两口就吞进去了——浮躁。 我特别欣赏北京人那种处乱不惊的气度,还有他们身上的没来由的自信、讲究。北京人讲究味道和性情,爱说不爱做,“玩”中见精神。而且北京人语言准确、生动、丰富,天生具有后现代反讽的精神,好“斗机锋”,善于用各种各样的语调和语法,比如用赞赏来进行嘲讽。真正的老北京人说话很讲究,声音不大,速度也慢。那种老门老户的人家,即使窘迫了也窘得很有体面、有尊严、很从容。 记者:《五月槐花香》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看了觉得有意思,可是大家又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单调。 邹静之:我是愿意在大街上找乐子的人。你永远想不到一个普通操场是多么有意思,我爱和楼下的人聊天,像理发师、开电梯的小女孩,都很有意思。生活看你怎么看。很多人用文学家的眼光、不用生活中的眼光来看,那的确是很没意思,我宁可用一个生活者的眼光来看。一个盲人曾告诉过我,他不怕车水马龙、沟沟坎坎(因为有参照物)。他最怕把他一个人扔在大广场上,他说那样他就真瞎了。 以头撞墙的写作 记者:大多数中国作家都认为写影视剧会对自己的写作有伤害,而你不同意这一点,还说从中获益不少。 邹静之:你说的大多数,我没调查过,我认识的大多数作家都写过影视作品。中国古代小说原就是说书人的话本,《金瓶梅》、《三国》、《水浒》就是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再早有连台本戏,《牡丹亭》什么的一演半个月,与电视剧有相同的功能与功效———现在都把这些当做名著了。当然有的小说不适宜改成影视剧,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改成电影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我敬佩老舍,他可以写小说(还有英文的)、相声、大鼓词、话剧、诗歌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能,现在人差远了。那些说写剧本对他们有伤害的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不喜欢写,或者觉得写影视是等而下之。 记者:您还呼吁作家参与电视剧、电影的创作,并认为电视剧和文学一样伟大,也是可以传世的,你有哪些例证? 邹静之:电影刚刚出现时,被文化人看作是光影的杂耍,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小视的综合性艺术。当然这一切都取代不了文学,也没有谁想取代文学。我看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电视剧,有的比电影好看。我觉得国内的电视剧能够在亚洲与其他国家的电视剧相抗衡,正因为有很多作家加入到这个队伍里。中国电视剧是在世界的华人地区最有影响的艺术形式。越南那些国家会放中国戏,韩国有中国电视剧频道,这比漫画、电影的势头都强劲。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播途径,否则恐怕只有什么哈日、哈韩、哈好莱坞了。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看,我是因为阿巴斯的电影才多多少少地知道一些伊朗,我是因为这些年的电影才了解韩国。你要有声音,《英雄》能在美国两周排行第一,《孔雀》和其他电影能得奖,他们就是民族英雄。 记者:你说你是把电视剧当诗写、写歌词也是写诗的一种,这怎么理解? 邹静之:我写话剧、写儿童剧,包括写歌词,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我是一个通过追求变化来求得写作新鲜感的人,有人认为不断变换文体是一种伤害,而我认为是有帮助的,一种文体的经验可以丰富另一种文体。我最近在改我以前的散文,我发觉它们语言不利落、有障碍,这种感受在我写剧本以前是没有的。 记者:诗在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吗?你在平时生活中经常从诗歌里获得愉悦吗? 邹静之:读到一首好诗会让人失神,就像箱子“咔嗒”一下合上了,这种感觉无法形容,豁然开朗。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不要放到什么“坛”里去,诗人不是从“坛”里出来的,诗人是个体的。经济发达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往往知道一个人而不知道他的作品,作者可以被传媒包装为资讯的主角,往往先于作品,但是作者是需要依附作品成长起来的。我在《诗刊》做了很多年的编辑,我发现很多优秀的诗人并不关注诗坛,或者是在诗坛边缘的人。我也不关注什么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出现好诗。 记者:你写戏剧《夜宴》、《我爱桃花》,是否因为它纯粹是编剧的,而不是属于导演。好像你还有一系列的戏剧创作计划。 邹静之:电影永远是导演的,歌剧是作曲家的,电视剧永远是演员的,只有话剧会提到是谁写的,是属于剧作家的,比如老舍的话剧、莎士比亚的话剧。一个好的文本会不断被重排,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管演绎多少次,凸现的是作者、是文学。但是不要以为由于这个凸现,我以前写电影、电视剧就感到委屈,然后才转到戏剧上来。 我特别喜欢戏剧,剧场的人都知道我爱看戏,写戏剧的过程也特别地有魅力。昨天上午我坐了很久写不出来,不得其门而入,想用头撞墙,傍晚的时候我又突然写出来了。电视剧是由内心向外释放,把你内心的东西释放出来,而戏剧和诗歌首先要把你的感悟往心里收,过滤,过滤后再放出来,它更精细、更准确、更让人凝神。 (责编:幽山)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