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家资耀华之子忆父亲:一心要摘资产阶级帽子(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4/12 18:28 文汇报 | |
|
解放前由于工作需要,他“应酬”很多,在外面比在家吃饭的时候多,但是从不涉足歌场舞榭,极少在9点以后回家。除了我外婆来天津住的期间为了她有时请朋友来家打麻将外,我家与麻将绝缘。我们都不会打。父亲特别认为搓麻将的气氛有一种“乌烟瘴气”。大约是受他的影响,我对麻将也有这种感觉。作为银行业者,需要“来的都是客,招待十六方”,似乎应该练就善交际、比较圆滑的作风,但是父亲又截然相反。他作风极方,有时甚至近乎迂阔,违背自己原则的事决不通融。从他的回忆录来看,他打过交道的国、共两党的高 他一生为人的座右铭是“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在实践中可以说推向极致。对于规章制度,连制订者都不一定执行的,他都严格执行,解放前后,大事小事都如此。小事例如同样的药,他不许母亲吃他的,因为报销渠道不一样。大事例如书中提到1948年他赴美刚好与后来成为香港船王的董浩云(即前港首董建华之父)同船并同室,欢谈甚洽。董是乘战后大批美国战舰退役之机去买船,并动员他也在这方面投资,这是稳赚大钱的,而且机会稍纵即逝。资说自己没钱(这是事实),董即建议上海银行投资,他说这么大笔钱他无权作决定,必须董事会通过(他当时在上海银行地位不低,是整个华北地区各分行的总负责人)。个人“无钱”,对银行“无权”,非常说明其为人特点。 但是从书中提到的许多关键事件来看,他并非一味的谨小慎微,有时在非常形势下能采取有一定风险的非常行动,出奇制胜,在抗日前夕与在沦陷区的天津尤其如此。书中提到在1941年以后日本占领期间“群魔乱舞,人妖难分,不得不与平日素所鄙视,或不愿接触的人物虚与委蛇”的苦痛心情,我完全能想象。记得在那期间很少见他笑容。终于积郁成疾,生了几年肺病。又值物资匮乏,那是我家日子最难过的一段时期。 父亲衷心拥护共产党,而且直到晚年始终不渝,这里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也有他本人的特殊性。共性是指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的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引无数英雄竟折腰,百年民族屈辱和忧患迸发出热泪如雨。我见过父亲的一篇自述中说到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作为中国人受到的是公开的蔑视和欺负,在美国留学期间受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二者他都受不了。所以在年近半百时听到毛主席那句话,立即热泪盈眶,从此决心追随共产党。外人和当代青年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后对种种苦难、委屈、乃至残酷、荒诞竟有那么大的承受力,感到不可思议。要理解这一点当从这句话开始。那种强烈的对民族屈辱的感受,那种刻骨铭心的对国家富强的向往,怎一个“爱国”了得! 至于特殊性,他体质很好,很少生病,壮年一共生过两场险些夺命的大病,一场是让日本人气的,已如前述,一场是让国民党气的。对国民政府深刻的失望对他打击尤大。他奉陈光甫之命不得已忍辱负重留在沦陷区,每时每刻都在盼光复,偷偷在被窝里听广播,每听到重庆的声音就很兴奋,是对国民政府寄予很大希望的。本书第二十三章叙述他在抗战胜利后作为华北金融界的代表访问重庆的失望情况我也有记忆。他去时正浸沉在日本投降的兴奋之中,抱着满腔希望和宏远的规划而去,归来时判若两人,几乎是抬回来的。记得胜利后第一个“双十节”,我们学校组织庆祝游行,还有“欢迎国军”之类,他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庆祝”、“欢迎”什么呀,不要去了。后来,如书中所说,宋氏家族又对他们那些民营银行虎视眈眈。 所以,他从1935年到天津“创业”到1948年底天津解放的十几年中名副其实地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没有真正舒心过,因此对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心悦诚服。他1948年赴美,在美国期间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大为兴奋,更促使他兼程赶回国。他原来是立志不参政的,但是1949年共产党请他参加政协代表会议他欣然参加,并参加《共同纲领》草案审议小组,一直以此为荣。解放初期他真的是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其中被认为立了大功的一条就是及时劝阻了新政府准备取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名号之议(因为那是官僚资本),保留这个名字,从而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今天中国银行的职工,乃至整个银行界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除了民族国家大的方面之外,我感到他的秉性、生活方式以及对私产的淡薄等都使他比一般上层人士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统治,更少抵触和顾虑。从意识形态上讲,他并不特别欣赏自由主义。他不大喜欢美国人的放任,而佩服德国人的认真、严谨和纪律。当然,他在二战中的立场绝对是在反法西斯一边,只是为德国人民惋惜。我听他说过,30年代(大约1933年)到德国时印象很深,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优秀、“有出息”的民族,真可惜,被这么个人领上了歧路!他自己的作风也很严谨,例如把准时、履约看作很重要的原则。所以,解放初期他对共产党的讲纪律并不像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那样感到拘束。他与我母亲都厌恶纨绔子弟,解放后发现他熟悉的青年以及子侄辈中冒出来不少地下党员,而这些人符合他的标准的朝气蓬勃、勤奋向上的青年,也增加他对共产党的好感。凡此种种,都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工商界人士惶惶不安,不少上层家庭准备南逃时,他反其道而行,从美国弃船坐飞机赶回天津,决心追随共产党。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解放初期的“积极”也是真诚的,极少被迫的成分,更不是投机。 “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受到极大的冲击,而且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牢骚和怨言,对此保持绝对沉默。书中对这一段到反右也只字不提。我觉得一方面他的确个人比较想得开;一方面对共产党采取“为尊者讳”也是他的一贯态度。晚年他几乎完全失聪,可能对有些民情比一般人闭塞。但是以他的阅历和对国事的关心,恐怕也不可能对现实全然无知。有一件事可能说明一些问题:大约在他逝世前一年,他曾表示要送一件象征性的礼物给一位经常对他生活照顾有加的统战部官员,略表感谢之意。华筠建议送一件刻一篇古文或诗词的小型工艺品。他欣然同意并立刻提出要刻“阿房宫赋”,并且一反常态,大声说要的就是最后那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由此看来,他虽然平日无言,心中并非没有想法,而且想得很深(后来听说那件礼物终于没有用此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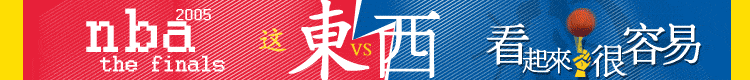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