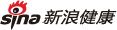科学家研究发现行为可能改变基因遗传给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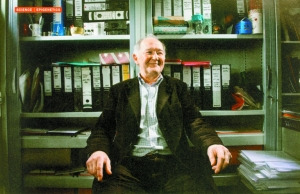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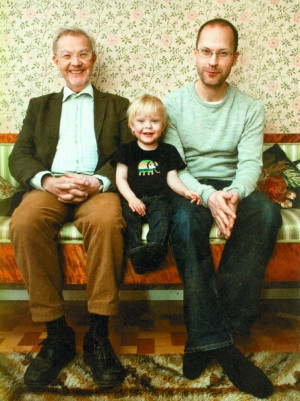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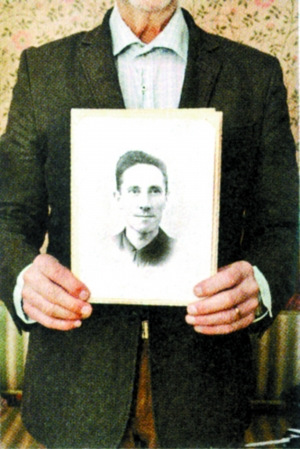
“赌徒的后代很有可能会子承父业继续赌,父辈的坏习惯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显然是一种有违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告诉我们,环境对物种的作用力通常不会很快显现,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
然而,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科学家最近宣布,后天的生活习惯、环境等多方面条件都可以对人类的基因产生迅速而直接的遗传影响。
这个发现在科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长期以来,生物学和遗传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恰恰是问题的反面,即基因对于人类后天行为的影响。至于后天环境、行为对基因有多大影响,则几乎是一片未有涉足的“科学荒漠”。
瑞典科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濒临饿死)会在人类卵子和精子的遗传物质上留下深深的“印痕”,这种基因标记会在短时间内将新特性传递给下一代。
当代科学家公然挑战进化论鼻祖达尔文,孰是孰非?这篇报道将带领读者再次走进人类基因的神奇世界。
“荒原”上的人类基因密码
瑞典北部长年被冰雪覆盖,人迹罕至,而这里却诞生了一个有关人类基因的神秘故事。
故事发生在瑞典最北部的北博滕省,偌大的省份却人烟稀少,人口密度只有2人/平方公里。早在19世纪,这个省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如果赶上年份不好,人们就只有饿死的份。更恶劣的是,这里的土地仿佛和人作对似的,要么就是丰产丰收,要么却是颗粒无收,结果是粮食要么多得摆几个月宴席都吃不完,要么就是严冬来临却无米下锅。
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拉斯·奥雷·本内博士的关注,他想知道丰年和荒年对当地儿童的影响。本内博士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对象不仅限于当时的儿童,还包括他们的后代,这是个旷日经年的课题。
本内博士在北博滕省的奥佛卡利克斯教区,随机选取了99名1905年出生的孩子作为研究样本,并通过详尽的历史档案追踪溯源,把孩子的父母甚至祖父母都找了出来。之后根据本地的农业档案,确定了孩子的父辈和祖父辈年轻时的食物供给情况。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本内博士被一篇发表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1986年)上的文章深深吸引。文章认为子宫发育不仅影响胎儿成长,也影响着成年后的健康。如果孕妇营养不良,孩子成年后患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受到这篇颇具“异教”特色文章的启发,本内博士心中又升起了另一个问号:这种影响是否早在怀孕前就开始了?父母年轻时的经历是否能改变遗传呢?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科学界真得算是“平地一声惊雷”。长期以来,DNA不会在后天被改变的理论统治着主流生物学界。不管我们选择如何过完这一生,发胖也好,长期“亚健康”也好,都不会改变我们的基因——人类的“种子”,当下一代出生后,父辈的一切就被涂抹殆尽。
更为重要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已深入人心。环境对物种的作用力通常不会很快显现,进化是个历经数代数百万年的自然选择过程。但是本内和其他科学家搜集的大量历史数据却显示,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濒临饿死)会在人类卵子和精子的遗传物质上留下深深的“印痕”,这种基因标记会在短时间内将新特性传递给接下来的一代。
根据本内的研究,奥佛卡利克斯教区那些赶上丰年的男孩子们,不论他们是正常饮食,还是暴饮暴食,其儿孙辈的寿命却意外变短了。和经历荒年的男孩后代相比,平均寿命要减少6年之多。再加上社会经济变化因素的影响,寿命差距竟然上升至32年。本内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01年荷兰的《生物技术学报》上,他在文中援引了同事提供的该省其他地区的资料,显示这种状况对于女孩也适用。简而言之,经历过丰年衣食无忧的年轻人,产生了类似生物链的效应:他们的后代却要比他们早逝几十年。这可能吗?
基因是“硬件”,外基因是“软件”
要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就不能单单从自然环境和后天养育入手。本内和同事历经20载春秋,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实验胚胎学(epigenetics)。它的研究核心就是基因活性的变化,在不改变遗传密码的前提下,这种变化是如何被成功“植入”子女一代的。
他们认为,基因表达模式受到一种名叫“外基因”的细胞物质的控制。这里所谓的“外基因”,位置排在基因之外,因而其英文对等字是在“基因”genetic加上了表示“在……之上”的前缀epi。正是这些外基因的“标记”,发出指令,控制着我们的基因开关。外部刺激就是通过外基因标记(epigenetic marks)作用于基因,因此环境等后天因素,比如饮食、压力、孕期营养等,就会对子女一代产生影响。
实验胚胎学传递出的信息,让人喜忧参半。忧的是,吸烟,暴饮暴食等坏习惯会改变DNA之外的外基因标记,使得肥胖基因占据主导地位,而长寿基因则退居末位。以前大家都知道抽烟或者肥胖无法让人活个大岁数,而现在人们却突然发现,这些不良习惯甚至会波及子女,增加他们的患病率和早逝风险。即使宝宝尚未出生,这些仿佛已经被“命中注定”了。
不过人类向来相信“与天斗,其乐无穷”,外基因一经“出世”,科学家就开始尝试控制外基因标记,开发一种能抑制坏基因,激活好基因的药物。2004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首次批准了一种外基因药物——氮杂胞苷(Azacitidine),用于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该药通过外基因标记不断激活血液母细胞基因,提高该组基因的主导地位。据总部设在新泽西州的Celgene公司介绍,MDS重症患者服用氮杂胞苷后,平均能多活两年,而采用传统疗法的患者,存活期只有15个月。
对于进行中的外基因研究,最理想的成果就是只要轻触“生化按钮”,就能赋予基因一双慧眼,自行抵抗疾病的入侵。到那时,什么癌症、精神分裂症、孤独症、老年痴呆症、糖尿病等疑难杂症,统统靠边站——让坏基因去冬眠吧!最终,人类就有了自己的王牌,可以叫板达尔文的进化论!
最近,科学家进一步认识到实验胚胎学的妙用。利用这个新式“解码器”,许多传统遗传学不能解释的科学奥秘,就此得到了破解。比如为什么同卵双胞胎,一个有燥郁症或者哮喘,而另一个却若无其事?为什么患孤独症的男孩数量是女孩的四倍呢?为什么在北博滕省父辈饮食的两极分化也会导致子女寿命发生巨大变化呢?以上种种,基因或许都相同,但显然基因表达模式发生了偏差。
打个比方吧,如果基因是硬件,那么外基因就是软件。只要用户愿意,完全可以在苹果机上安装Windows。尽管“心”还是原来的芯,就好比基因都相同,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软件,操作模式也就变得两样了。
基因也许会在几代之内生变
19世纪瑞典最北部的北博滕省丰年和荒年的交替出现,导致了该地区人口外基因的改变,这点早在2000年初似乎已经被“圈内人”接受。而一直困扰本内博士的问题是这种改变是如何进行的,一次他偶然看到一篇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谜底才逐渐变得触手可及了。这篇文章由伦敦大学著名遗传学家马库斯·彭布雷博士撰写,尽管有些晦涩,却成了本内眼中的“启明星”。
虽然彭布雷博士的这篇论文在当下已经荣升为实验胚胎学上的一份开山之作,但在完成之初却是处处碰壁,主流学术期刊都拒绝发表,好不容易才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学术期刊上找到了落脚点。彭布雷本人是一名坚定的进化论支持者,但在这篇论文里却用现代实验胚胎学的观点对达尔文提出了质疑——如果工业时代来自环境和社会变革的压力越来越大,进而迫使进化要求迅速做出反应,情况会如何?而如果基因顺应了进化的需求,则不需要经历数百年或数代人,也许几代之内就会发生改变,情况又会如何?
更多关于 行为 遗传 的新闻
- 女性出现欺骗行为44%源于母亲遗传基因 2009-11-02 11:11
- 最新研究发现人类寿命长短或源自父亲遗传 2010-01-02 10:55
- 研究称男女购物方式不同由遗传基因导致 2009-12-05 05:40
- 研究发现女性出现少白头多由遗传导致 2009-12-04 11:25
- 人类长寿基因主要从母亲处遗传 2009-10-02 10:33
- 专家表示身材胖瘦30%受遗传基因影响 2009-09-05 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