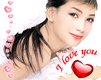科举与国学:在纠葛中共存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9日10:43 新京报 | ||||||
|
学者们认为,科举与国学是辩证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阻碍
任继愈 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现为国图名誉馆长。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中国哲学史论》等。
陈明 1962生,湖南长沙人。现为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儒教室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对谈录》、《儒者之维》等;创办《原道》并任主编。
王曾瑜 1939年生于上海。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宋朝阶级结构》等。 科举与国学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漫长的科举发展史中,科举对国学的发展有着片面而深刻的影响。本版通过三位学者的观点细述了它们之间的纠葛。 ●科举促进国学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科举之前,考生们一般以读经学书为主,做官以后,读其他的国学著作就自由了。 ●儒学作为文化道术,其整体的文化功能因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搭载而有相对稳定的发挥实现,但并不能说没有科举就没有儒学。 ●经学里面有一个不太好的传统,就是把宇宙模式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创造、解释。 任继愈:科举促进国学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科举首先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它由国家统一出题、统一考试、统一教材,教材就是四书五经。它让多民族国家都要接受这个教育和经学训练,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各个民族的人才。 科举考试主要是经学,也就是圣人说的话。这就使经学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套叫做“国学”的东西。 国学和科举都起到了使各民族团结,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作用。科举制度的一个好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明朝以后有一个规定,各地区都要出人,比如云贵偏远的地方录取人少一点,江浙地区录取的人多一点,但都得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向心力和凝聚力,科举制度和国学加强、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出题比较活,考试的时候考文学,让人写诗。唐朝的诗歌很繁荣,与科举这个指挥棒关系很大。科举出什么题目,国学的那个范围就会有很多人去钻研。宋朝的时候,考试范围也比较广。书目列举在那里,你自己去读。为了读懂这些书,书生们还会参考其他的解释性著作。这个阶段,读书较多,知识面较广的人更有优势。 科举促进国学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科举之前,考生们一般以读经学书为主,做官以后,读其他的国学著作就自由了。 在国学里面,经是主干,史、子、集都是分支,“集”从哪里来的呢?它就是解释“经”的著作。像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集,好多都是解释经的。《四书》就是朱熹定的,它后来获得了与《五经》同样的地位,科举就考这个。而且从明朝以后还规定,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答案。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新思想的发展。因为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解释中发展出一个新体系也说不定。建一个理论,代替圣贤说话,不是你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就把人给限制死了。 从科举考试内容就开始限制,这就很有害,而不是科举本身有害。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题目都出尽了,因为《四书》文字有限,考了600年免不了有重复,就用上一句尾巴上的话,下一句头上的话,两个凑起来作为题目,还让你做,写成八股。这样既不能培养人才,也使国学走入了死胡同。在文章里面说假话、空话就是从八股文里面开始的。这个时期,发展国学的人都是在做官以后或家里有钱,不愿意参加科举的人。 陈明:科举与儒学是多维立体复杂辩证的 把科举与国学的关系转换成特定选官制度与儒学的关系,虽然略有出入,谈起来却可以具体深入许多。简单地说,科举是国家政府的选官制度,而这个权力机构是以皇帝及其利益集团为轴心;儒学是文化道术,它反映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通过考试儒学出仕朝廷为官,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儒学来说,就像对于王权一样,具有某种双刃剑的性质。从这样一个视角观照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科举与儒学的关系乃是多维立体复杂辩证的。 从历时性上说,它经历了一个二者由相对冲突对立到相对稳定统一的过程;从共时性上说,它一方面使儒学的政治功能、社会权威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和强化,另一方面又使儒学的道义目标、理论生机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和抑制。 先说第一点。作为制度性选官渠道,科举制所否定取代的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汉代察举制的极端化或变形。这使得“儒宗地主”日益发展。隋文帝统一中国后,皇权重新获得对社会力量的控制权,九品中正制被自上而下的科举考试制度替代就成为必然。著名的牛李党争,也有此深层背景在。唐代裴行俭说“士之志远,先器识,后文艺”,以及后来“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读书当以经义为先”的议论,都是指向当时科举重才能技能轻德行境界这点。 再说第二点。儒学的理想是行王道,“士之仕也,行其义也”。但秦汉之后,“君子不器”、“志于道”的儒生不得不妥协降格为“器”或“技”以获得进入霸道体制的可能。公孙弘被讥为“曲学阿世”,董仲舒也不免。科举制使天下英雄尽入皇帝彀中,儒学自然更是不复孟子时代“说大人物则藐之”的浩然之气。这既不能怨儒生,也不能怪科举,而是莫之如何的历史必然。 另一方面,元、明、清均用王安石定下的考试方法,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这使得儒学经典沦落成为读书士子的记诵文本。 儒学作为文化道术,其整体的文化功能因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搭载而有相对稳定的发挥实现,但并不能说没有科举就没有儒学。不要忘了废科举之议正是张之洞、康有为等儒士大夫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提出来的。在科举制废弃后,儒学的其他功能(如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等)如何实现?这才是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王曾瑜:科举阻碍了国学在自然哲学领域的发展 汉武帝以来,国学的整体面貌就转变成以尊孔读经为主,以后总的来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本来唐朝是诗赋取士,宋朝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改成了经学取士———而经学正是国学最主要的部分。从当时来说,这种做法有其必要性。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副作用比较大,因为教育的功能有很多方面,经学取士就把教育的功能狭隘地变成了单单是为了考试做官。 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胡适先生做过一个研究对比。他研究了清朝经学的乾嘉学派,他觉得,西方人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搞自然科学,这应该是西方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中国这些学者不是没有聪明智慧,但是全用在钻故纸堆上。 这一点使中国与西方国家拉开了差距,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偏重于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自然哲学不发达。 经学里面有一个不太好的传统,就是把宇宙模式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创造、解释。比如无极生太极,阴阳生五行……不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科举把无数士人的聪明才智弄到了经学上,读经学就是为了做官,乾嘉学派就是多了一些考据,所以科举考试后来被废止也有必然性。 整个科举制度,不仅没有改变国学缺乏自然哲学的弊病,反而使这种现象加深了。王安石变法和八股文是文化专制的主要因素———统治阶级利用科举制度,让国学为他服务。他认为最有用的就是经学,因此选取了这一部分。如果说,国学有一部分需要扬弃,那么科举则让这种扬弃彻底杜绝,你必须按照统治者设定的范围应答,不然它不取你。因此,科举制度就是让国学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在发展。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模式,就是落难公子中状元,一个书生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先读经,读了经以后中科举,然后施展抱负,治国平天下。从来没有一个书生想到,我在自然科学上有什么发展。当然,我们也有沈括这样的科学家,但是没有形成风气,绝对没有人说,我们要造就沈括这样的人。 本报记者张弘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