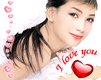余华:以《兄弟》逼近现实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0日09:22 南方日报 |
|
热点透视 文/特约记者 吴立艳 编者按 在当代文坛活跃着的作家身影中,余华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一位实力派作家。新作《兄弟》甫一面世即广受关注,顿成文坛争论的热点。本报特意编发记者对余华的访谈,同时为了给读者提供不同的声音,配发一篇“辣评”,以活跃大家的思路。 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发表10年之后,余华终于出版了他的新长篇小说《兄弟》。为这本书,喜欢他作品的读者已经等得太久。 因为余华的名气,《兄弟》的出版成为文学界关注的一件大事情。虽然《兄弟》到目前还只是出版了上部,但是开机20万册的首发数已足够让余华扬眉吐气。 对自己的书的畅销,余华认为,“我的书是在《活着》在国外拿奖以后越卖越好的。《活着》现在每年都能卖好几万册,加起来的总数量大概有50万册了。我也想过,它卖得这么好的一个原因是这本书有名,被张艺谋改成了电影,通过新闻媒介,它不断被读者注意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活着》很好读,在这本小说里,我采取的写法是让福贵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福贵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他自述的口吻限制作家只能操持那种朴素、平实、易懂的语言,故事也是呈单线条发展,大众能够比较容易读下去的。” 《兄弟》上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它通过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现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 而根据余华自己的解释来说,《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这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在上海书市现场,出版社打出的宣传口号是“余华十年磨一剑,《活着》以后看《兄弟》”。余华一听就乐了:“什么十年磨一剑,其实1995年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后,我一直在写东西,但是电脑坏了,而我写的东西都是用老格式存的,放到新电脑里打不开,加上已经写的东西我本身就不满意,干脆就不写了,偷懒给自己放了假。到2000年才又开始写一部长篇,写几个家庭一个世纪的事情,写了一半又停下了。直到2003年8月,才动笔写《兄弟》,十年一剑,其实是一年多磨出来的。” 在余华眼睛里,《兄弟》比《许三观卖血记》、《活着》更加丰富和饱满,是一部超过以往创作水平的作品。谈到对《兄弟》的自我评价时,余华非常自信地表示,这绝对是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且他认为《兄弟》在叙述的力度上超过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和以往的纯文学开头不一样,《兄弟》有一个畅销书常用的开始:李光头的父亲和别人通奸时不怎么光彩地意外身亡,而同一天李光头出生。因为在厕所偷看了女人屁股的李光头让对他寄予厚望的母亲李兰非常失望,在饥饿最困难的时期,宋钢的父亲宋凡平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挺身而出,帮助了李光头的母亲李兰,被后者视为恩人。几年后宋钢的母亲也亡故,李兰和宋凡平在互相帮助中相爱并结婚,虽然这场婚姻遭到了镇上人们的鄙夷和嘲弄,但两人依然相爱甚笃,而李光头和宋钢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也十分投缘。李兰去上海看病,而“文革”开始,宋凡平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虐待,但他坚持给病中的妻子写信,隐瞒了事实真相,用想像出的美好生活欺骗着妻子,但最终仍然逃脱不了惨死的命运。李兰为宋凡平守孝,7年不洗头,而李光头和宋钢则在相互照顾中成长…… 《兄弟》里的温暖情感和人性之光让熟悉他艺术风格的读者感到惊讶。余华说,因为小说的上部故事发生在“文革”中,那样惨烈的回忆如果没有家庭的温情和忠诚来调和,“这小说我没法写下去”,于是,那些关于家庭的温暖细节,就成了余华和读者在残忍暴力冲突中的精神支持,也成为余华新作中最吸引人的亮点。 写《兄弟》让余华再次体会到了失控的感觉和激情。现在,《兄弟》的下部已经写完,等忙完出版社的各种宣传活动以后,余华将把下部再打磨好,交给出版社,在明年年初出版与读者见面。 余华表示,下部的结构与上部几乎一致,但内容却有很大不同。上部描绘的是反人性的文革时代,下部则是人性在现时社会的表现,主角还是李光头。文革中,李光头的母亲临死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李光头,这个人到了新时代反而能如鱼得水,宋钢那样的老实人却陷入了困境,在时代背景下,兄弟俩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驰,各自有了不同的结局。 写出真正的中国人——余华访谈录 文/特约记者 吴立艳 记者:同你以前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在结构、叙述、文体上有了新的变化。整个小说的语言回旋反复,这是不是同你喜欢听音乐有关? 余华:我们这一代作家写不好对话是要命的。有段时间我非常羡慕王朔,他的对话写得很精彩,我对王朔说:“你用方言土语写我们都看得懂,我用方言写作你就看不懂”,像我们生活在南方那么一个环境,用我从小使用的方言写作的话,完全会成一堆错别字。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方语言对南方语言是一种压迫。南方作家只能曲线救国,用不同的办法去解决这个困难。在叙述上节奏感被打乱了。 后来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用越剧中的腔调写,它经常有一点啰嗦,把一句简单的话说得啰嗦一点。当它一旦重复,它的旋律感也就出来了。所以这种叙述的音乐感推着向前走,生活化的对白气味也就出现了。刚开始写没把握,后来就顺手了。感觉好极了。这样我在写长篇时遇到的两个困难:心理描写和人物对话问题得到了解决,前面解决了心理描写,后面解决了对话问题。这个对话不仅仅是人物在发言,它还承担着推动叙述的作用。我想以后遇到的困难将会是作家在感觉判断上的一些小问题。 记者:现在看来《在细雨中呼喊》的叙述还比较华美,到《活着》时就发生了变化。有了新的尝试,对话开始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看到《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后,觉得你的作品在整个风格上发生了巨变。与此同时,整个先锋派文学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试问,对这些变化你是怎么想的? 余华:我经常遇到这些话题。现在有一些人,他发觉时代在变化,身边的朋友在变化,他没有感觉到自己也正在变化。所以老有人问我“你写的作品为什么和80年代不一样?”我说我今天和你对话的话题和80年代是不是一样?一切都在变,作家也在变。从个人体会来说吧,有人说年龄越大越理智,但我恰恰相反,年龄越大越相信感觉的东西,而不相信那些教条的东西。刚开始写作时,总是想把对世界本质的看法写出来,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世界的本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表达他内心对生活、人生、命运、世界的全部感受,但一个作家优秀与否,和他长期写作中叙述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他应该知道写到什么地方笔下的人物应该说什么话,这一句应该在叙述中达到什么效果。这是一种判断、一种叙述中必须掌握的技能。另一方面来说,我感觉到用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可能比作家自身的东西在不同的环境中更有力量。 记者:记得王安忆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细雨中呼喊》标志着你的作品走出了迷雾:由模糊到清晰,找到了把握世界本质的方法,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人物的形象刻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物活起来,这非常好。 余华:在我以前的作品中,人物基本上都是一个符号而已,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以前我有一个理论,一个人物和一幢房子,一条街道像一棵树一样的,都是道具,彼此都不是很重要。但写到后来,我觉得一个人物要比一棵树木重要得多。记得有一次在黄山时,我与林斤澜老先生去散步。他谈到有一次汪曾祺去见沈从文,问他关于形象描写的问题,沈先生想了想说了一个“贴”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对。许多前辈作家的经验我年轻时都反对,但是我现在回过头一想,我的写作证明他们的经验都是正确的。 记者:从你的创作来看,你的早期作品许多方面都在表现“人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建立在冷漠的叙述之上的,展示人的丑恶,而从今天的作品来比较,你的作品总的感觉趋向于温和了。 余华:我早期的作品里,对恶表现更多更充分一些。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这种写作是某种认识走到极端的反叛。我们在成长期受到的教育都是正面的教育。那时不是从事物的两面或全面去观察和分析事物,只强调一面。我有一天发现从前被掩盖的认识有着许多层面,包括暴力和残忍。恶其实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激情形式,一种表达内心的渴望。人归根结底不是说老是渴望拥有钱、穿好衣服,吃一顿好的饭,有时侯也渴望砍掉一棵树杀死一条鱼,这种渴望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我当时的写作主要是从这一方面有所反动,试图重新去审视我30多年的经历里被自己或别人一块儿帮助我掩盖的那些事物,而到了90年代以后,我的作品相对来讲,变得温和多了。但是,生活就不残酷吗?程永新看完小说后给我打电话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小说比《现实一种》要更残忍,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有道理,这给我印象很深。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法斯宾德的世界》,这部电影有两个结尾:一个结尾是女主人公过上了很正常的生活,还当上祖母。另一个结尾是女主人公暴死街头,死得很惨。后来记者就问法斯宾格,你更喜欢哪个结尾?他回答说喜欢第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样更残忍。我理解,这是他对生活全理解之后才能说得出这种话来。所以近几部作品越来越温和,而作品中那股力量却没有减弱,而且还得到了加强。 记者:如果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80年代的早期作品,你比较注重形式、暴力、死亡,90年代你比较重视揭示日常生活现实的残酷。从这个角度来看,《兄弟》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余华:通过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发现十几年的写作就是作家在不断理解他笔下所写出来的人物。写到今天为止,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当一个作家就是一辈子不断地去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和各种不同的人,理解越多越对写作有好处。小时侯住在医院里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哭声,我奇怪的是晚上死的人要比白天多,凌晨时更多。写《兄弟》我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在里面的。总的来说,《兄弟》标志着作为一个作家我已经完全成熟了。我的写作状态有了新的改变,让我恢复了激情,使我又能写上好几年。目前为止,我经历了好几次起伏,开始是在《星星》发表时,那是我的处女作。后来是《十八岁出门远行》、《许三观卖血记》,又维持了几年的写作激情,现在有了《兄弟》,我相信我是能够创造一个高峰的。它对我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就是我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走向了平民的立场。 辣评 煽情的文革故事和余华的退化——读余华小说《兄弟》 文/张弘 应该说,《兄弟》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从主人公李光头在厕所偷窥女人屁股被游街开始,作者沉浸在特定时空特定事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中,在低级趣味被无休止的释放和满足的同时,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余华在叙述背后得意的微笑,仿佛李光头看到刘镇美女林红屁股时的沉迷。而余华对于暴力的迷恋,又恰似小说中李光头继承了父亲刘山峰爱在厕所看女人屁股的光荣传统——刘山峰因此掉入厕所被淹死并没有成为前车之鉴,不知不觉延续父亲习惯的儿子因此还享到了口福,这或许也是他先在厕所闻臭而后再吃香喝辣的回报。而余华的回报就是畅销所带来的版税收入,这一点他乐于见到;而另一方面的回报则是文学上的失败和畸变,即使他不承认,但是在他的写作上已经毫无疑问地发生。 《兄弟》选取了一个极端的故事,人格伟岸的宋凡平因为跳下厕所捞起刘山峰的尸体,最后因此与李光头的母亲李兰结婚,宋凡平的儿子宋钢因此和李光头成为兄弟。其后,宋凡平因家庭成分为地主被折磨致死,李兰也随后病故。从一开始,余华就流连于现象的迷宫里,自我感觉良好地游走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茫然。他称,“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作为文学的典型,李光头一家的故事的确发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比它更残酷。而就本书所描述的内容而言,“本能压抑”指的就是性压抑,从刘山峰、李光头偷窥,到李光头在板凳、电线杆上寻求性满足以致他的性欲消失,作者都在强调这一点。 由此,余华的局限和浅陋一览无遗。他对“文革”的悲剧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只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和塑造闭门造车。以此为出发点,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蹩脚、变形的文革故事,在满足读者窥私癖的同时,也显示出自己创造力的委琐和衰竭。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文革”的悲剧性都不会从性压抑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恰恰相反,“文革”中后期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文革”的最大悲剧在于,它经由国家领导发动,让社会的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降为动物与动物之间相互残杀的关系,人性恶的一面在正大光明的旗帜和口号下表现到了极致。不管是作为文学家还是学者,穿越丑陋事实的表象,在不同领域用不同手法表现、追究其发生机制和原因,由此让读者对丑恶事件背后的根源产生深刻了解并保持警惕,才是其神圣的使命。与此相对应的例子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书中用激昂的控诉,愤怒的谴责,尖锐的嘲讽,深切的诉说,揭露了俄罗斯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直面罪恶,直指元凶,不仅显示了作家在反思历史时的过人眼光和思想高度,也显示出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道德承担和勇气。因此,它能够带给人以感动和震撼,并将成为文学殿堂永远不朽的名著,而在《兄弟》中,局部细节的煽情描写尽管能催人落泪,却无法让读者警醒并得到思想上的升华。 《兄弟》的写作再次验证了思想高度决定作品高度的正确性,虽然他有自知之明地宣称自己写不出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那样的小说,但是,这决不能成为《兄弟》过于平庸的借口。迷恋暴力和残酷的余华让自己的嗜好在本书中再次得到了体现,他不仅乐此不疲地描写了孙伟父亲的自杀和宋凡平之死,而且让宋凡平死去之后,需要砸断膝盖才能睡进棺材。重要的是,他不是控诉、谴责那种操纵个人的国家暴力和人与人之间相互施加的暴力,而是沉溺于暴力叙事所带来的快感。本末倒置的习惯使余华的写作游戏于联想、编造以及傲慢与偏见(他在一次讲座中声称“文革”那种情形让有些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更亲密),《兄弟》由此成为余华文学创作中最大的失败——除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连贯性之外它乏善可陈,更不必说优秀了。 我希望余华在用全书的上半部《兄弟》(下半部还没出)在与读者开一个玩笑,就像三句半的前三句只是一种铺垫,后半句才是点睛之笔,赋予前半部以另一种生命,焕发出全新的色彩。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本版照片为本报资料 余华主要作品目录 两个人的历史 命中注定 死亡叙述 爱情故事 鲜血梅花 往事与刑罚 祖先一个地主的死 战栗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古典爱情 偶然事件 世事如烟 四月三日事件 一九八六年 难逃劫数 现实一种 河边的错误 夏季台风 活着 在细雨中呼喊 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能否相信自己 许三观卖血记 在细雨中呼喊 图: 作家余华在接受媒体采访。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