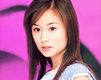[书友]追忆林桦先生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30日10:19 新京报 | ||||
|
编者按 9月1日,78岁的翻译家林桦先生在北京病逝。他溘然辞世后,丹麦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做了报道,然而,国内除了一篇短短数百字的文章外,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位老人的悄然离去。数十年来,林桦先生为翻译和研究安徒生的作品付出了很多心血,在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喧嚣声里,一位中国“安徒生大师”的身后事却是如此寂寞······安徒 生说过:“人生就是一个童话,充满了流浪的艰辛和执著追求的曲折。我的一生居无定所,童话是我流浪一生的阿拉丁神灯1这句话用在他的译者身上,似乎也不为过。本报特约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安徒生文集》编辑、与林桦先生共事长达五载的张福生,回忆与他合作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谨以此纪念林桦先生。
林桦 1927年生于云南,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著有《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等著作,曾获得“布里克森奖”。为表彰他对安徒生作品的翻译、研究工作,以及他对中国和丹麦文化交流的贡献,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他“丹麦国旗骑士勋章”,同时,他还获得了“安徒生特别奖”。
《安徒生文集》(全四卷) 安徒生著 林桦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3月版 定价:150.00元 □张福生 燃尽的蜡烛 8月24日,我去友谊医院看望林桦先生,他当时已经很虚弱,瘦得没了以前的样子。尽管如此,他见到我来了,仍很高兴,我们谈了许久,他几次称赞《安徒生文集》做得很漂亮。林桦的夫人袁青侠告诉我,林桦在医院从头至尾仔细读了一遍文集,非常满意。临告别时,他又抬起手,这对他来说是吃力的,我忙过去又和他握了握手,没想到,这一握竟是永别。几天后,林桦先生静静地走了,像一支燃尽的蜡烛。 从2000年初,我们开始做《安徒生文集》,到2005年2月校订完最后一批通读样,他几乎一天也没有真正地休息过。为了赶在今年4月去丹麦参加纪念安徒生诞辰两百周年之前印出《安徒生文集》,我们“日夜兼程”,连星期六、日都不敢放松,我在办公室他在家,为的是可以随时解决稿子中的问题。做文集是一项繁杂的工程,常常需要当面交换意见。他怕耽误时间,始终坚持亲自来出版社。他家在通州,来一趟至少两个小时,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又胖,坐公交车,其困难可想而知。他老伴不放心,总陪他来。五年里,他到底来了多少趟,我说不准。记得春节前那次来办公室,交待完四卷所有的事后,他如释重负地对我说:“小张,我真觉得很累,医生要我住院,我决定春节后再去。等《安徒生文集》出来后,约上老孙(绳武)和蒋婉(孙绳武老伴),咱们好好庆祝一下,我请客。” 2月6日,袁青侠打来电话,说林桦的胰腺上发现了一个肿块,叮嘱我不要告诉他。3月4日,林桦先生住进了医院。3月7日,《安徒生文集》四卷检查样书送到社里。这期间,我几次去医院看他,他一次比一次消瘦。9月1日,林桦先生就去世了。 林桦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与安徒生神交了大半生,呕心沥血,献出了本该享受人生的晚年。现在,他可以坦然地带着《安徒生文集》微笑着去见安徒生了…… 初识林桦 我与林桦先生初识,是1990年在“丹麦文学研讨会”上。这次会议很重要,因为1989年以后,国内与北欧的文化交流一时遇到了挫折,许多谈好的项目都停滞下来。这次研讨会是重新开始的好兆头,所以从冯至、叶君健,到我们出版社都十分重视。会议休息期间,在东湖宾馆的阳台上,我和林桦先生谈起了丹麦文学。那时他刚离休不久,对译界的事知道得不多,但他对北欧的文化历史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都如数家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0年2月,中国译协举办丹麦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研讨会”,我们再次见面。这次他因翻译布里克森的作品成了主角,在会上做了精彩的发言。很快,2月21日,丹麦的三位学者和金谷出版社的约翰内斯·里斯来访问,林桦先生做翻译。这时,我对林桦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是从此时起,我们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交往。 当时,林桦先生已翻译了安徒生的自传《我的童话人生》大半部分。我很早就知道这本书,我们也有出版几位北欧文学大家传记的计划,所以对他翻译这本书,我很放在心上。为此,我还征求了曾主管外国文学的副总编孙绳武和绿原两位前辈的意见,他们都很赞同。后来,我请孙绳武先生携老伴蒋婉,林桦先生携老伴袁青侠一起吃饭。四位老人都很尽兴,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谈得甚是融洽。饭吃到最后的时候,出现了感人的一幕。林桦对蒋婉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蒋婉也回答说有同感。原来,1953年,林桦先生在丹麦任驻丹麦使馆随员时,曾接待过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北欧的蒋婉。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友重逢,当年的青年已进入耄耋之年,怎能不感慨万千。 外交生涯 安徒生拉近了我与林桦先生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我了解到,林桦先生1927年生于云南昆明,1950年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其后到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1953年到1968年调至外交部,除中间三年回外交部西欧司任职外,两次到驻丹麦使馆工作,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难怪他对丹麦的情况那样熟悉,对我提出的稀奇古怪、犄角旮旯儿的问题他都能脱口而出,据说在丹麦,他还常常被陌生的路人认出。1972年至1975年他又到驻冰岛使馆工作,这期间,几乎跑遍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常到挪威、瑞典、芬兰等地广交朋友。后来他又调到驻泰国使馆,同时兼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副代表。1983年至1988年离休,在驻印度文化处工作了近五年。前后三十余年,他一直在外交事业上,从事中丹、中冰、中泰、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 翻译安徒生 1988年离休后,林桦先生又将其全部精力转到了用笔介绍外国文化方面,在国内外几十家报刊、出版社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翻译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主要作品有《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丹麦驻华大使白慕申的两部著作《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和平与友谊———中丹官方关系》(1674-2000年)以及《丹麦概况》、《丹麦立宪史》、布里克森的《七篇幻想的故事》、《冬天的故事》、冰岛的《埃伊尔萨迦》等。此外,他还撰写了《丹麦文化简史》和《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这两部著作。 1997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为他颁发了“丹麦国旗骑士勋章”,同年4月,丹麦奥登塞市安徒生委员会又授予他“1997年安徒生特别奖”。他还被推举为冰岛冰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荣誉会员和丹麦奥登塞安徒生国际协委会委员。但在我看来,翻译《安徒生文集》四卷,是他对介绍外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搏,这比任何奖项都更沉重,也更具价值。 推出某一作家的文集与介绍某一作家的单本作品有很大不同。主要难度在于,做某一作家文集不仅对这一作家所有的创作,包括日记、书信都要有深入的研究,还要掌握这一作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认识其所处国家的历史及当时的文学状况,将其置于当时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大潮中去。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许多相关的资料,犹如要认识一棵异邦的古树,除了了解其树干、树叶、树根,还要了解它生长的土壤、气候……这对译者的专业知识、翻译能力,甚至生理上的耐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读者看到的是一部《安徒生文集》四卷,但经译者阅览和苦心研究的何止是一个四卷、两个四卷…… 2001年3月16日,来华访问的丹麦文化部长一行由丹麦驻华大使陪同,邀请时任社长的聂震宁等吃饭。席间,我听到了一则故事:有位丹麦学者在安徒生研讨会上,对中国听众说,知道五篇安徒生童话的,请举手。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再问,知道五篇以上的,请举手。有一半人没举。又问,除童话外,知道安徒生其他创作作品的,请举手。几乎没有人再举起手来。这显然符合国内读者对安徒生了解的实际状况,但还是让我非常感慨。 当天,我和林桦先生在饭店门口分手的时候就约定,除原定选收安徒生的自传、小说、诗歌外,还要增加他的戏剧、散文、游记,甚至日记、书信。后来由于时间关系,书信和日记未能收进来。这不能不说是这套文集的遗憾。 尽管林桦先生为翻译《安徒生文集》做了多年的准备,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真的翻译起来,还是遇到了相当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安徒生是位大旅行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种飘忽不定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思想跳跃性很大,让人无法抓住主脉。《在瑞典》是较典型的一篇,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同时,夹叙夹议地讲述了挪威、瑞典、丹麦在君主统治时期的历史,奇思妙想、激情飞扬,加上怪异的形容和超越想象的比喻,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许多难点。大部分问题,林桦先生通过到丹麦访问的机会,咨询有关专家得到了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林桦随时通过电子邮箱,请教丹麦朋友来解决的。我手里留有几封这样的原件。其中一封是满满的两页纸,就十余个问题他请教了两位丹麦学者。最下面有两行字,是林桦先生对我说的:“我希望你能从中体察到我对待疑问的认真;我的翻译很‘硬’,很蹩脚,但不懂就是不懂,我从不装懂,不懂的东西我一定追根到底。” 林桦先生就是凭着这种对问题“一追到底”的认真劲儿,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了五年翻译一百余万字,撰写前言、注释、年表几十余万字的艰苦历程,给国内读者留下了一部认识、欣赏和研究安徒生的优秀范本,使安徒生这位世界级的大作家的形象更加丰满鲜活。 林桦先生一生得到过荣誉,也受到过挫折,但总在匆匆地向前“赶路”,他似乎从未放慢过生命的脚步。 现在,林桦先生,您可以好好休息了。 ■书友反响 周国平的志向 □佚夫 “周国平伪书案”有了新的进展,日前,我从新京报9月27日的新闻中,获悉了周国平起诉书商索赔14万元的消息。笔者对周先生的“较真”持赞赏态度,并对之前其他名家受到同样的冒犯,却选择沉默或者私了的做法感到失望。选择庭外私了无疑是对违法者的姑息,以后再出现“伪书案”也就在所难免。笔者在此除了对周先生打官司表示支持外,更想谈的是自己对周先生作品由喜欢到反感的过程。 初次读周先生的散文是十多年前,好像是在一本杂志上。就像后来出版社宣传的那样,周先生的作品“集哲学与文学于一身,融理性与感情为一体,哲学论著闪着诗性的光华,文学随笔透着哲学的智慧”,一下把喜欢看杂七杂八通俗读物的我给征服了。我成了周先生的粉丝,见到周先生的宏文都要细细品读一番。先后买了《守望的距离》、《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译著《偶像的黄昏》和对话录《自由风格》等,并因此喜欢上了尼采,开始读哲学史著作。但是,在读了几种尼采著作和哲学史之后,再来读我的哲学领路人周先生的散文,却突然觉得兴味索然。像一位音乐家所说的那样,我在读周先生的散文时,也必须不时摘帽行礼。因为周先生不过是位高明的文字加工者罢了,他的散文并没有多少创见。 近年来,周先生的名气越来越大,已经加入到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声直追余秋雨(去年他们先后出版了大受争议的文学自传)。周先生的散文著作再不是“多年积累一本”(《守望的距离》序),而是成套地出版,流行报刊上更是比比皆是。周先生在《自由风格》中对别人称其为哲学家还表示不配,如今已经赫然把哲学家的冠冕戴在头上了。(凭良心讲,中国近现代以来哪有什么哲学家,不过都是一些学哲学的人而已。) 据说,周先生散文的读者多是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这也许是真的。因为,国内的大学生,无论理工农医,还是文史政法,除了必修的教科书外,很少接触西方哲学经典著作。因此,当周先生用文学笔法普及西方哲学时,自然会给哲学知识囿于教科书的“知识分子”们一种新鲜感。比起晦涩难懂的哲学原著,周先生的哲普文章更容易下咽。台湾作家刘墉的哲理散文是中学生的最爱,大学文化程度的人难免会觉得幼稚,看不入眼。周先生的散文正好填补了图书市场上的这一空缺。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国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周先生散文的行情会越来越好。 但是,笔者认为,这样一条名利双收的成功之路,不应该是周先生的最佳选择。记得几年前,有位老学者曾建议周先生不要写什么哲普散文,应该把全部精力用于翻译尼采全集,因为,以周先生的才思文笔,无疑是翻译尼采的最佳人眩为国人留下一部名译,显然要比写那些散文更能传之久远。因此,笔者此文的目的不过是把老先生的旧话重提,希望年届花甲的周先生能把翻译一部尼采全集作为其余生的志向。至于畅销的哲普散文,当作余事好了。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书友]追忆林桦先生](http://image2.sina.com.cn/dy/o/2005-09-30/551e435f964389a87ab0396e3b8711d3.jpg)
![[书友]追忆林桦先生](http://image2.sina.com.cn/dy/o/2005-09-30/e5d2315dbf0740d9565fcb3086f54f8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