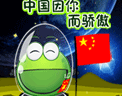家,一切都改变了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02:32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 |
|
○赖武 巴金1987年回到成都时专门去看了双眼井,说:“只要双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 老正通顺街已经“消失” 正通顺街中段巍峨地耸起了几幢相连成排的十八层高楼,称为“东珠美地”,一侧正建着更高的楼房,对面是外观嵌着肉色瓷砖的“战旗剧常”“盛世年华”与“战旗剧潮东侧都是大片已围的空地,长满青草,零星有些大树,如银杏、女贞、皂角树等,显然是原先巴金故居的风水树。空地的四周边缘除了水泥楼,看不见老宅的一砖一瓦,东头接太升北路,两边全是新楼。街也扩宽至十多米,汽车来回飞驰,那原先仅宽几米的幽深的老街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的两个婆婆说,老房子三年前就拆完了。 我最迟是在2003年的正月间来过东珠市。记得当时小巷里的老院子就拆得差不多了,仅中段剩下一个开杂货店的老门斗儿,它的两侧是工地,正建高层楼房,小汽车穿过,扬起浓浓的灰尘,窄巷成了施工通道。以前就听这街上居民说过作家巴金的故居在正通顺街,其后门就开在东珠市街。所谓“珠市”原为猪市,因嫌其脏,巴金祖父李浣云遂拿钱出来建房,渐成街道。又因西头有珠宝街,这里就改称珠市街。可见巴金家对这条街是有功德的。 街上的人说,“最早《家》的电影拍宅院门就在这街上,因为前后门外观都变了,所以就选在东珠市巴金老宅隔壁一家最好的龙门子”(35号),门墩上有石狮子,挑枋、雀替都有雕刻。院子最早的主人是一个姓孙的成都警备司令,后来易主给一个姓谢的知县。 巴金祖屋早就不存了。如今,连祖屋所在的老街也已旧貌换新颜,老街坊们都散去无踪,谁还能在这个城市的这条街站在一个准确的位置上传达一个家族、家庭、家人真实而生动的历史信息? 从太升北路走几步,我便自东向西穿过三百五十多米长的正通顺街。那里几年前就已经没有什么可观的了,除了双眼井,看不出老街的一丁点痕迹。街已扩宽至十多米,两侧全是水泥楼,也有已拦而未建的空地。 西头近百米长的街道已拓宽,来回穿梭的不仅有各式小汽车,从成仁路口到九里堤的106路公交车不时驶过。如果不是西头靠北侧街沿边的双眼井还在,就算老成都人要来看看正通顺街,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印证他们对这条街的记忆,实际上他们认识的这条街已不存在于城市地理中。 双眼井成了巴金的感情支点 从清末的成都城地图上看,正通顺街原叫古佛庵街,因街南有古佛庵而得名。其实这条街上还有福音堂(街南),大仙祠(街北)、云南会馆(街北)等。往西穿过一百多米长的北东街就进入北大街,往北再跨过珠市街就直抵北门城门洞,东南与其它街相连,故后来称“通顺”街也说得过去。 成都很多街道以寺观名称之,如这儿与古佛庵挨着的就有新开寺、玉泉寺、火神庙、灶君庙、小关庙、兴禅寺等。这些寺庙废了后,街名在,后人还晓得街上曾有过什么寺庙宫观。然而“古佛庵”街名一变,“庵”再不存,后人就很难把这条街与这庵联系起来了。 街北侧尚有英国领事馆(据说原是清末驻藏大臣风荃的公馆),加上福音堂,在清末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环境之中,这条街的西方色彩很浓。当时福音堂建的还是“华式房屋”。这里成了当时西方人来成都主要居留的街道之一。北邻的东珠市街又是当时德国领事行馆之所在。这种地方西洋人活动较为集中的氛围有可能对生长于此的童年巴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他16岁进成都外语学校、19岁毅然决然地离开封建家庭并跟着又走出国门的一个因素。 建国后一些单位进来,一些祠庙废掉,当一些老宅易主又改建,铺面多过门斗儿,当水泥楼替代穿斗房,街道扩宽,车马喧阗而成闹市,人们才惊叹这变化太快,仿佛是没有任何过渡,一下子,过去的印象就遥远了、淡了。 市人摆正通顺街的老龙门阵,提得起来的,确凿无疑的无非两样:双眼井、作家巴金的故居。一者还在,一者虽迹不存却名满天下,成了本街至今广被认同的历史坐标。 曾有街上老人说现存正通顺街西头双眼井为原新开寺内古井。新开寺是唐宋时所建城内大庙子,直到清末尚有遗迹。不过,寺庙的规模可能经街市的变化而逐渐缩小,以至于原先属于寺内的水井后来竟分离于寺外而暴露街边。成都虽有“二江环抱”,城内也多分布河溪池塘,但市井百姓洗用之水却多依赖院内、街上的水井。清末统计成都城街道五百一十六条,而水井就有二千五百一十五眼,可见除了街巷外有水井,院坝里也通常有水井。那些著名的街上水井,在清代的城街地图上都标示了出来,如正通顺街上的双眼井就单独标了出来。 巴金1987年回成都老家,专门去看了双眼井,说了一句话:“只要双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这仿佛在说双眼井可以涵盖巴金所有童年的记忆。双眼井成了作家对正通顺街对故里全部感情的支点。据说,巴金家老院里原有五眼水井。或者因为老宅早就易主,解放后又渐改渐毁,旧物不存。 大约五六年前,正通顺街西头南侧尚有老院子时,我经过双眼井。那里与我八十年代所见水井贴着墙根窄窄的街沿上的情形不同,井旁修了楼房,一侧有巷道,水井后面是楼前小坝子,井边立了碑,筑了石栏,又加了石井盖。这是老街在拆时对水井的保护。井盖上还拴了铁链子,不晓得里面还有没有水。那时成都很多水井都枯竭了,或者填塞了,找不到踪迹了。所以,双眼井的存在,是正通顺街的幸事。 正巧遇上一个就在双眼井边楼底开影屋的朋友,他说,这一带拆得凶,他以一角一匹的价格买了上百块城墙砖,把双眼井到他影楼的空地上铺了一层,其余在一侧靠墙处垒砌了个花台。我一看果然是这样。“这些老城墙砖,扔了,很可惜。以后政府要重建城墙,我再捐出来。”他说。 消磨了巴金童年的居所 巴金写出蜚声海内的长篇小说《家》后,否认这是以他自己家庭为蓝本写的自传,称写《家》不过是要反抗他生长于旧家庭的“不公平的命运。”“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了一个可怕的黑暗,我没有一点留恋。”但小说出版后没几年(1937年),他就承认所谓“没有一点留恋”是不可能的,“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我的<家>》)。 他说在开初构思《家》的小说结构时,最先浮现在脑里的,就是他曾经“熟悉的面庞,”那许多“不能够忘记的事情,”还有那些“消磨了我的童年的地方”。“我的眼睛把那些人物,那些事情,那些地方连接起来成了一本历史。”可见巴金是把自己幼年所生长居住过的这条街和这个家的情感深藏于小说字里行间的。 在巴金离家几年后的1927年,正通顺街上的李家故宅就易了主。据说先是一个四川军阀的军需处长,接着是一个国民党保安处长。“门前还有武装的兵在守卫,”这大概就是解放后老宅被川西军区接管的直接原因之一。从那时至今,“李宅”一直是军产。1958年,毗邻的西院张家同李家东院打通合并。西院当时为军区歌舞团驻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修战旗文工团职工宿舍,老宅相继被改造。但至迟在70年代初,李宅院落的格局尚在,老房子也不乏一些可欣赏的细节,过来人于破败中仍能嗅到旧世人生的气味。但很快,随着经济建设和旧城改造步伐的加快,到80年代李家故宅旧貌已荡然无存,除了半堵残存的东墙和一株已枯的桂树。 随着离乡时间渐久及年岁渐长,还因为写《家》用心之太深太苦,巴金是愈来愈恋成都的老宅。他去乡的八十多年间,仅有几次踏上故土的机会。就像他创作《家》时,头脑里最先浮现的是“消磨了我童年的地方”一样,提起小说《家》时,他也情不自禁地说到坐落在正通顺街的家。 “我离开成都十多年没有回过家。我不知道那里还留着什么样的景象。”他还记得自家院里“那个小池塘也因为我四岁时候失脚跌入的缘故被祖父叫人填塞了。代替它的是一些方砖,上面长满了青苔。旁边种着桂树和茶花。秋天,经过一夜的风雨,金沙和银粒似的盛开的桂花铺满了一地。那馥郁的甜香随着微风一股一股地扑进我们的书房。窗外便是花园……春天花开繁了,整朵地落在地上,我们下午放学出来就去拾起它们。那柔嫩的花瓣跟着手指头一一地散落了。我们就用这些花瓣在方砖上堆砌了许多‘春’字……这些也已经成了捕捉不回来的飞去的梦景了”(《关于<家>》)。 1941年1月,巴金在离家18年以后首次回到成都,呆了五十天。后来他到重庆写了《爱尔克的灯光》,不是靠记忆,而是实录所见故居的现状及内心的感受。“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就在那时,故宅已经变化了,而且“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巴金第一次回故里就已经不能再进那个滋生着他童年梦境的老院子了。从那时直到今天,恐怕那座老宅旧址上唯一没变的就是卫兵把门。 深藏在内心中的老街 解放后,巴金终于可以进那座门楣上写有新主人名字“黎阁”的老院坝了,“‘黎阁’依然,而那个作威作福的主人已经完蛋。”20世纪的60年代初,回蓉看故居的印象是老院坝“又干净,又简单,又大方的西式大门使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门墙上钉着‘战旗文工团’的牌子,我看见这个新的景象……” 1987年10月,巴金最后一次回蓉,故居已然大变,八十多岁的老人只能回忆老宅的一切。他从出生到辞亲远游,除掉其间跟父亲赴广元任的两年,总共只在故居生活了17年,而陪同他的参观者中有住此达几十年之久的文工团军人,对老宅的熟悉程度比巴金更甚。而巴金仍能指出把西邻张家院子当成李家院子是张冠李戴。可见,由于老宅拆毁,人事已非,巴金故居的确切位置及其格局渐已模糊。今人提及巴金故居,都无一例外地说就是98号战旗文工团里,那种笼统而公私纠缠的含混词语里不仅缺乏老宅归属的确定性,还总像隐含着什么别的意思。 原战旗歌舞团的张耀棠根据自己的考证、调查,绘制出了巴金故居复原图;后来有关方面还做出巴金故居模型在巴金百年诞辰时送给再也不能回成都的老寿星。这种平面的或立体的巴金故居图形自是可以聊以慰籍那些从来就没有机会对大作家旧居瞟上一眼的人的怅惘之情。 1985年,四川有关方面提出恢复巴金故居,省上也批了,但巴金晓得后于1986年10月三次写信反对此事,说要搞纪念,可以在旧址上钉个牌子,写上“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坚决表示“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到巴金百年诞辰时,又有人提出重修故居,更有人提议把正通顺街改名为“巴金街”,理由之一就是以大文豪的故居塑造成都的城市文化形象,所谓“增添一张城市名片”。 巴金1941年回成都看到的照壁上“长宜子孙”那四个字时说,“该是我祖父留下的东西罢。……他用空空两手造就了一份家业,到临死还周到地为儿孙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但巴金晓得财富并不“长宜子孙”,这“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的大家也并没有守住正通顺街的老宅。它几易其主,后又从私产变为公产。家庭的盛衰、社会的变迁,整个老城整条老街都渐次改头换面,一院落安能幸存?重建故居又岂能替代历史遗迹? 六十多年前,那时祖屋还在,巴金剖白自己的情感:“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1983年巴金仍然感叹:“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的足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愿化作泥土》)。这种身处异乡而对故里、对童年的足迹的寻觅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那一切在如梦飞逝之后更为强烈。对于已没有一幢老房子的正通顺街,所有离去与仍在的老住户,多少年后都会同巴金一样地去寻觅内心深藏的这条街,这大概就是一条老街所有遗迹消失殆尽后很重的情感分量。 现在,巴金故居的旧址上并没有巴金在19年前就提议过的故居牌子,倒是街西头“巴室茗品”茶楼及双眼井旁一家“巴井乡肺片”勉强让人们能联想到这里还有巴金家的影子。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