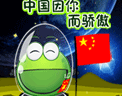巴金与俄罗斯的文学情结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0日21:26 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
|
高莽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的情结持续了整整一生。在他踏上文学道路的初期,在他创作旺盛的日子里,在他困惑的岁月以及在他体衰力弱的晚年,都无时无刻不对俄罗斯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在俄罗斯文学中探索过人生的道路,从俄罗斯作家身上汲取过力量,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借鉴过写作的技巧。 1980年巴金在《文学生活50年》的讲话中,说他是在法国学会写小说的。他历数了几位法国作家,称他们为自己的老师。同时他又说,除了法国老师之外,还有英国老师、日本老师和俄国老师。 俄国老师中他提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1812—1870)、自由派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1828—1910)和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1868—1936)。这是几位思想意识并不相同的人物,但巴金却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细读巴金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对他创作生涯发生过影响的远不止上述四位。他还提及过雷列耶夫(1795—1826)、普希金(1799—1837)、果戈理(1809—1952)、冈察罗夫(1812—1891)、涅克拉索夫(1821—1878)、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琴斯基(1851—1895)、迦尔洵(1855—1888)、契诃夫(1860—1904)等人。另外,还有克鲁泡特金(1842—1921)、薇拉·妃格念尔(1852—1942)和爱玛·高德曼(1869—1940)。后三人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他们的自传和文章对青少年时代的巴金影响甚大。 新中国成立初年,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后来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以至破裂,这期间巴金仍然殷殷关注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1957年9月27日他回答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提问时,复信中说:“旧俄作家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后来也喜欢高尔基与契诃夫。我还喜欢过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巴绥夫的一部分作品(鲁迅和郑振铎翻译的)。”谈到苏联作家时,他写道:“我最喜欢的是肖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费定。”他注意收集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插图本。他托人为自己或为朋友代买过爱伦堡的《大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田德利亚科夫的小说《死结》、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等。说明他对变化中的俄罗斯文学一直十分关注。1964年1月18日巴金日记里有一段记载:“午睡一刻钟,一点后动身去儿童艺术剧场看苏联影片《士兵之歌》和《晴朗的天空》。”记得1992年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看望巴老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苏联文学艺术的近况。 巴金翻译过不少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处女地》、高尔基早期描写草原上的人们生活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斯捷普尼亚克的《地下的俄罗斯》、迦尔洵的《信号》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等。 巴金一再表示,他从事翻译是为了学习。他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了人道主义精神、爱人民的思想、反对封建的斗志、对被压迫受侮辱的人们的同情、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学到如何把感情化为文字。 最喜欢的一部书 巴金说过,他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和回忆录,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这与他当时的向往与苦闷有关。他厌恶封建大家庭,渴望自由生活,于是便博览各种书籍排解烦恼,寻找出路。他在困惑的时期,得到一本小册子——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这本小册子完全攫住了茫茫不知去向的少年的心。“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巴金1936年在《我的幼年》一文中提及这本小册子时写道:“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巴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上,每夜拿出来阅读。“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1928年,巴金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1930年他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又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七年以后巴金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又名《一个反抗者的话》,有人译为《告少年》)。 巴金在他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一书的代序中,建议青年读者要熟读它,要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因为它是“青年们的福音”。巴金介绍书的作者,说“著者把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又说,克鲁泡特金“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我们从巴金的代序中还可以感受到他是何等地热爱这个安那其主义者,爱他的人品与思想。“帮助别人,牺牲自己”成为青年时代巴金追求的目的。 《我的自传》只是克鲁泡特金的前半生的生活记录,从1842年写到1886年,这里还没有包含他生活的最重要时期。其实他那多灾多难、灿烂辉煌的后半生的基础,远在1886年以前已经确定了。 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是一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史。 1933年,《我的自传》译本再版时,巴金增加了15幅他从外国搜集到的插图。巴金对再版这部书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巴金认为《我的自传》是他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他的“影响极大”。这部书的理念和奋斗精神为巴金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也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事业。 跟随着“自由”的旗帜 巴金是小说家,是翻译家,主要翻译小说。但他青年时代还写过诗和译过诗。1922年,巴金18岁在郑振铎编的《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报》上发表过十二首短诗,以后又写过《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眼泪了》和《上海进行曲》等。 他译的诗歌有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美国的。他译的诗不多,但富有叛逆精神,和他当时的思想倾向相一致。 巴金24岁时译了两首歌颂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斯特潘·拉辛的民歌:《伏尔加的岩石上》和《伏尔加伏尔加》。 …… “我将牺牲一切而毫无怨言, 我愿把头颅奉献给自由之祭坛。” 司特潘的有力的声音 响彻了伏尔加的四岸。 …… 他译的普希金的诗只有一首,即《寄西伯利亚的音信》。这首诗代表了普希金的性格,表达了诗人对革命者们的同情,也倾诉了译者的胸怀。 写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是1825年的12月14日,俄国一部分有知识的激进分子为争自由,拒绝参加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誓典礼,在圣彼得堡圣伊萨基辅大教堂广场实行军事政变,企图建立共和国政府。他们的行动缺乏广大民众的支持,政变事败。佩斯捷尔上校、诗人雷列耶夫等五位领袖被处以绞刑,其余的121人被判处服劳役,流放到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他们在冰天雪地上的生活感动了不少的人。诗人普希金为他们献上这首诗: 在西伯利亚矿坑深处, 你们骄傲地忍耐着; 那艰苦的工役不会成为徒然, 叛逆的思想永远顽强地存在。 一声呼喊,狱墙便会崩颓, 粗重的镣铐也将落自你们的身; “自由”将堂皇地迎接你们。 你们的弟兄也会送还你们的军刀。 …… 普希金请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穆拉维约娃将这首诗带往西伯利亚。过了不久,十二月党人奥多耶夫斯基以流放西伯利亚的囚徒的名义,同样用诗回答了普希金,表明他们虽然深陷囹圄,但并没有屈服。《答普希金一首》也是巴金译的: …… 但是,朋友啊,请不要怀疑我们, 我们要骄傲地负着那恼人的铁链——我们的命运; 铁格子关不住我们的深邃的心, 在现今我们还敢侮辱那盛怒的暴君。 我们的艰苦的工作决不会成为徒然, 从这火光里将冒出一股强烈的火焰, 我们的人民也将从睡梦中惊醒, 跟随着“自由”的旗帜,不怕长夜漫漫。 …… 巴金说那些诗是“血和泪的结晶”,他曾被它们感动过,“希望别人也受到它们的感动”。 巴金当时翻译这些诗时虽然不是根据原文,但他的译文却强烈地反映出原作的精神。巴金自认为译文“十分恶劣”,可是今天我们诵读时仍感到气势磅礴。 雷列耶夫是俄国十二月党人诗人、1825年2月14日起义的领导人。他的作品有抒情诗、历史诗、长诗等。他的诗充满俄罗斯浪漫主义所特有的政治联想。 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书名就来自雷列耶夫的长诗《纳里瓦依科》。当年巴金将雷列耶夫的长诗的几句译成汉文,印在小说的扉页上,表达了他愿像长诗中的人物一样,献身革命的决心。雷列耶夫在诗中说“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雷列耶夫本人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巴金称赞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 巴金说:“《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 言行一致 巴金一生都与列夫·托尔斯泰维系着精神的交往。他研究过这位俄罗斯伟大文学家的生平,倾心阅读过他的小说,撰写过他的传记,几十年间多次在文章中回忆他阅读《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时心灵所经受的震撼和感动。 早在1921年巴金17岁时,他就在自己的家里与朋友们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平民之声》,从第4期起该刊便开始连载他写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 1928年巴金在巴黎时,应胡愈之之邀为《东方杂志》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从法文转译了托洛茨基有关这位俄罗斯文豪的文章。 1931年4月巴金发表《家》时,在总序中开头便写道: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他对这句话又予以否定,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肯定与否定之中展示了巴金当时的思想的演变。这种演变贯穿了巴金的全部创作。 1935年巴金在日本时,广读各种书籍,说“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过了50年,他还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一些情节。 早在20世纪50年代,巴金从法文转译了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托尔斯泰和他夫人的矛盾、他的家庭悲剧,有个时期成了社会热门话题,包括我国在内。托尔斯泰身为贵族,有庞大的庄园,有一大堆儿女,还有不少食客。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很不容易。托尔斯泰夫人是位相当能干的女人,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料托尔斯泰和管理家务上。她崇拜托尔斯泰,为托尔斯泰抄过七次《战争与和平》的稿子。托尔斯泰到了晚年厌恶贵族生活,要改变生活方式,几次想离家出走。托尔斯泰身上充满矛盾,他在艺术上成就越高、名气越大,就越想做到言行一致。他放弃了文学创作,一心为农民编纂课本;平日也穿起粗布衣服,常为贫民去耕田。然而,全部家务事都压在夫人的肩上。托尔斯泰夫人有苦无处申诉。巴金认为高尔基在文章中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话”。 不管怎么说,托尔斯泰正像巴金所说,是“十九世纪文学的高峰”,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1984年巴金在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托尔斯泰的道德力量影响着巴金。 1985年,巴金81岁了。有一天老人在《读者良友》杂志(第二卷一期)上读到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作者以揭示托尔斯泰私生活秘密为名,实际上是在伟大死者的脸上抹黑。巴金读后异常气愤,觉得作者活脱脱用的是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腔调。他认为必须予以反驳,维护大文豪的尊严。他也写了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但在标题上加了一个问号,以示与原作者针锋相对。巴金说:“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又说:“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讲真话,照自己说的做,却引起那么多的纠纷,招来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终没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了。” 巴金理解托翁为矛盾的思想所苦,知道他与妻子与信徒们的关系的复杂性,看到他晚年如何否定艺术,但巴金坚定地认为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说“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托尔斯泰年轻时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 巴金说“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可是巴金认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一生最后的工作 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被巴金视为是他“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尔岑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政论家和出色的作家。他30岁流亡国外,长期生活在西欧,死后安葬于法国尼斯。 巴金清清楚楚记得他初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时,书中的人与事使他如何激动,如何亢奋。他说:“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通过纸和笔化成一行、一段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 几年后,巴金撰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时,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赫尔岑:赫尔岑的家庭、他的学历、他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流亡国外,创办《北极星》和《警钟》杂志,他与俄国的巴枯宁、法国的蒲鲁东、意大利的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交往,他的家庭悲剧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巴金后来翻译《往事与随想》作了铺垫。 1936年,巴金翻译了赫尔岑回忆录中的两个片段《海》与《死》。他还向鲁迅表示过要翻译这部100多万字的巨著。 1940年,巴金又译出回忆录中的第一部分(1848-1852),并以《一个家庭的戏剧》为名,于同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欣赏赫尔岑的文笔,说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说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 巴金在上世纪40年代初写的一些散文,如《雨》、《火》等中不止一次引证赫尔岑的话。巴金时断时续在翻译赫尔岑这部巨著的一些章节。 “文革”后期,1974年,70岁的老人再次拿起笔来,每天翻译几百字,一边翻译一边作详细的注释。他把翻译《往事与随想》看成是一种学习,“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又说,“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1975年2月巴金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一百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译完,即使不能印出也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他写道:“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19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 1977年3月巴金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赫尔岑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写得很出色,值得学习。“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这块牌子,也无怨言。现在认真学习,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又能多活几年,有机会再拿起笔给‘四人帮’画个像,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 我想,赫尔岑的回忆录不仅在文体方面给予巴金诸多益处,而且“文革”期间在精神方面也给予这位受尽凌辱的老人以力量、以希望、以信念,增强了他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他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经历时,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1977年他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第一册包含原作中的前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和《监狱与流放》。 巴金年龄越来越大,体力越差,疾病缠身,写字困难,精力也不够。他只译了《往事与随想》的五分之一,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而感到遗憾。这时,我国有两位翻译家主动愿意帮助巴金完成他的译著,一位是臧仲伦,另一位是项星耀。臧仲伦帮助巴金校对了他的全部译文。项星耀则把这部巨著全部译出。1993年年终,90岁高龄的巴金写信给项星耀说:“在这个金钱重于一切、金钱万能的时代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他感谢这位译者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其书名即来自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金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 影响与联想 巴金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多次提及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对他从事创作的影响。除了前边讲过的几位俄罗斯作家之外,还有作家斯捷普尼雅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斯捷普尼雅克是19世纪善于揭示人的心理的作家。巴金翻译的他的《地下俄罗斯》是一部人物特写集,其中写到几位在国内遭受迫害的人,还有几位流亡国外的人。当时这些人的牺牲精神、为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非常合乎他的思想要求。 事过几十年后,到了1961年,巴金谈及当年翻译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俄罗斯》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时说,这两本书不像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那样难以解释,“书中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倒适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译时一再揣摩,体会,无意间受到了一些影响。”正是这些“影响”促成巴金一部又一部大作的问世,促成他作为大作家的成长。同样,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也使他非常欣赏。巴金说读了他的“充满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并说他的小说《灭亡》里,“斯捷普尼亚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不是一类的人。” 巴金在《随想录》中一再反思自己在十年浩劫期间的表现,检查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竟会自残自罚、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有时,他的思想就会联想到经过炼狱的俄罗斯作家们。 1981年,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那段惨不忍睹的经历时,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己当时已在“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造反派”看来,是“反动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巴金,引导巴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巴金沉痛地说:“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上一世纪80年代巴金在法国访问时,有人向他提问:他的作品中是不是有一种提倡受苦的哲学?巴金回答:“我写作品是反映生活,作品里并没有什么哲学,我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的作家。”在这里他又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明确划分了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界限。 巴金的作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拷问心灵的作品有一定的区别,但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确实讲过“痛苦是我的力量、我的骄傲”一类的话,如小说《里娜的日记》。巴金明确提出:“我并不提倡为受苦而受苦,我不认为痛苦可以使人净化,我反对禁欲主义者的苦刑,不赞成自找苦吃。可是我主张为了革命、为了理想、为了崇高的目的,不怕受苦,甚至甘愿受苦,在那种时候,痛苦就是力量,痛苦就是骄傲!’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哲学。” 1985年1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文学界出现了新的变化。巴金更多地在考虑“创作自由”的问题。这时他又想起了俄国,想起19世纪的俄国作家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创作的。他想到诗人涅克拉索夫临终前在病床上诉苦的情景,说涅克拉索夫开始发表作品就遭到检察官的任意删削,当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巴金说,他记不清楚涅克拉索夫的原话,可是“《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涅克拉索夫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同情城市下层平民、劳苦农民和妇女的遭遇。他先后主持过当时进步刊物《现代人》和《祖国纪事》。1848年法国大革命吓坏了俄国当局,沙皇政府于是按照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成立了专门审查进步刊物的委员会。《现代人》的出版一年比一年困难,但涅克拉索夫没有屈服,后来办《祖国纪事》时,他仍然同审查机关进行不懈的斗争。巴金说:“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没有自由,更不用说‘创作自由’了。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许多光辉的名字都是从荆棘丛中,羊肠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 巴金赞扬涅克拉索夫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深深感受到创作自由来之不易。同时巴金又提及托尔斯泰,说他的三大长篇和最后一部《复活》都是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没有出过一种未经删节的本子。” 巴金语重心长地说:“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又说:“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 巴金期盼我国作家们,特别是中青年作家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勤奋创作,以使我国的文学园林百花盛开。 巴金文学生涯的开始,他的第一部小说的篇名《灭亡》即取自俄罗斯革命诗人雷列耶夫的诗句。巴金老年撰写《随想录》,其书名又是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启发。巴老100年的漫长生涯中一直和俄罗斯文学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俄罗斯优秀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