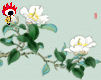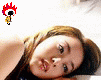| 真水无香:从自发的情感到理性的摄影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08日15:22 中国“幸福工程”组委会 | |||||||||
|
——评于全兴的《母亲》 孙京涛 于全兴是揣着一颗赤子之心西行的。
于全兴西行的目标,是那些他从未谋面、却牵肠挂肚日久的贫困母亲们。他希望他的照片能够帮助“幸福工程”组委会,为那些承担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本的母亲们筹措到更多的资金。行前,自己的母亲细细地捏出的那些送行的饺子,让这条一米八几的长大汉子心灵中最柔软的部位一阵阵抽搐。他愈加感到此行目标的崇高与责任的重大。 西部迥异于东部的大城市——那里山峦纵横,那里朔风长啸,那里贫瘠苍茫……于全兴早就估计到了西行的凶险——在其后的采访中,他也确实遇到了他想象得出的和想象不出的凶险。可是他还是铁定了心要走,他强烈感觉到自己该用这次采访来报答母亲——现实中的母亲以及他胸中虚拟的那个精神上的母亲。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很难体味于全兴的这种情感。对于一个很小就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来说,母亲那双瘦削的肩膀是他唯一的依靠。在那些并不从容的岁月里,活着的艰辛经常让他们母子凄然而无助,他们甚至不知道生活的风帆最终会飘向哪里。全兴说,在父亲刚刚去世的那几年里,没有文化的母亲只能靠糊纸盒、加工外活来养活她的几个儿女。十几岁的全兴聪慧而敏感,为了能帮母亲一把,他去学刻剪纸,在春节来临之际挨家挨户地卖。在凛冽的寒风中,当人们满怀同情地将几分、几毛钱塞进他那红肿的小手中的时候,他真实地感觉到了能帮助母亲分担生活重负的欢欣。 他想重新体味这种欢欣。 对过去艰辛生活的咀嚼、对日渐老迈的母亲的依恋、对为人夫、为人父苦辣酸甜的品味,在他的心底下层层积奠,并发酵成为一种强烈的、要为女性做点什么的冲动。而大都市那种灯红酒绿却不免虚假、物质丰富却不免矫枉的生活更加促使他要为自己的情感找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出口。我想,除了幸福工程国家组委会的委托,于全兴的这种情感冲动和心理动机,是他有勇气在放弃摄影六七年之后又重新拿起相机最强大的驱动力,也是他义无反顾地奔向西部真切地面对那些不幸母亲最充分的理由。从这个角度上说,《母亲》这组照片,是于全兴理解“母亲”这个字眼的形象化体现,是他对母亲特殊情感的一次集中释放。 于全兴急切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采访,就像一直困在笼中日久的鸟儿冲向神圣的天空一样冲了出去。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那种重获自由的快感,他将要面对的,是母亲岣嵝的腰身、孩子们菜色的小脸、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路上可能遇见的危险、无奈以及心灵上的刺痛。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一个几年前就有过的愿望,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但忽然间,我的心底却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茫然。就像一个渴望远行的人,打点行囊即将出发,却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路途”。在这种心境下出发的于全兴,很快就被他面前的景象搞得方寸大乱。他不敢相信这样恶劣的地方还会有人,更不相信她们活得那么艰难。他忘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只顾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送给那些被他的眼泪弄得手足无措的母亲们。他甚至把相机搁置一边,颠簸上百公里带一个生病的小姑娘去看病…… 临行前,我曾特意嘱咐他:不要给那些母亲钱物。这种近乎冷酷的告诫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纪实摄影真正的价值,在于用充分有效的图像告知人们真相,召唤全社会的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个人的怜悯行为微不足道;第二,一旦摄影师和被摄对象之间发生了金钱关系,摄影师往往要面对不期然而来的“以钱买照”的指责。况且,在一种贫困的环境中,金钱足以改变摄影者和被摄者之间的权力秩序,最后出来的照片,往往让人将信将疑。 但是我知道这种劝告根本无效——仗义豪侠、从心而动才是全兴的本我。当他结束了近一个月的采访返回来的时候,除了满脸的疲惫,就是些思绪散乱、肤浅表面、拍摄手法不一、甚至连曝光都不准确的照片。无论作为一个摄影师、还是图片编辑,我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从于全兴真切的眼神、滔滔不绝的诉说和时常哽咽的语调中,我分明感受到,他送给母亲的钱物不是施舍,他也没有想用金钱开路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真诚,准会为他的图像铺就一层温暖厚实的底色,这种底色很快就会在他以后的照片中显影出来。 第一次不算成功的采访令人沮丧,但于全兴在整个采访中的行为却再一次提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心性冷漠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纪实摄影师。19世纪末,尤金·阿切特因为对老巴黎深情的依恋,用相机忠诚描摹了那些被风霜雪雨、和煦的阳光触摸了几百年的老房子、老门廊、老雕塑、老街道;奥古斯特·桑德不畏纳粹的淫威,不屈不挠的拍摄德国人的面孔,是因为他对同胞深沉的爱;戴安·阿勃斯迷恋于那些社会边缘人,是因为她认定他们是经受了生活特殊考验的“贵族”;尤金·史密斯是含着眼泪、颤抖着双手拍下“母亲为智子洗浴”这张不朽名作,是为了替水俣的村民们讨还一个公道;即使那个浪子一般的罗伯特·弗兰克,在解释他拍摄尖刻辛辣的《美国人》的动机时也认为“批评可以出自爱”…… 可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师,要拿出真正可以彪炳于世的伟大作品,仅有自发的、朴素的爱以及发自个人的感情冲动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从不接受表面现象开始的。 在众多朋友们的帮助下,于全兴随即进行了细致的案头工作和深刻的反省。而促使他变感情为理性、变躁动为沉稳、变貌似客观的事件记录为带有象征性的静态肖像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重新审视作为幸福工程国家组委会聘用摄影师的责任与价值。 历史上,由国际机构和社会团体聘用摄影师进行的纪实摄影工程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刘易斯·海因担任美国国家童工委员会专职摄影师期间,他所拍摄的那些在棉纺厂、煤矿、农田中劳作的孩子们的照片促使美国立法宣布使用童工为非法;FSA的摄影家们在罗伊·斯特莱克的组织下为美国广大农村所做的纪实,有效地帮助了政府应对大萧条对农民造成的沉重打击;解海龙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拍摄的“希望工程”,解决了成千上万失学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对纪实摄影师而言,类似这样的成就每个人都梦寐以求,于全兴也不例外。而最为重要的是,前辈摄影师在采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责任感也提示于全兴必须把他摄影的目标,与聘用他的组织的目标统一起来。因为正是有了这种责任感,摄影师对被摄对象的情感流注,才不是那种排山倒海式的,而是如冰山溶雪一般细流涓涓而又连绵不绝;才不是剑拔弩张式的,却如绵里裹针沉实有力——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有社会影响力的照片。 于全兴这次摄影计划源起于他1996年4月参加的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策划的一场大型公益活动。这个挂靠在国家计生委下的公益组织成立的初衷,就是帮助那些因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缺乏男性劳动力的家庭尽可能富裕起来,救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窘迫的母亲,救助方式是提供小额贷款、提高母亲的自救能力。如刘树勇所言,这种发乎日常人伦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久违了的国人的慈悲和歉意”。而于全兴个人的体悟与幸福工程组委会的情感取向产生了强烈共鸣。作为《家庭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会报)的记者,于全兴有条件加入到这项富有人情味的工作中。而这个组织成立的价值观以及七年来所秉承的不事张扬、扎实而富有建设性的工作态度,同样启发于全兴要把他的个人情感和情绪,蜕转为与“幸福工程”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摄影行为和表述方法。 二、如何评价“贫困母亲”这组人群。 在我们的视觉记忆中,大凡与母亲有关的摄影形象,都洋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多萝西亚·兰格的《季节工母亲》、大卫·伯内特的《柬埔寨难民》、沃纳·比肖夫的《印度干旱》、罗伯特·卡帕的《沙尔街上示众的卖国贼,法国,1944》、德米特里·巴特曼茨的《悲伤》、亚历山大·罗钦可的《我的母亲》……在我们这个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世界上,对女性的不公是由来日久的,我们的艺术也抒发了太多的对女性不辨真假的怜悯与同情。而作为以奉献为“高尚美德”的母亲,她们的弱势地位似乎理所当然而又不可动摇。在任何的时局动荡中——哪怕只是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她们都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母亲”这个字眼天然的孪生姐妹。 然而太多的悲剧会让人丧失希望、看不到光亮。 站在于全兴面前的这些挣扎在贫困中的女人、这些被疾病困扰的女人、这些因为没有文化而在心灵深处没有一点星光的女人、这些在苍凉的天地间单薄而渺小的女人,真的需要摄影师以一种怜悯的目光看待他们吗?这些承担了国家改革的成本、这些不温不火却坚强地承担着命运的苦难的女人、这些仍然秉承着相夫教子古训的女人、这些天然而美丽的女人不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爱吗?这样的思考可能又落入了滥情的、概念化的人文主义圈套之中,但是,当思考是以真诚的个人体验为出发点的时候,它的可信度也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在于全兴随后用方画幅拍摄的照片中,每一个女性的可敬与可爱,很自然、很单纯地流淌出来。当人们与那一双双温文尔雅的眼神相遇时,你会真实地感觉到,你向她们伸出的援手,是双向的帮助,而不是单向的施与——在同一个苍穹下,人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这些女人在精神上和人生体验上可能比我们富足得多。 三,该如何为这个人群“造相”? 摄影的目的在于保留事实和揭示真相。但是,摄影的特征却决定了它对事实的掩盖多于揭示。就“贫困母亲”这个现象而言,它背后牵扯的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自然地理的、观念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以摄影先天不足的叙事功能,要揭示这些纠扯不清的问题显然力不从心。通常的情况是,当你很认真地述说了一个母亲的生活故事时,其他人的状况与这个母亲却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当你很完整地记录了一个母亲当下的生存状况时,你却不可能记录她的过去或未来及其背后的动因。实际上这样两难的问题是对纪实摄影师持久的困扰,而如何解决这样的困扰正是摄影师创作能力的考验。 于全兴很聪明地选择了拍摄现场肖像,而把叙述和揭示的位置让给了长于此道的文字。这些肖像虽然名姓齐全,但是它却超越了个体而成为“贫困母亲”群体的一部分、超越了具体形象而成为一种抽象的象征。这种超越最后的结果是,它提醒了人们有这样一些人存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存在——由于不是个别的、个体的存在,它的社会性就显现了出来。它的画外音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应该携起手来,群策群力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正是纪实摄影“以一个社会学目的为目的”的真正价值。 全兴差不多想清楚了,他又走了。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带回了这样一些照片。这些照片让我们想起玛丽琳·科菲的一句话:有激情的思想才有力量。 2002年10月 济南 相关专题:中国“幸福工程”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幸福工程”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