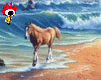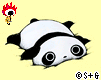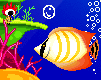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现代都市的角落里 卖花女孩童年被涂改(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06日06:31 重庆经济报 | |||||||||
 拖一身疲惫回到棒棒公寓  女孩在收拾当天未卖完的玫瑰花 -9个孩子,被9个大人操纵,组成一个“家庭” -孩子们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卖花 -每天15支任务,卖花姑娘不惜下跪
-“爸爸”用着带有摄像头的高级手机 两张床,两把电扇,五个桶,五支花,一间脏屋子,中午,昏睡。 卖花姑娘高庆红被殴昏迷之事经媒体曝光后(详见本报3日报道),这些从外地流落入渝的女童们再次引起市民关注。她们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昨日中午,在确信其“父母”出去“解决问题”之后,记者几经曲折来到了王家坡棒棒公寓,找到了11岁的高庆红。 卖花养活“爸妈” 虽然已是中午,高庆红还是睡眼惺忪。紊乱的生物钟和连日卧床让她看上去极其疲惫。混乱的房间里,飘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发了霉。 高庆红脸上有块擦伤的疤,但她主要的伤在屁股,走动起来很不自然。 “你们有几个孩子住在这里?”记者问。 “9个,那个是我弟弟,10岁了。”她指着另一张床上酣睡的小男孩说。 “是你亲弟弟吗?这里有几个大人?” “是我亲弟弟,9个大人。”这意味着她弟弟也不是现在的“父母”亲生的,而9个大人9个孩子的“家庭”显得很不正常。 “你读过书吗?你出来卖花究竟多久了?” “读了二年级,出来四五个月了,一直卖花,每天要卖30块钱才够吃的”。 “你爸爸妈妈有工作吗?他们靠什么生活”? “他们不上班。” “他们就靠你一个人养活?” 小女孩想了半天,说:“还有我弟弟。” 也许她并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以及“爸爸”是怎么买得起摄像头手机的。他的邻居说,经常看到这几家安徽人很晚出门,“他们半夜才回来,闹得人心烦,白天什么都不干。”另一个邻居也说:“他们好像还干了点别的事,但不是上班。” 高庆红说,晚上“爸爸”随她们出去卖花,红玫瑰两块钱一支,不卖完15支是很难回家的,所以她们不惜下跪,死缠路人买花,有时会被路人打骂。 “你们晚上要卖花到什么时候?”记者问。 “周末要到2点钟,我们要听话。” 记忆已被“涂改” 9个卖花的孩子,昼夜颠倒,沦为赚钱工具,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失去家园、学校、父母和自由,她们是怎样来到重庆的? “我也不懂为什么到重庆来,我们家乡的孩子都到这里来。”高庆红说话时,双眼迷茫,“我们家乡田多草多地多,比重庆还热。” “你见过自己真正的爸爸妈妈吗?想跟他们在一起吗?” “见过”。小女孩说完后,便一直沉默不语。也许,她不愿也不善于表达喜欢跟谁在一起的话。 并不懂为何来到重庆的她说,花还会再去卖的,过段时间找了钱就会回家上学,而自己来重庆的原因是成绩不好。这些话听起来很不真实,明显被教过——这么小的孩子谈何“成绩不好”? 尽管还有伤在身,高庆红还是习惯性地摆弄起了桶中的玫瑰花。这些花已经凋谢,没有卖相,一支支装在塑料膜中,显得丑陋而艳俗。 午后,高庆红没有吃饭,她说“妈妈”临走时盛了饭,但锅里空空如也,冷锅冷灶的不知饭在哪里。 棒棒公寓里还有来自其他省市的人,他们对“安徽人”印象不佳,说“安徽人”无所事事奴役孩子,而且孩子非常调皮。这些孩子,上午睡觉,下午奔跑于王家坡吊脚楼间的角道里、石梯上,傍晚离开,半夜回来,日复一日,就这样过着没有资讯、没有尊严、没日没夜的悲惨生活。 本报记者涂源/文 韩峰/图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