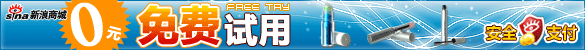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
|
|
萧瀚:逃课是自由的象征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3日10:44 新民周刊
“逃课是自由的象征” 萧瀚写过一篇《我的课堂纪律》的文章,他如此阐述他的课堂纪律,“其一,这里是课堂,不是教堂,这是思考的地方,不是无条件接受他人说教的地方;其二,我是教师,不是牧师,所说的话不是真理——最多只是我认为的可能真理,所以随时可以被质疑……其四,课堂也可以是食堂,来不及吃早饭的同学,可以带食品来,一边吃一边听课,也可以带零食来吃,但不要弄脏环境”。 他也撰文表达了对80后学生的尊重及鼓励,“大学教育中,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这本来就该如此,但在80后身上却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教师必须意识到这个独特问题”。 一位大二时选修萧瀚《中国宪政史》课程的学生回忆,萧瀚“身材瘦弱却精神奕奕”,“上课前,他调侃地宣称自己是普通话说得最好的台州人,骄傲地谈起自己的同乡方孝孺”,还有很多难忘的细节:萧瀚老师走下讲台,倚在第一排的桌子边上,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这么一句话,中国宪政史要从先秦讲起;萧瀚老师曾经跟学生们说过,“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要为自己负责”;萧瀚老师上课爱喝水,他不止一次地一边喝着冰冷的矿泉水,一边宣布他的课堂纪律,他的课堂允许学生把老师的话当成佐料,掺在南方风味的小笼包里津津有味地吃掉;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教室后,放下自带的笔记本电脑,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关掉自己的手机,整整一个学期他的手机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响过,哪怕是小小的振动声;他说过,大学里不培养奴才…… 萧瀚的《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一文或许能更真切地代表他的所思所想,他说,“听课人数的多少有时确实会影响教师的上课情绪,不过,即使听课人数再少,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是不会用点名去强迫人来听课的”。 滕彪理解为,“萧瀚的看法是,应该和学生平等相处,让学生更自由些,如果学生不愿上课,对他们逃课也应宽容,在课堂上应该让学生更多地思考问题、去质疑老师”。 萧瀚跟同学们说,“我不会点名的,我丢不起这脸,如果自己讲不好课,还要逼人听课,这岂不是双重不人道?没人听我的课,我固然伤心,可我的课要是都得动用权力才有人听,那我就更加伤心。我不尊重你们,就是没有自尊——逃课是你们的自由,如果点名是为了保证听课人数,那我就没有点名的权力,因为我没有逼人听课的权力。”他甚至“怂恿”学生,建议“他们只要觉得自己不想听我的课,就不必来,时间宝贵,浪费不起,如果当年我在北大不逃课,我怎么能比别人有更多看书的时间呢?” 王建勋基本赞同萧瀚的教育理念,“听不听课,学生应该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说,不管老师讲得如何、是不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学生也必须来听课,那是一种很糟糕的方式”。 也有人批评萧瀚此论调是“不负责任,误人子弟”,但滕彪指出并非如此,相反,“萧瀚对学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学生对他也非常尊重”,同时,萧瀚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理解,“萧瀚认为,自由并非散漫,而是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学生应尽到学生的责任,教师也要尽到教师的责任,所以,虽然学生可以逃课,但教师必须要仔细地准备、认真负责地讲每一课”。 在王建勋看来,刚开始,萧瀚觉得是否当老师无所谓,因为萧瀚并非一开始就当老师,但是,“从我们最近的交流看,他越来越喜欢当老师、和学生交流,这学期他甚至跟学生组成一些讨论小组,我想他从中应该找到了很多精神上的愉悦”。 萧瀚撰文称,他的课堂是可以自由进出的,但“整个学期18周的课,课间有同学提前走的,但很少,而上课过程中走的一个都没有”,“因为尊重是相互的”。 萧瀚在他本学期最后一课上讲到,“信仰之下,应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依我之见,这个法门只有三个字:‘爱’和‘创造’”。 这给滕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传授知识、解决疑问是教育的一方面,但教育更应该做的工作是,让一个人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成府街与北大时光 王建勋与萧瀚相识迄今12载,他至今记得,初次见到萧瀚是在北大法学院贺卫方老师的课堂上,那时萧瀚正手捧《古拉格群岛》课间苦读;有一次,贺卫方还让萧瀚在课上讲述了自己的读后感。 “他特别喜欢读书,读了很多的书;他很关注社会现实,非常有正义感”,萧瀚的文史功底、人文关怀,及对法治之不懈追求,给王建勋的印象极深。 1992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后,1995年,萧瀚在北大“蹲点复习”,准备考研,当时他尚是“北大边缘人”,王建勋也在北大法学院读书,在他的记忆中,每次贺卫方老师的课,萧瀚都会去听,他们因此一起上了一学期的课,时常见面。那时的萧瀚喜欢交友,“虽然当时他不是正式登记的北大学生,但我没看出他有失落”,相反,王建勋认为,住在成府街的萧瀚生活得很快乐,他每天逛逛万圣书园,找一帮朋友聊天,谈一些严肃的话题;萧瀚也能喝点酒,但“酒量不是非常好”。 在万圣书园,萧瀚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包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萧瀚曾撰文回忆成府街,他诗意地描述成府街为,“你在的时候,你就是一切;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是你”。 那时,萧瀚“疯狂地买书,几乎是没有节制地买”;那时,萧瀚虽没有进北大,但已认识了很多北大的研究生,“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喝酒、咖啡、茶,聊天,到未名湖散步,有时半夜三更地跑到未名湖的石舫上,湖东岸的一排房子在水中的倒影显得静穆而深邃,我们就着湖光月色,抽烟、喝酒、吃零食、聊天,高兴起来还会唱歌”,他和何海波(萧瀚天台同乡、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常去清华吃刀削面,“对我来说,清华最可爱的就是她美味的刀削面了”。 在北京复习的3年里,萧瀚还经常“冒充北大学生听课”,“边缘人选择听课的老师一般都是课讲得最棒的老师,如中文系的钱理群,法学院的贺卫方、朱苏力等等,我们不仅仅是从老师们那里获得知识,更是从他们那里感受一种思想交流的艺术”。 1998年,经过第四次考试,萧瀚进入北大读研,他自认,“总算进了北大,可是一点也没有收获的喜悦”,“因为又有政治课了,还是必修,有的老师点名。于是,原生的逆反心理就又开始冒头,具体表现就是逃课,看自己的书;不去图书馆,看自己的书”。友人说,萧瀚一直如此。 何兵近日撰文回忆,在北大读书期间,萧瀚与何兵的室友何海波是好朋友,“这位萧瀚同学,现在的萧瀚教授,每每要到夜里12点来找海波同学聊天!头发长长的,身体瘦瘦的,颇有孔乙己的遗风。他的自由和散漫是一向如此。但他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却是出奇的认真”。 其间,因为“马”之类的课的考试,萧瀚“没按标准答案答题而没有拿到成绩”,再后来北大法学院改革,这门课由许多老师一起开课,他才交作业过关。 3年后,从北大毕业的萧瀚慨叹,“确实,北大不好进;可是,北大真好出”。 精彩时评 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萧瀚去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财经》杂志的法律顾问。 “天则所当时创办中评网,主要是萧瀚负责,他到现在仍为中评网做些事,但已非常少。”王建勋记得,在中评网那段时间,萧瀚写了很多时评。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孙志刚事件”后,“三博士”、“五学者”分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作合宪性审查,萧瀚为“五学者”之一,他为此撰写了大量时评,呼吁“恶法必须立即废除”。此后,从黄静案、李思怡案到刘涌案,均可见萧瀚的精彩时评。 一位读者评论萧瀚的时评,“让人热血沸腾”,“情感的冲击力直入心灵”。 “萧瀚关注社会上的特别跟法律相关的公共事件,他有强大的写作冲动;虽然他表示不愿再写太多时评,但仍在写”,王建勋说。 在王建勋的印象中,萧瀚学识渊博,视野宽广,笔耕不辍,非常勤奋,“萧瀚很多时间都在家阅读、写作,有很多时候我们叫他出来参加学术会议或关注某个事件的会议,他会说,有很多写作任务、有很多书要读,觉得路上浪费时间太多,都不愿来,他更愿在家里多读点、多写点东西”,因此,即便是学术会议,萧瀚最近都很少参加。 滕彪认为,曾有段时间,萧瀚每天写一篇时评,现在虽少了些,但萧瀚对社会问题仍非常关注,“实际上,萧瀚更多的时间是自己看书、写东西,他用在社会交往上的精力并不是太多”。 在个人博客“追远堂”,萧瀚承认自己是个容易伤感的人,更是容易落泪的人,“一切的情感,一切的美,一切的感伤故事、感伤的人,都可能使我落泪……也许是因为我太爱笑的缘故,落泪也就变得寻常”。 最近,萧瀚为外界关注的许霆案做了详细的法律分析,也特地为陕西绥德校长追县长签字被拘事件做了一首七言古体诗。他给学生推荐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与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他写小说,散文,感怀世事,也表达了对诗歌的喜爱,他常提到顾城与海子。 王建勋近期跟萧瀚有过交流,在他看来,萧瀚目前状态一如往昔,“干他自己的事,阅读、写作,我想这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事业”。 滕彪评价,萧瀚是一个充实、幸福的人,一个让人感觉温暖的朋友,一位能对年轻人的生命起到影响的教师。滕彪认识萧瀚多年,方知萧瀚的真名为叶菁,“现在很少人知道萧瀚就是叶菁,因为萧瀚太有名了”。-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发表评论】
|